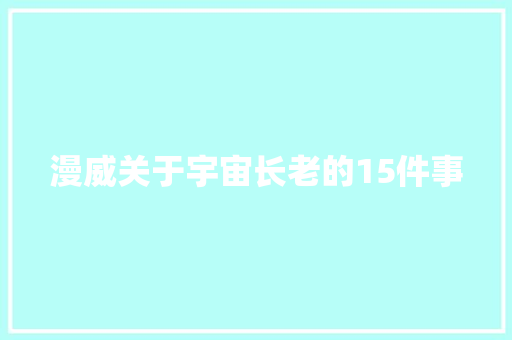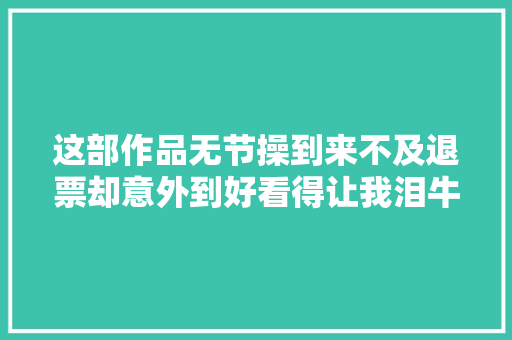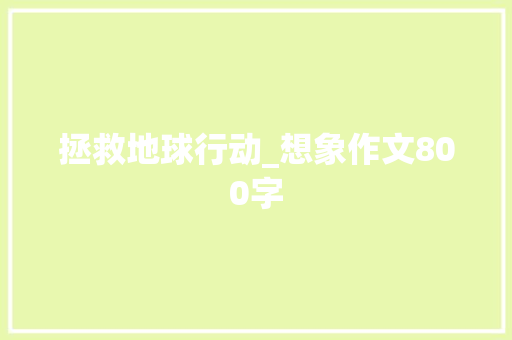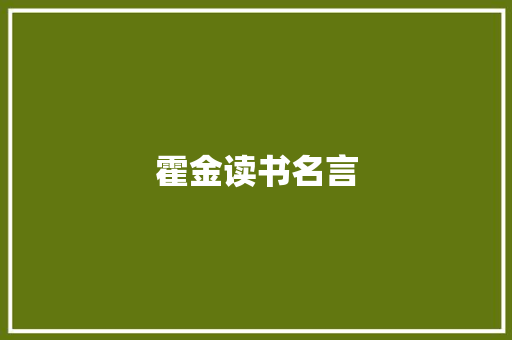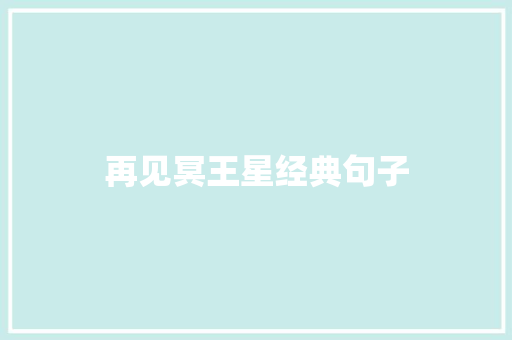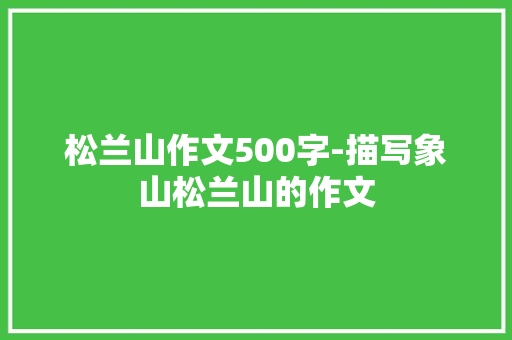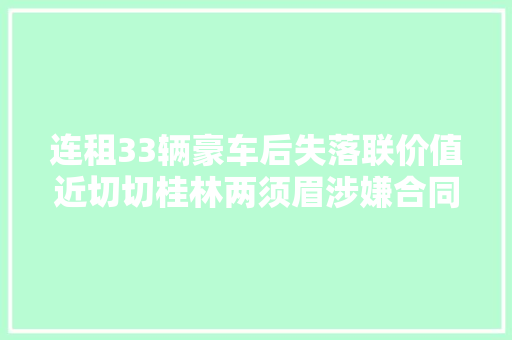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谈到大乘佛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时说:“总的说来,大乘佛学对中国人影响最大者是它的宇宙的心的观点,以及可以称为它的形上学的负的方法。”(《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此处所谓的“宇宙的心”(Universal Mind)是一种与宇宙本体(古代称之为“天”或“道”)同一的精神意识,它不是一种生理学意义上的心(冯友兰称这种心为“个体的心”),而是一种形而上的本心。如果说“个体的心”是一种履历意识,因而各自差异、具有有限性,常常表现为私我意识的话,那么“宇宙的心”便是一种超越的、无限的“宇宙意识”(Cosmic Consciousness),它不受个体的生理、生理所限定,从而能够当下表现宇宙本体的无限性,或者说本身便是宇宙本体。在宋明理学中,这种“宇宙的心”尤其表现在心学或具有心学方向的思想家中。
《大学章句集注》书影 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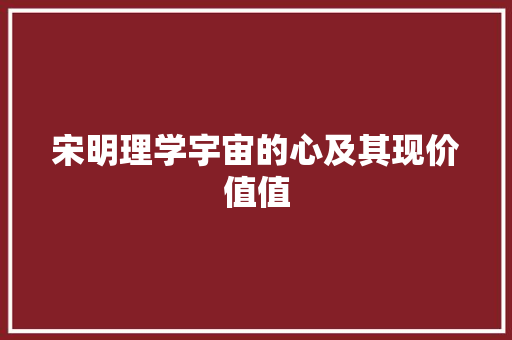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儒家文籍中就有“天心”或“天地之心”的不雅观念,但紧张不是说天具有一种知觉意识,而是“指天地、宇宙、天下运行的一种内在的主导方向,一种深微的主宰趋势,类似民气对身体的主导浸染那样成为宇宙运行的内在主导”(陈来:《仁学本体论》,第227页)。这种观点在宋明理学中仍旧具有主要意义,如朱子学者会说“仁”便是“天心”或“天地之心”,但是他们常日认为这种“天心”或“天地之心”实在是“无为”的,即没有知觉意识。但是在心学的系统中,却可以看到,个人的道德本心与“天心”或“天地之心”的合一,当然这里所谓的“合一”,并不是指两个心合二为一,而是指个体的本心或良知便是超越的、无限的宇宙本体,舍此之外,宇宙别无本体。唐君毅说:“此外宋明儒如陆王之言心,乃即‘民气’即‘天心’。亦有一形而上的绝对意义。”(《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心学家所说的“宇宙的心”便是有知觉的。冯友兰在《新理学》中说:“照心学家的说法,我们个体底人的知觉灵明底心即是宇宙底心。”这种具有知觉的、普遍的、超越的本心,既然是宇宙的本体,则对这种“宇宙的心”有所觉悟的人,一定会产生一种“宇宙意识”,对宇宙中的万物都抱有一种普遍的原谅、仁爱之情,能够与万物相感应、感通,其终极境界一定指向“万物一体”,即万物都是个体道德意识所涵摄的工具,而且都内在于此“宇宙的心”的不雅观照范围之内。对此“宇宙的心”充分觉悟状态便是宋儒程明道所说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程明道是最早具有这种“宇宙的心”意识的理学家,他曾说“只心便是天”(《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河南程氏遗书》卷四),也便是说这种心并不是一种私我的意识,而是一种与天为一的意识,乃至本身便是宇宙的本体(天)。基于此,明道在《识仁篇》中所说的“仁者混然与物同体”“此道与物无对,大不敷以言之”的状态,便是这种“宇宙的心”之表示。可以看出,此种“宇宙的心”是无限的,外物并不在此心之形状成对待,而是为此心所原谅。明道还进一步将其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仁学思想干系联,表示了明道所说的“宇宙的心”,实际上是对孟子的心性论和仁学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明道之后,陆象山是明确地具有这种“宇宙的心”的心学家。陆象山十一岁的时候,曾读到古书中“四方高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的说法,溘然以为他的心产生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无限感,用他的话说便是“原来无穷”,于是他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集》卷二十二)的说法,这可以说是“宇宙的心”的最明确的表达。象山所谓的“本心”便是指这种“宇宙的心”,他所说的“发明本心”便是要将我们的“宇宙的心”从个体的自我意识中凸显出来,成为我们生命乃至宇宙的真正主宰,这便是象山所说的“先立乎其大”。这种“宇宙的心”(本心),由于本身便是宇宙普遍之理(天理)的表示,以是这种心具有普遍性,也便是象山所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然象山并不因此为任何人现实的生理意识都是这种本心,都具有普遍性,由于个体的生理意识可能受气质、物欲、见地、习气等负面成分影响,从而方向于自私,因此不可能具有普遍性,也就不可能是“宇宙的心”。只有从这些成分中解放出来、振拔出来的普遍的道德意识才是真正的“宇宙的心”。象山所谓“才自警策,便与天地相似”(《象山外集》卷四),说的便是这个意思。当人的“宇宙的心”(本心)全体显现时,便是宇宙之理的显现,二者是同一的,其普遍性不言而喻,而贤人之心,便是这种“宇宙的心”的表示,因此古往今来的贤人,都是心同理同的,象山说:“东海有贤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贤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贤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贤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贤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象山文集》卷二十二)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便是,象山的“宇宙的心”的实质便是对万物的普遍仁爱之心,以是象山一方面将心提高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另一方面也自觉到处在“宇宙的心”境界中的人,对万物抱有一种普遍的任务,即“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同上)。
象山的这种“宇宙的心”不雅观念为其弟子杨慈湖所传承。有一次,杨慈湖问象山什么是本心,象山屡次答以孟子的“四端”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慈湖终不能明了。期间,有二人由于买卖扇子起了争执,来找慈湖评判。慈湖在听完二人的陈述之后,对二人的是非进行了裁定并丁宁走了他们,紧接着他又连续请教象山什么是本心。象山答以:“闻适来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敬仲本心。”于是慈湖大悟,“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宋元学案·象山学案附录》)慈湖所谓“无始末”便是超越韶光,“无所不通”便是超越空间,因此慈湖所悟到的本心便是超越时空的“宇宙的心”。基于此种体悟,慈湖作了《己易》,认为《周易》不是在描述宇宙的客不雅观变革,而是在描述“己”之变革。慈湖说:“《易》者,己也,非有他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无际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也。”慈湖这里所说的“己”,并非个体的“个人”,而是席卷宇宙万物的“大我”,这种“大我”实在便是他所体悟的“宇宙的心”的表现。
陈白沙是明代心学的开端,他曾跟随明初的朱子学者吴与弼学习朱子学,希望能够通过多读圣贤之书而悟道,但是终无所得,后来摒弃书册,从事静坐,从而“静中养出端倪”(《明儒学案》卷五),即悟得了本心。这种本心实质上也是一种超越的、无限的“宇宙的心”,白沙对弟子说:“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同上)白沙所说的无内外、无始终、无处不在、永一直息的“此理”,实在便是超越时空的宇宙本体。悟到“此理”的心也就与宇宙同其广大,此时的主体便是一个与宇宙合一的“大我”,故可以说“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实质上这种说法所描述的境界便是杨慈湖《己易》的境界。后来,白沙的弟子湛甘泉继续了白沙的这种“宇宙的心”不雅观念,他作《心性图》,在个中说:“故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明儒学案》卷三十七)这种包括天地万物,与宇宙同其大的没有内外可言的心,便是一种“宇宙的心”。一旦对此“宇宙的心”有了真切的体认,在现实中,人就该当对宇宙中的万物抱有一种一体之感,从而泛爱万物。甘泉说:“本心宇宙一也……不知天地万物同体者,不敷以语本心之全。”(《明儒学案》卷三十七)这一说法就表达了这一意思。
王阳明是湛甘泉的好友,也是明代的心学家,他晚年曾经提出“心外无物”的意见,认为万物都在心的感应范围之内,从我心能够感应万物的角度,可以解释万物和我是一体的,反之,也正由于万物与我是一体的,以是我心才能感应它,否则就不会对其有感应。因此“心外无物”的本色便是理学中常说的“万物一体”的仁学思想。有学生曾问阳明,从形体上来说,禽兽草木等生物以及天地和人是不同的存在,为什么可以说和人是同体的,阳明回答说,“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传习录下》)可见阳明是存心的感应能力来解释万物同体。在阳明看来,从终极上来说,可以将宇宙万物视为一个大身体,而人的本心或良知则是这个大身体的精神主宰。因此这个本心与良知便是一种“大心”或“大良知”,其不雅观照、感通的工具该当遍及宇宙万物,而不应该局限在个体生理躯壳的关注范围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本心和良知便是一种“宇宙的心”。阳明和学生有一段对话,充分表达了这一点:“师长西席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甚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么教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传习录下》)《礼记》曾说“人者天地之心”,阳明根据《礼记》的说法将人视为“天地的心”(可以称之为“宇宙的心”),但他进一步指出“天地的心”实在便是人的“灵明”,详细来说便是人的本心或良知,而不是在本心良知之外的另一个超越的存在。正由于人的“灵明”便是“宇宙的心”,以是它才是满盈宇宙,不受个体躯壳限定的。因此我们该当对宇宙万物一体关怀,而不能受形体限定,陷入自私自利。阳明晚年曾经做了一篇有名的《拔本塞源论》,在个中表达了其“万物一体”的仁爱思想,充分阐发了人对全体宇宙万物的任务。这篇文章的核心不雅观念便是这种作为“宇宙的心”的“良知”。
总之,心学所说的本心或良知,不是受个体生理躯壳限定的、履历生理学意义上的个体意识,即不是“个体的心”,而是超越时空限定的普遍道德意识,乃至一种“宇宙意识”,也即“宇宙的心”,这种“宇宙的心”将全体宇宙万物都纳入了主体的不雅观照之中,并视之为与人一体干系的整体,从而该当一体关爱。从这个意义上说,“宇宙的心”是儒家仁爱思想在主体心灵上的充量发展,理解这一点,才能读懂心学家对付心体的某些看似张皇浮夸的描述,以及明白其建立在此根本上的仁民爱物的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心学家所做的统统工夫,都是环绕着如何证悟、教化、实践这种“宇宙的心”展开的,其终极境界便是“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心学所说的“宇宙的心”对付我们本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都具有主要的启示意义,可以为我们供应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10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