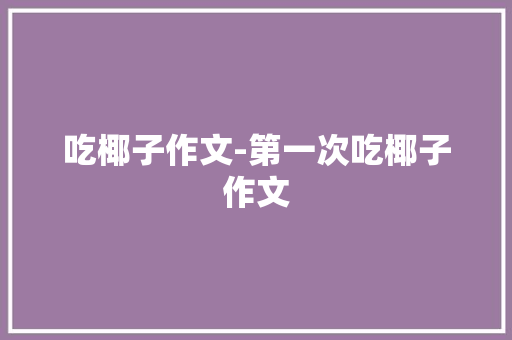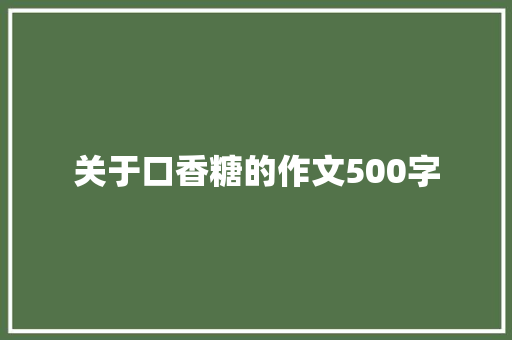“我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乡下的粉肠和红糟肉,你小时候我带你去吃过的,真是好吃。”
夜晚沿着仁爱路的红砖道闲步,正是春夜晴好。仁爱路上盛放着橙色的木棉花,叶已全数落尽,木棉树的枝丫呈着靠近黑的褐色,仿佛已经干去一样平常,它唯一还证明自己活着的,是那些有强硬花瓣的,在夜风中微微抖动的花朵。

到了二段往后,木棉少了,只有安全岛上的椰子树孤单而高傲地探触着天空一角。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以为城市里的木棉与椰子树是兄弟一样的品种,不着花的时候,每每使我们忘却它的存在,但是它们却一年年活了下来,相互看守道路,在寂寞的时候相互对应。
有时我追索着为什么把它们当成相同的品种,是由于长久的不雅观察,使我知道,在都邑的木棉与椰子是永不结果的。如果在我的故乡,春末的木棉花开过后并不掉落,它们在树上结成棉果,熟透之后就在树上爆裂,木棉的棉絮如冬天第一场细雪,随风飘落。每一片乳白的木棉絮都连着一粒玄色的种子,随风落处只假如有土的所在,第二年就长出木棉树的新苗。以是我们常会在水田中看到一株孤零零的木棉耸立,那可能是几里外另一株木棉飘过来的种子。
到了夏天,是椰子结实的时候,那时椰子纷纭“放花”完成,饱满青苍色的椰子彷佛用起重机高高地升到树顶上。但是收采椰子的时候,农夫常常留下几棵最强壮的椰子做种,等到椰子内部长成实心的时候才采收下来,埋在地下,不久就长芽抽放;如果将它放在大盆子里,每天浇点净水,椰子也还是地萌芽,然后运送到城市,成为充满绿意的盆栽。
记得我故乡的国民小学,沿着低矮的围墙就种满了椰子树,门口的两株长得格外高大,那椰子树是父亲读小学时就有的,后来我才知道全体校园的椰子树全是由门口的两株传种,一个校园的上百株椰子树事实上是一个弘大的家族,有着血亲的关系。每次想到那一群椰子,都给我一种莫名的冲动。
如今在仁爱路上的椰子,不要说结实传种,它们乃至是不着花的,只有站在安全岛的一角,默默谛听途经的车声。
过了临沂街右转,就走进铜山街的巷子,走进了我生命中的一段历史。
十几年前我初到台北,虽然心中有着向新环境开拓的想法,但从偏远的乡间溘然进入这样的大城,不免有一种惶惑和即将迷失落的恐怖。我从台北车站小心翼翼地坐上零南公车,特殊交代车掌小姐在临沂街口让我下车,我坐在车掌身后的位子上,张皇地看着窗外的景物,直到瞥见了仁爱路上的椰子和木棉才稍稍放松心情。
公车到站的时候,就读小学三年级的大侄女,在站牌上等我,带我到堂哥家里。堂哥当时住在铜山街三十三巷一号,是一个两百坪的日式平房,屋前的庭园种了正在盛开的花草,门口的两边各种了一株数丈高的椰子树,那时正结满了椰子。屋后的院子是水泥地,让小孩子玩耍。
初到台北时寄住在堂哥家里,他让我住在庭园边的小房间,每天从窗口都能瞥见那两株高大到险些难以攀爬的椰子树。那时的堂哥正当盛年,意气十分风发,拥有一家规模极大的石棉工厂,和一家中型的水泥厂,他曾在故乡担当过一届县议员两届省议员,是普遍受到尊敬的。我非常敬爱他,虽然我们年事相差很大,不雅观念也不太能沟通,乃至在家里也很少交谈,但是我每天看他清晨在园中浇水,然后爱惜地抚摸椰子树干,心里就充满了冲动。
有一次我们坐在一起听音乐,同时看着窗外,目光不谋而合落在椰子树上,堂哥的脸上溘然流过孩子一样平常天真的笑颜,对我说:“你看,这椰子是不是长得和家里种的一样好?有人说台北的椰子不结果,我种的一年可以生一百多粒呢!
”我点头表示赞许,他随即感喟地说:“可惜这椰子长得太瘦了,没有我们家的强壮。”
接着我们沉默起来,让薄暮逐渐退去,阴郁逐步地流进来。
我找到过去住的铜山街,门牌的号码早就改换了,堂哥的屋子被铲平,盖成一栋七层的大楼,不要说椰子树,连一朵花都看不见了。
我在堂哥家住了一年,直到我考上郊区的学校才搬走。接着是台北一次空前的经济低潮,堂哥的奇迹纷纭因负债而被拍卖,乃至连住的屋子都保不住。屋子要卖之前我去看他,他仍像往常一样乐不雅观,反过来安慰我:“难不成我回家种田便是了。只是这两丛椰子砍掉,实在可惜。”
那一次卖屋子对堂哥的打击很大,他的身子没有以前健朗,加上租屋居住,时常搬家,使他的性情也变得忧郁了。他把末了的积蓄投资建筑业,奋力一搏,没想到遭逢建筑业不景气,反而使他一病不起。
他过世的前几天,我到医院看他,他从沉沉的昼寝中惊醒,那时他的耳朵重听,身体已不能动了,说话十分吃力,看到我却笑了一下,我俯身听他说话,他竟说:“我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乡下的粉肠和红糟肉,你小时候我带你去吃过的,真是好吃。”说完,失落神的眼睛仿佛转回了故乡那一担以卖粉肠和红糟肉有名的小摊。
第二天,我带粉肠和红糟肉给他吃,他只各吃了一口,就流下泪来,把东西放在病床一角,微弱地说:“真是不如我们乡下的呀!
”他默默地堕泪,一句话也不肯再说。
一个星期后,堂哥过世了。
他留下来的末了一句话是:“赶紧把我送还乡下去埋葬吧!
墓前种两丛椰子树。”
堂哥留下四个孩子,当年在站牌等我的大侄女,如今已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韶光就这样流逝,彷佛清晰如昨日的事,没想到已经十几年了。
静夜里我常想起堂哥的生平,想到他和椰子树那不为人知的情绪,令我悲哀莫名。或者他便是乡间移植到城市的一株椰子树,经由努力的灌溉,虽然也结果,却不免细瘦,在一全体城市与韶光的流转中,默默地消逝了。
我沿着铜山街,一步一步地走到底,整条街竟看不见一株椰子树,而仁爱路上的那些,是没有一株会结果的。
走出铜山街,举头见到满天的小老婆星,忆起童年常唱的两句歌词:“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老婆星。”星星还是一样的星星,可是星星知道什么呢?星星知道人间里的一株树有时就会令人落泪吗?
我溘然强烈地思念着故乡,想发迹乡木棉和椰子那落地生根的力量,想起堂哥犹新的墓园,以及前面那两株栽种不久还显得娇嫩的椰子树。
等到那椰子成熟,会不会长出更多的椰子树呢?那上面,永久都会有微笑闪动光明的星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