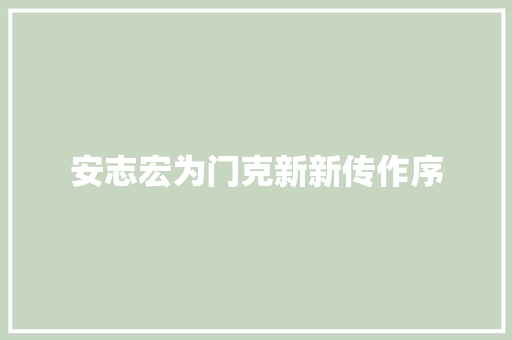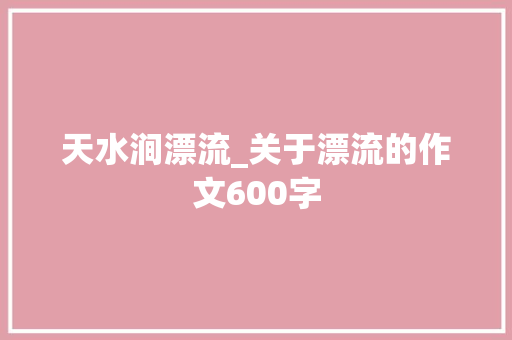在翻山越岭的宝兰线上,有这样一座车站——渭南镇站,在浩瀚车站中,它很普通,但它曾是多少人背起行囊告别故乡、踏上远方征程的出发点。
在这座小站,有一列运行于陇西至天水之间的7504/7503次绿皮车。这趟车记录着故乡的四季、幽长的隧道和一群已经终年夜的孩子的俏丽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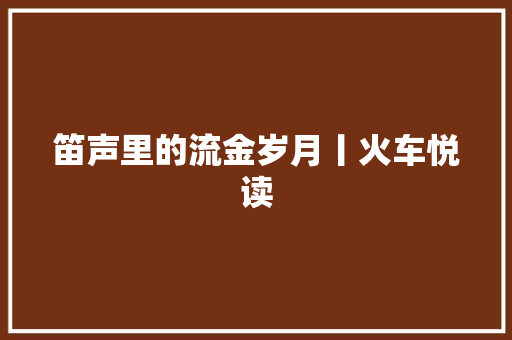
小时候,家住铁道边,看惯了各式各样的火车,听惯了火车的笛声,无论白天黑夜,那笛声里总有说不完的故事。
坐这趟车的人基本都是附近村落里的人。有担着一箩筐蔬菜去市里贩卖的菜农,有带着孩子去医院看病的母亲,有衣着亮丽去麦积山旅游的情侣,还有去城里读书的学生……火车差不多1个小时就到达了天水站。
车厢里挤满了人,好不热闹:靠窗的两个中年妇女相互倾诉着自家苦处,说到激动处,竟手舞足蹈比画起来;靠近车门的几个青年,讲述着各自的十丈软红;末了一排座椅的角落里,坐着几个穿校服的学生,默默看着窗外缓缓流动的远山,想着各自的苦处。绿皮车溘然启动,车厢里得到少焉的安静,之后又是此起彼伏的繁盛热闹繁荣,不认识的人经由一番发言便熟络起来,这列车载着每个人的故事奔向远方。
窗外有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在野外中招摇;有绿油油的颗粒饱满的麦田,在薄暮的热浪中来回翻滚;有漫山遍野的草木,在四季中变换着色彩;还有落满皑皑白雪的铁路栈道,合着山川一色,让人想起坐绿皮车去置办年货的场景。
渭南镇站到天水站,要经由三阳川站、南河川站,母亲的外家就在三阳川。关于这座小站,我一想起,脑海里就浮现出一幅明月沙地看瓜图。舅舅家以前种过好几亩西瓜地,我和弟弟每逢暑假去舅舅家,就会途经渭南镇到三阳川这段铁路线。有时,我们会遇见戴着黄帽子、沿着线路巡检的人,他们肩上扛着铁锹和钢叉,手中拿着一个玄色的“电话”,里面发出滋啦啦的声音。现在,我也成了铁路大家庭的一员,这是当时的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光阴悠悠,南山南
对付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北人而言,大山是我最深的印记。
渭南镇站的南边是一座座连绵起伏的山脉,像极了奔驰的野马,追逐着天边的太阳。绿皮车就在这此起彼伏的山脉间缓缓前行。绿皮车途经我们村落时,我能看清老院门前那棵白桦树上的几只喜鹊和我家的青瓦房顶,一起上能遇见许多熟习的村落。尤其是远方的南山印象最深,平时看它,没什么新奇之处,可坐在车里,随着火车的移动,这山就缓缓地躲在列车后面了。我目送它,直到看不清时才转过分,乃至竖起拇指就能遮住一个山头。
那时过年,在外的人都选择从天水站坐绿皮车回家,经由十几条长短不一的隧道,就能瞥见熟习的家乡景致了。远方的南山,彷佛一动不动,让人不禁想起“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那些年,家乡的变革不大,变革大的是我们每个归村落夫坐在绿皮车上的心情。看着故乡的一草一木,望着夕阳下的羊群,心情难以言表。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他们还好吗,他们的内心是否也跟这大山一样,依旧苍翠如初。
最近几年回家,故乡的变革天翻地覆。高铁贯通了,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穿行于山峦环抱中的高铁与连接城乡的绿皮车相呼应,让人记住了岁月的味道,感想熏染到了发展的喜悦。
予我欢畅城,绿影暖浮生
在渭南镇站阁下,有一处天水站分货场。一年四季,源源不断的货色从这里装卸,然后由大货车运往各地。父亲在货场事情过几年,有时太忙,顾不得回家用饭,我每次放学都会给父亲带饭。那时,我是第一次如此近间隔地打仗火车,它漆红的巨轮和刚劲的铁皮车厢让我肃然起敬。
现在,父亲不在货场事情了,我的火车情怀依旧在,由于它曾是许多像父亲一样的人奋斗过的地方,我对铁路又多了一份感激之情。
高中时,我在城里念书,周末回家都会和同学坐绿皮车。火车是下午4点从天水站发车,每次我们都像跟韶光赛跑似的。下午上课前,提前整顿好东西,下课铃声响起,我们早已冲出教室。当瞥见站台上停靠的绿皮车时,那一抹绿影,让我们感到无比亲切。如今,假如在某座车站,或者某本杂志上瞥见绿皮车的身影,我依旧心存温暖。坐在绿皮车上,我们心中装着一种回家的幸福感,一起上,望着窗外的山影、广阔的野外和那条宽宽的渭河,我想到那个词“岁月静好”。
现在,再次坐在这列绿皮车上时,美好的回顾流淌成诗。想起那些熟习的人和事,欣然开怀。
来源:《公民铁道》报
笔墨:夏翔
图片:夏翔 王富泽
来源: 公民铁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