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父亲请了当地党支部的布告和几个委员好好的喝了一顿酒,于是就盖了个红彤彤的章。
根据母亲的描述,那个布告喝得满脸通红,然后在餐桌上大笔一挥写了一段笔墨,以是当我升到支部布告看到自己当年的政审文件时,我就理解为什么上面有一小片油乎乎的污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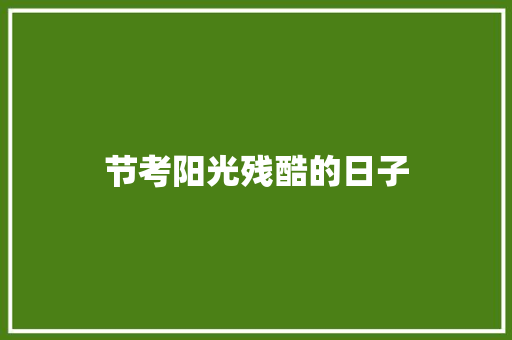
那份文件并不是那么好获取的,最少在父亲和母亲的印象里非常困难,以是才会有这么一顿酒。曾经姐姐、表哥的入党书被驳回,便是卡在这份政审文件上,而那个情由是小时候的我所不能理解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村落里人对我的称呼都不太一样。
村落中央破屋住的那个人,宅子褴褛的只剩下地基和几面残破的墙,像被炮弹炸过一样。两个篮球场那么大的院子里杂草丛生,有两棵巨大无比的梧桐树,遮天蔽日的树荫让那个宅子显得阴森胆怯。他住在一个塑料帐篷里,以捡褴褛为生,晒得黑洞洞又瘦的像个猴子,牙齿很白,朝人笑的时候像一只营养不良的黑猩猩。他叫我“谢家相公”或者“谢相公”,总让我觉得他在叫我老公一样。
听老人说猴子的祖上非常富有,但是家里托生了个穷苦人,整日吊儿郎当吃喝玩乐,赌博、逛妓院,后来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折腾了十几年总算是把家底败光了。一想到这个,就觉得猴子是个很可怜的人,我也不怎么反感他相公相公的叫我了。
我有个四姑,大名谢四花。她长了一张好脸,年轻时是我们那有名的美人,但是我记事开始她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尖细。后来嫁给了一个外地来的男人,生出的孩子跟我一样平常大,总喜好陵暴我们这些小孩子,到处惹是生非,我就以为她越来越丑了。
虽然是四姑,但她从来不叫我小名,总是一口一个谢公子的叫我,这个称呼让我更加厌恶她。
春节我最不喜好的一个环节便是拜年,同龄的小伙伴们平时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这样称呼,但每到拜年的时候我就从弟弟变成了小叔叔,上了中学还变成了小爷爷,和父母同龄的人我要叫哥哥嫂嫂。由于我以前只根据年事来判断称呼,以是每次拜年前都会问一遍我该叫他什么,但纵然这样也闹了不少笑话。
直到16岁许可我去翻阅族谱和村落志的时候,我才大概理解了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奇怪的称谓。
谢家,祖上是地主。
每次看到别人爷爷奶奶的叫着,我都有种说不出的倾慕。听说隔代亲是最亲的,而我从来没有体会过。在我姐姐出生前,家里的老人就过世了。大概对我来说唯一幸运的事情,便是不会很快就经历死活别离吧。
族谱上说,爷爷是自尽的。
在那个阳光残酷的日子里,划分阶级以打标签的形式把人们分别隔,他是中下贫农,你是城镇贫民,还有小业主转的资产阶级,我们家是地主,一开始是富农,后来变成了反革命的地主。
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16岁,从那开始每每想到父亲16岁就没了父亲,以是我从来不问也不提爷爷的事情。族谱上对爷爷的评价有一句“貌力雄奇,来日诰日理,固人伦”,这是父亲写的。
我成年后,记得有一次修缮族谱的时候,我小声地问了一句父亲“爷爷长什么样子”。父亲先是一愣,然后转头打量了我一下,说你自己照照镜子就知道了。
听说爷爷身材高大,有1米8多的个子,体格健壮,村落里晒麦场的碾盘有400多斤,爷爷可以一个人立起来滚来滚去。爷爷博学,由于地主家的儿子有钱念书,以是知识渊博,乃至还会说一些大略的英语。爷爷热心肠,常常接济一些村落里的穷汉,送粮食送钱请大夫。“咱们家不哀求大富大贵,能周转就行,咱们的钱都是村落里相亲们给脸才赚的。”父亲说这是爷爷曾经跟他说的话。
父亲没有遗传爷爷的身高,母亲说,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吃上饭。
村落里的祠堂被毁了,排位全部烧掉了,四大天王的雕像被砸碎涂上了五颜六色的油彩。我们家老宅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插上红旗的。以前当过保长,宪兵队的老人都被揪了出来,就在被毁掉的祠堂门口的台子上。
爷爷跟家人告别后的第三天,就被抓走了。
第四天二奶奶和三奶奶带着孩子一个北上一个南下。
后来我上小学,溘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个三叔,他把三奶奶的骨灰送了来。再后来,我才知道三奶奶当年去了深圳。
再后来我上高中,中午回家惊异的看到一辆奔驰停在门口,父亲让我叫一个油头粉面的老头二叔,我才知道二奶奶当年去了北京,后来去了美国。
就这样,我们家祖坟阁下又多了两个小坟。
爷爷每天清晨都会抱着一块牌子出去,晚上再拖着一块脏不拉几的牌子回家,他会把牌子擦的干干净净第二天再用,绝不让家人碰。
爷爷会笔直的站在台子上,他们嫌爷爷长的太高了,就用棍子抽打他的膝盖窝让他跪在地上,爷爷会笔直的跪着。
爷爷的腰被打断了。由于他跪着也没比他们矮多少,他们厌恶这个无论站还是跪都这么理直气壮的人,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求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匍匐在地上认错。
爷爷能逐步佝偻着背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他们冲了进来夺走了拐杖,父亲和大伯被推倒在地上。他们当着爷爷的面殴打着父亲和大伯,打的他们两个滚来滚去,打的他们两个一身尘土、满脸是血。爷爷的手撑在腿上,没有跌倒。
爷爷那天清晨吃了很多东西,心情特殊好,然后留给父亲和大伯一人一个窝头就抱着自己的牌子出门了。当天中午,爷爷撞去世在了祠堂石狮子剩下的底座上。
听说当时爷爷的背又直了起来。
窝头里面有个字条,该当是兄弟两个随机的。
大伯在奶奶的衣橱里找到了先容信,后来平反找到了爷爷曾经帮助过的一个人,成了一名国企的工人。
父亲在老宅子的石榴树下挖出了一坛黄金,后来学做司帐,改革开放后做起了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