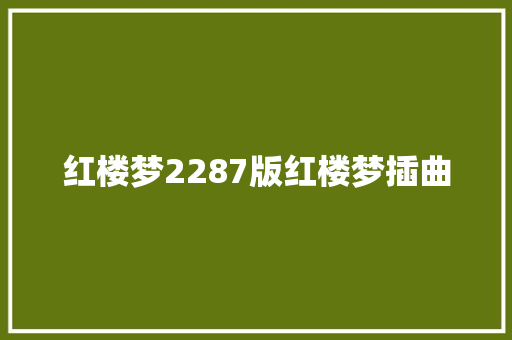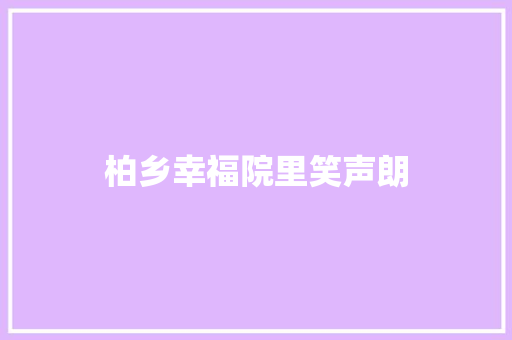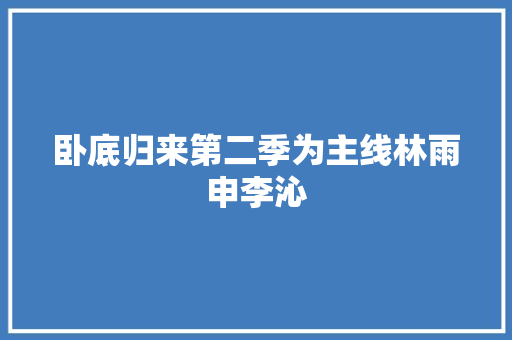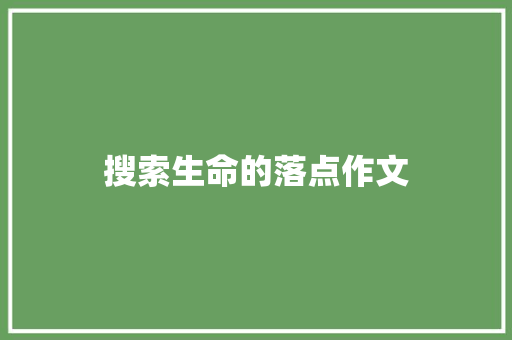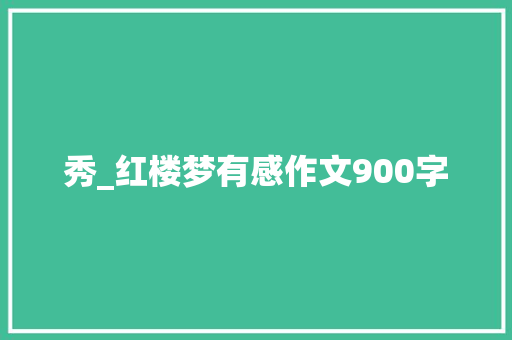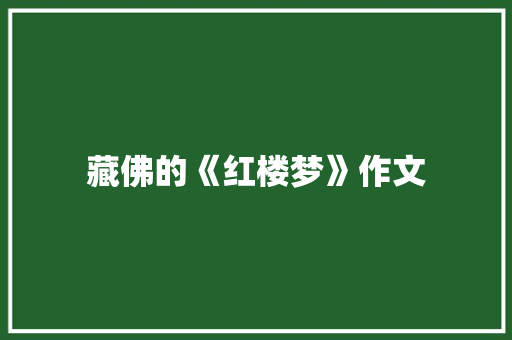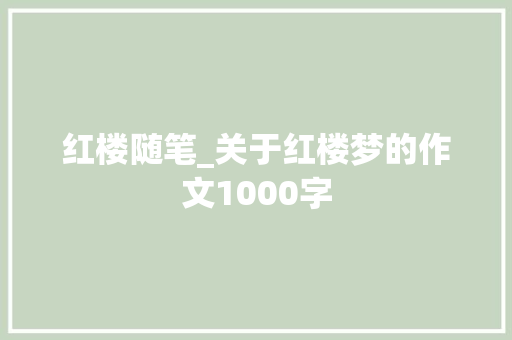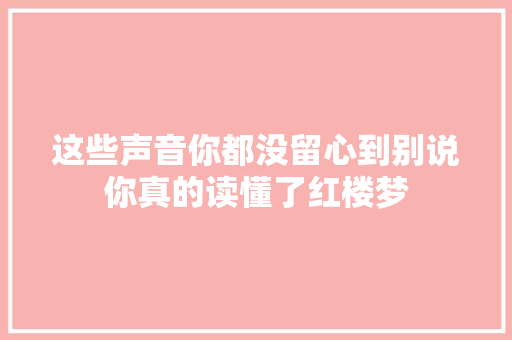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命十二仙女为其演唱《红楼梦十二支》,演唱完第3曲《枉凝眉》,“宝玉听了此曲,散漫无稽,不见得好处,但其声韵凄婉,竟能销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问其来历,就暂以此释闷而已。”脂砚斋作为《红楼梦》的第一位批书人、曹雪芹的密友批语道:“妙!
设言众人亦应如此法看此《红楼梦》一书,更不必深究其隐寓。”(《红楼梦》第五回)
太虚幻境,是曹雪芹虚构的一个梦幻境界。它在第1回甄士隐的梦中被侧面述及;在第5回又于宝玉的梦游中正面展开描述。按照第1回开篇的阐述,整部《红楼梦》原来是女娲补天遗落在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幻形入世”的一段经历记载,即《石头记》。“到头一梦,万境皆空”,《石头记》本是一场幻梦。太虚幻境是这场幻梦之中的幻梦,是梦中之梦。因此,太虚幻境是极虚至幻之境。我们知道,太虚幻境是元春封妃后贾府兴建的大不雅观园的隐喻和预示。正如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中止于虎狼鬼怪齐聚的险恶迷津之地,在惊吓胆怯中梦醒;大不雅观园在仅仅一年的“温顺福贵”之后,即落入肃杀凋零。与大不雅观园虚实相照,太虚幻境所蕴含的人生寓意是不可忽略的。因此,我们对付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的解读,必须转虚为实、幻中求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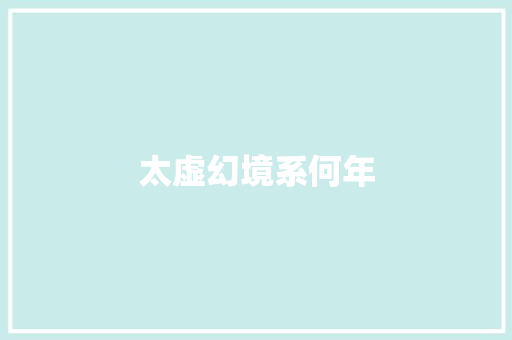
如果梦境是虚幻,那么,现实则是真实。这场虚幻的梦境,是在现实的什么节点上展开的呢?第1回已申明,《红楼梦》叙事不拘于“朝代年纪”,全书没有朝代或干支纪年。“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第1回),“又不知历几何时”(第17回)。这是对小说故事年代背景的虚化,即“将真事隐去”的叙事策略。“倏又腊尽春回”(第12回),“至越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第27回),“因今岁八月初三日乃贾母八旬之庆”(第71回)。书中紧张以节令、时令特色和人物生日表示韶光发展和岁月更替。书中虽然没有朝代和纪年,但是有一条确实的韶光线索。这个韶光线索,因此书中紧张人物的年事交互参照作标志的。我们要确认宝玉梦游的韶光节点,亦即要确认宝玉当时的年事,必须在他与大不雅观园中众女孩的年事参照中做推测。
宝玉梦游发生在黛玉与宝钗先后寄住贾府之后。据第2-3回的阐述,黛玉是在丧母之后两月内动身来都中入住贾府的。她到达时是冬季。这一年,黛玉6岁。据第4回阐述,宝钗因在其兄薛蟠抢买小妾喷鼻香菱(原名英莲)、打去世人命之后,随母兄来到贾府。在第3回末、第4回顾,小说述及,初入贾府的越日,黛玉就在看望王夫人时得知了薛蟠命案,此时薛家三口已经带着喷鼻香菱离开金陵,前往都中。这一年,薛蟠15岁,宝钗小其两岁,即13岁。第五回,在略述黛玉和宝钗先后入住贾府情形之后,以“因东边宁府中花园内梅花盛开”一句,转入宝玉进入宁府做客、在秦可卿卧房中梦游的情节。
俞平伯拟的《〈红楼梦〉底年表》,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阐述的事,是曹雪芹11岁到19岁的事;小说正文开始于第3回黛玉进贾府。他认定宝玉与曹雪芹的年事是相同的。(《红楼梦辨》)据俞平伯之说,宝玉梦游是在其11岁之后的事。然而,周汝昌撰的《红楼纪历》将宝玉梦游时的岁数确定为8岁。(《红楼梦新证》)此后,周绍良在其《〈红楼梦〉系年》中也将“宝玉梦游”定为其8岁时势。(《红楼梦研究论集》)
宝玉梦游的结尾,是在警幻仙姑的教导和安排下,与乳名“兼美”、字“可卿”的女孩儿举行儿女之事后的越日,在无路可走的惊吓中失落声喊着“可卿救我”醒过来。回到现实中的宝玉,被袭人创造了梦遗,只好将梦中之事见告她,并且强求她“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第6回)从梦游到现实,从兼美到袭人,“同领云雨之事”,一虚幻,一真实,宝玉的性启蒙就如此开始了。从生理学讲,男孩首次梦遗的年事一样平常在13岁旁边。如果宝玉梦遗,只是梦中之梦,自然无不可。但是,这不仅是梦中之事,也不仅是一次真实的梦遗,而且,梦醒之后的宝玉强使比他大两岁的丫鬟袭人与他初试房事。这是一段写实的描述。我们不可能相信,唯恐“失落其真传”的曹雪芹会把宝玉写成一个8岁就梦遗、并且与丫鬟考试测验房事的奇人。
这时,袭人多大呢?小说中没有直接阐述袭人的年事。但是,在第62回宝玉庆生时,小说写道:“大家算来,喷鼻香菱、晴雯、宝钗三人皆与他(袭人)同庚。”
在第4回阐述薛蟠命案时,借应天府门子的口说出当时喷鼻香菱“如今十二三岁的光景”。在同一回中,小说阐述,当时宝钗13岁。这是印证了喷鼻香菱与宝钗同岁。在第1回中,喷鼻香菱3岁时,其父甄士隐梦到青埂峰的顽石幻形入世,这是暗示宝玉出生,也暗写喷鼻香菱比宝玉大两岁。两年之后,宝玉中魔怔,被僧道二人补救,那僧人持着宝玉佩带的通灵宝玉说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
”(第25回)这是暗示衔玉而生的宝玉此时已13岁。综合印证,宝玉梦游之时,他11岁,比他大两岁的喷鼻香菱、晴雯、宝钗和袭人均为13岁。
周汝昌将宝玉梦游定为其8岁时行为,紧张依据的是第3-4回中的阐述,特殊是小说以薛蟠命案为两人先后入住贾府的连接。黛玉进贾府越日就知道薛蟠命案,且贾雨村落两月后就补缺上任应天府,并即审理薛案;待薛家到达贾府前,结案的已达贾府。周汝昌因此断定,黛玉和宝钗入住贾府,不过一冬一春(半年)间事。但是,贾雨村落审案时,代去世者冯渊告状的冯家仆人说:“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这便是说,从案发到结案,至少一年多。那么,宝钗入住贾府,至少比黛玉晚一年多。再者,就第5回开篇阐述黛钗先后入府后的情形而言,不仅可见在宝钗之前,黛玉已经入府成年累月,而且宝钗在府中的生活也在数月之上。
更主要的是,在后来的争吵中,宝玉对黛玉说:“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的这么大了,他(宝钗)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疏离你的?”(第20回)不久,宝玉再次对黛玉重复说“(两人)一桌子用饭,一床上睡觉”。(第28回)由此可见,在宝钗进入贾府之前,黛玉和宝玉经历了一个两小无猜、由小终年夜的岁月。黛玉6岁多、附近7岁入府。宝玉梦游在宝钗入府之后,这是绝不可能在他8岁时发生的事。宝钗入府时13岁,宝玉11岁。宝玉梦游发生在其11岁时,是无疑的。
在其“红楼梦年表”中,俞平伯认为小说正文开始所述之事,是宝玉(曹雪芹)11岁时之事。但他又把正文开始定为黛玉初入贾府的第3回。黛玉入府,年仅6岁多,次年2月12日才满7岁。此时,宝玉“如今长了七八岁”,符合黛玉所说“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从七八岁长到11岁,还须要三四年。因此,若以宝玉情窦初开、步入少年时期的11岁为正文开始(“入书”),则是第5回。第5回,宝钗13岁,黛玉10岁,宝玉11岁。过去三四年间,尚处孩提时期的宝黛“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行同止”;现在,“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这日,不知为何,他二人言语有些不合起来,黛玉又气的独在房中垂泪”。(第5回)钗玉的“金玉良缘”和宝黛的“木石前盟”之冲突、争夺,由此而始。俞平伯也忽略了这段不当忽略的三四年韶光差。因此,若采取俞平伯的“正文”说,《红楼梦》的“正文”不是从第3回黛玉入府开始的,而是从第五回宝玉梦游开始的。这一年宝玉11岁,符合俞平伯所定《红楼梦》“入书”年事。
书中有两个情境明确表现了曹雪芹对人物年事的郑重态度。其一,宝玉在宁府的一个小书房撞见书童茗烟与一小丫头偷情。在指示这女孩儿跑走之后,宝玉讯问茗烟这女孩儿的年事。茗烟回答说:“大不过十六七岁了。”宝玉说:“连他的岁属也不问问,别的自然加倍不知了。可见他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
”(第19回)其二,晴雯被伤害病逝后,宝玉做祭文《芙蓉诔》。该祭文前部写道:“窃思女儿自临浊世,迄今凡十六有载……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有畸。”(第78回)称晴雯“十六有载”,宝玉计的是实岁,按习气打算虚岁,晴雯17岁,合书中与宝钗诸人同岁之说。这两个情节表明,在宝玉的心目中——自然也是在曹雪芹的心目中,年事对付一个人的人生具有分外的代价,是否关注一个人的年事,是与是否对这个人关爱而且深于情相联系的。
11岁,宝玉梦游是其由一个孩童进入青春期间的节点。在梦游之后,从第6回到第16回,在大约一年间的过渡中,小说以层波叠浪的笔法展示了一个繁芜险恶的贾家世界。这是“终年夜了”的少年宝玉所看到和感想熏染的成人间界——为了集中展示这个天下,曹雪芹安排黛玉回家探望病父和守丧。这是11岁的宝玉心性磨炼和成熟的一年。在第17回中,费时一年兴建大不雅观园。这年宝玉12岁。从第18回到第53回,即从元春省亲的元宵节到次年元宵节,是宝玉与众姊妹在贾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极享温顺福贵、纵情任性的岁月。这是宝玉的13岁人生。转入次年,宝玉14岁的生日,“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第62回)这场没有成年长辈、完备由一群“不过十五六七岁”的男女少年参加的生日夜宴,是一场春心放肆、诗意烂漫的青春祭。此后一年,渐入败象的贾府日露恶厉,凤姐逼去世尤二姐;夏金桂摧残喷鼻香菱;王夫人抄检大不雅观园,残酷驱赶晴雯,致其含冤病亡。大病一场的宝玉出门看到的大不雅观园,是一个花落人去的凋零天下。“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第78回),情天恨海的大不雅观园显形为一个现实中的残酷无情的天地(第79-80回)。这一年宝玉15岁。
在传统中国社会,15岁是一个告别少年进入成年的年事。15岁的薛蟠,已是一个皇家贩子了,“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第4回)曹雪芹原作80回往后文稿佚没,高鹗等续书似是而非。第80回往后的宝玉又将如何呢?我们只能百般揣测了。
《红楼梦》是曹雪芹平生唯一著作,他著书的宗旨是为其“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作“真传”。“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濒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红楼梦·凡例》)他自述著《红楼梦》,一方面,“因曾经历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另一方面,“至若悲欢离合、兴衰境遇,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这是虚实结合、真幻变换的叙事手腕。读《红楼梦》不须要以索隐和考证的办法在书中追求作者的寓意和出生——“不察其原委、问其来历”。但是,如果不理解曹雪芹独到的叙事手腕,不能从虚幻中见真实,则不能真正领略这部旷世奇书的人文意义和美学代价。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虚幻至极,但又极其切实。如果只是恍惚读来,则必错失落其深刻的真实(“事切”)和隽妙的意蕴(“真传”)。
脂砚斋批语说,曹雪芹撰《红楼梦》,情之至极,言之至确(第18回);妙神妙理,请不雅观者自思(第8回)。读《红楼梦》,不仅须有一腔热心肠,还得具备神清意明的理智。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15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