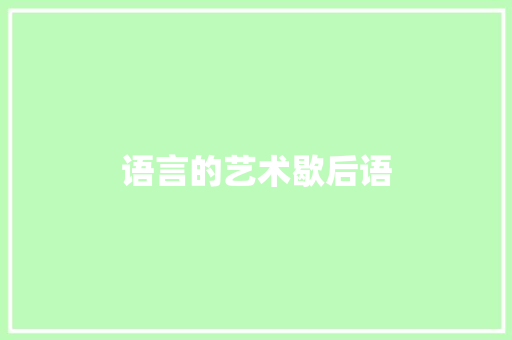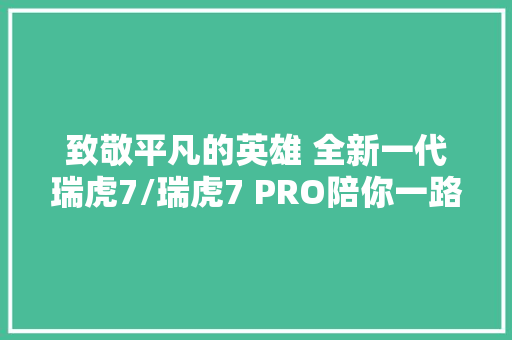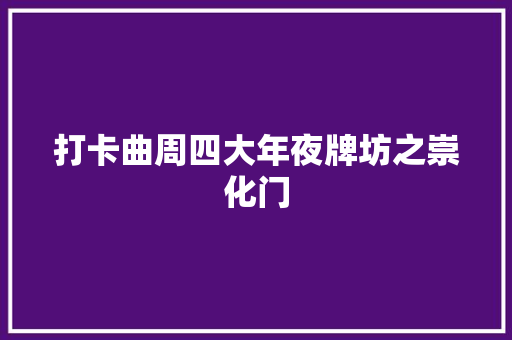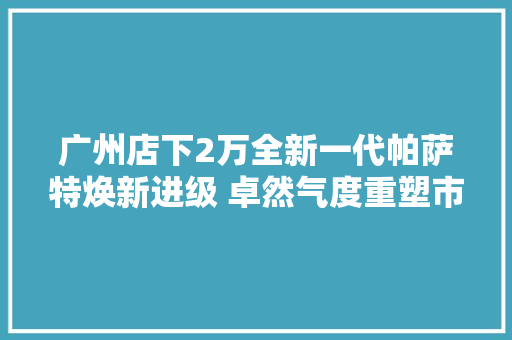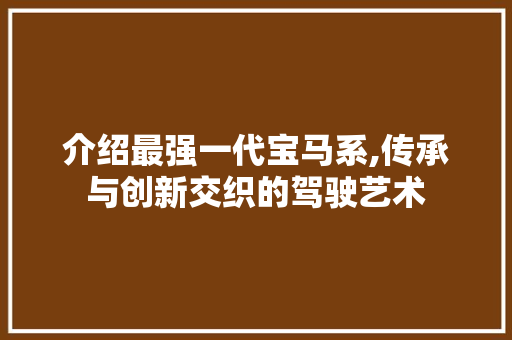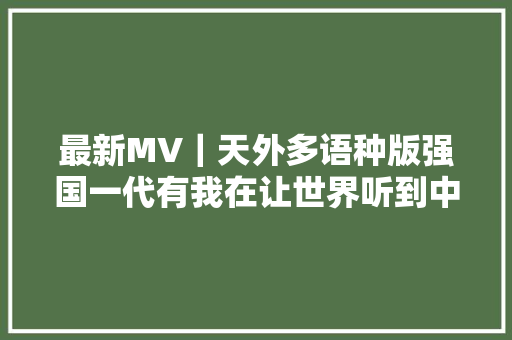《在路上》
作者:杰克·凯鲁亚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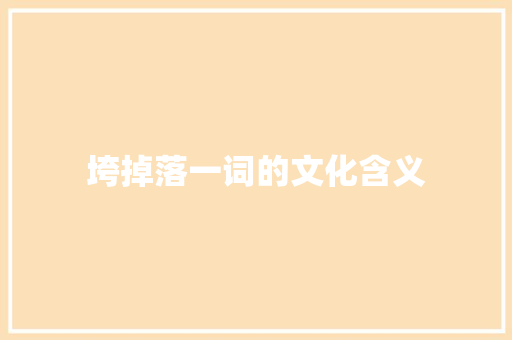
译者:陈杰
版本:大鱼文库|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
哥伦比亚大学
科瑞格斯摩尔西115号
巴纳德学院
“城市之光”书店
六画廊
“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是美国20世纪中叶的一个主要文学流派,也是西方文学史上最为奇特的一个文学流派。对付许多普通读者来说,“垮掉的一代”的吸引力彷佛更多地来自于他们特立独行的生活办法,而非他们的文学作品。然而,为什么像《在路上》这样的小说能够受到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喜好,而且还被列入文学经典著作的行列呢?即便是拿“垮掉征象”来说,爵士乐、吸毒和性放肆,这些与念佛修禅截然不同的生活办法,又是若何统一在“垮掉的一代”文学中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须要搞清楚“垮掉”一词的含义(beat)。正如凯鲁亚克的传记作者查特兹(Ann Charters)所说,“垮掉”一词“就像一把伞那样展开,险些覆盖统统”。作为“垮掉的一代”的共有特色,“垮掉”这一关键词,不仅反响了“垮掉的一代”背叛的生活办法和态度,而且还表示了他们精神追求的内涵。
简言之,“垮掉”有三层含义:“垮掉”(beat down),指一种落魄和赤裸的精神状态;“垮掉”(beatific),指狂喜、极乐、至福的精神状态;“垮掉”(beat),指节拍、节奏、韵律。
“垮掉”含义之一
落魄和赤裸
“beat”是英文常用词,意思繁杂,可作动词、名词和形容词。它的常用意思包括:(动词)击垮、剥夺、耗尽;(名词)节拍、节奏、韵律;(形容词)厌倦、怠倦、困惑、空空如也。在“垮掉的一代”的语境中,学术界一样平常把“垮掉”的定义归功于凯鲁亚克。
在1948年“垮掉派”还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凯鲁亚克对霍尔姆斯讲到了“垮掉的一代”的定义:“我们像是一群生活在地下的人。你知道,我们的内心见告我们那种‘"大众年夜众’的生活是摆样子的,是没有用的。我们过的是一种‘垮掉的’的生活办法——我的意思是,直面生活,直面自我,由于我们的确都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同时,我们厌倦这个天下统统形式和社会规范……我想你可能会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
霍尔姆斯在《这便是“垮掉的一代”》一文中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这篇于1952年揭橥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是第一篇对“垮掉的一代”进行定义息争释的主要文献。这篇文章和他同年出版的小说《走》(Go),使"大众年夜众第一次知晓了这个文学群体的存在,这是“垮掉的一代”走出地下的主要一步。霍尔姆斯在文中写道:“这个词……还指心灵,也便是精神的赤裸,一种只剩下意识时的觉得。简言之,这意味着一个人被无情地推向了自我之墙。”
“垮掉的一代”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危急中终年夜,又经历了“二战”的戕害,然后又在冷战和核威胁的胆怯氛围中生活,这使得他们一贯处于一种“落魄”的精神状态。但与像“一战”后的“迷惘的一代”不同,他们不再纠结于空想的幻灭,由于他们本来就处于空空如也的精神“赤裸”状态,唯一剩下的只有面对自己。按照霍尔姆斯的说法,“垮掉的一代”唯有“相信自己”一条路可走,因而他们才“以一种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办法极度地肯定自我的生命”。于是,我们看到了他们与“迷惘的一代”最大的不同:他们是激情果敢的行动者,而非艾略特笔下那些无能的虽生犹去世的“荒原人”。小说《在路上》中的一个片段非常形象地解释了这一点:“我们驱车离开,看到他长长的身影在夜色中逐渐隐退,就像在纽约和新奥尔良告别时的那些身影一样,我感到很难过:他们犹豫未定地站立在巨大的苍穹之下,周围的统统已然淹没无踪。去哪里?做什么?为了什么?——睡觉。可我们这帮傻子仍矢志前行”。
“垮掉”含义之二
至福
1954年夏天,凯鲁亚克回抵家乡洛威尔,他在天主教教堂里溘然得到一种启迪:beat这个词不便是beatific(至福)的一部分吗?查特兹在《凯鲁亚克传》中说:“对凯鲁亚克来说,这两者的关联绝不仅仅是一个笔墨上的双关,他现在不再谢绝孤独和卑微感,由于他在个中看到了得到拯救的可能性。”这个时候的凯鲁亚克已经开始修习佛教,同时仍旧受到天主教思想的影响。所谓“至福”,指的是天主教的“至福”或称“真福直不雅观(beatific vision)”。真福直不雅观,作为一个天主教用语,指对上帝的直接认知,只有完备净化的灵魂才能够面见完美的天主。
对“vision”(景象、异象、幻象)的追求,在“垮掉的一代”那里成为了对精神追求的代名词。这是一种灵魂得到超越,进入永恒体验的圆满境界。处于这意识状态之中的人能够“瞥见”超越时空的人与事物,在短韶光中产生一种物理韶光停顿、物理空间消逝的觉得,头脑中涌现一种超验的景象。在霎光阴,时空倒转,过去、现在、未来的界线消弭,顿然产生当劣等于永恒的感知,他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是超越时空的永恒的一个部分,这使得他处于一种“狂喜”、“极乐”或称“心醉神迷”(ecstasy)的状态。
“景象”的产生靠的是直觉的体验,它的基本意思是指人分开理性状态,处于一种受单一感情(常日是极度喜悦)掌握的状态。而在宗教体悟中,它便是一种与宇宙无物合一的精神(心灵)体验,也便是凯鲁亚克所谓的“至福”状态。
“垮掉的一代”对这种超现实的、宗教启迪式的“景象”的追求,最早见诸金斯伯格的“布莱克体验”。1948年夏,金斯伯格在纽约哈莱姆居住的公寓里读着英国墨客威廉·布莱克的《啊,向日葵》,溘然间他仿佛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吟诵这首诗。在恍惚中,他瞥见布莱克穿越时空的界线向他说话,而他则变成了向日葵:“我觉得全体宇宙成了充满了光、天使、互换和信息的诗,我的头顶彷佛被炸开,让全体宇宙的统统同我的头脑联系起来。”
不仅仅是金斯伯格痴迷于“景象”,在凯鲁亚克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佛教、爵士乐、性与毒品都成为“垮掉的一代”得到“景象”的手段和办法。《在路上》中的迪恩在博普爵士乐和性爱中到达了“极乐”,《达摩流浪者》中的雷·史密斯在佛教修习中到达了“极乐”。当然还有《在路上》中的那句名言:“一起走下去,我知道会碰着姑娘,会有奇景异象,会有统统;一起走下去,明珠会交到我手上。”
“垮掉”含义之三
节拍
“垮掉”的第三个含义是“节拍、节奏、韵律”。不丢脸出,这与“垮掉的一代”喜好的爵士乐有关。
博普爵士乐的精髓是即兴发挥。被称作“即兴重复段”的“riff”,除了把和声作为根本,它没有既定的音乐形式和规范,独奏者的面前没有乐谱,他的头脑中也没有一个确定的音乐目标要去实现,他全凭自己对音乐的感悟、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对现场气氛的把握,来表达一种个人的、情绪的、自由的、直觉的、纯粹的、赤裸的真实。简言之,博普爵士乐的精神便是独创性、自发性、即兴性和背叛性。
“垮掉的一代”从其生活办法、写作的理念和技巧,到作品的主题和蔼氛,无不受到博普爵士乐的影响。尤其是“垮掉的一代”文学的共有特色——“自发式写作”——与爵士乐的影响密不可分。
自发式写作,顾名思义,便是让思绪自发地、不受阻碍地溢出而形成笔墨。不受阻碍是指不受到理性反思和逻辑思考的“加工”,其本色便是自由和真实,正如凯鲁亚克在《孤独天使》中写到的那样:“不要停顿,不要思考,只管写下去,我想听到你发自内心的声音。”同在博普爵士乐中一样,自发式写作强调写作的“即兴性”。凯鲁亚克认为那种即刻迸发的思绪是弥足宝贵的,由于它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是最真实的、最纯粹的。“纯粹”是《在路上》中频频涌现的词汇,它意味着没有受到文化传统“过滤”,它是自然的,是更加富有生命的活力和激情的。相反,当它一旦暴露在理性反思核阅的目光下,它就会被修改、被规范,以至于失落去自己的“本来面孔”。金斯伯格用呼吸的节奏来决定诗句是非的写作手段,也是强调用最自然的、没有理性干预的办法直接呈现原初的思想。
凯鲁亚克后来在《孤独天使》中对“节拍”进行了总结:“统统都汇入到节拍之中——这便是垮掉的一代,这便是节拍,这便是不断持续的节拍,这便是心脏的节拍,它敲击着,敲向全体天下,敲出过去的原形,像是远古期间,奴隶们划着船打出来的节拍;或者是仆人们迁徙改变着纺锤发出来的节拍……”
“垮掉”的归宿
对崇奉的渴求
“垮掉的一代”的核心和本色就表示在“垮掉”这一术语的三重含义之中,它既反响出“垮掉的一代”的生存处境,又反响了他们的极度生活办法,以及在这种生活办法中蕴含的精神追求。
精神的“赤裸”是“垮掉的一代”的基本生存状态。它一方面意味着在一个代价虚无的社会中,他们处于一种精神的“落魄”状态,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他们在空空如也的精神“赤裸”中可以用一颗羞辱和暴露的心灵去追求和创造空想和崇奉。换言之,“赤裸”既是“垮掉的一代”的基本精神状况,又是他们精神追求的条件条件。金斯伯格十分看重“赤裸”或“袒露”,并多次在公众年夜众场合“身体力行”。1959年他在接管采访时曾说:“‘垮掉’的关键是你被弄得落魄到一种赤裸的状态,然后你就能够瞥见一个景象中的天下。”对此,肖明翰教授在《金斯伯格的遗产——探索者的诚挚与勇气》一文中指出:“‘袒露’便是要把自己——包括利用非常的方法——从社会、宗教、世俗不雅观念等各式各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原其‘存在的真实’。”
霍尔姆斯在《这便是“垮掉的一代”》中写道:“关注崇奉的失落落是‘迷惘的一代’的特色,对付崇奉的渴求才是‘垮掉的一代’的特色。”在凯鲁亚克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在路上》中的“嬉普士”的精神“落魄”终于在《达摩流浪者》中的“达摩流浪者”那里得到了精神上的升华,从而达到了精神的“至福”。正如金斯伯格所说,凯鲁亚克向我们表明,落魄(beat)和阴郁是通往至福(beatific)和光明的前奏。在一个短缺真正的崇奉和生活代价,同时又处于生存危急的社会时期中,唯一的出路是相信自己,在生命之路上跟随自己的“节奏”,在极度的生活体验中肯定生命并得到精神的升华,到达“至福”的境界。因此,“垮掉”的三重含义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一个彼此关联的统一体。这便是“垮掉”作为精神的“落魄”和“赤裸”、生命的“节拍”,以及“至福”之境的深刻含义之所在,也是“垮掉的一代”采纳的极度生活办法的一定性和内在逻辑性之所在。
贯穿“垮掉的一代”文学的是在一个代价虚无的天下里探求意义的主题。从一个更加广阔的时期语境来看,“垮掉”精神的“落魄”和“赤裸”便是在代价虚无的天下中人的命运的真实写照。从精神的“落魄”和“赤裸”,到在自由地创造自我中(“节拍”)寻求精神的超越“至福”,这便是“垮掉的一代”的追求的全过程,也便是永恒、不朽的“垮掉”精神之所在。
“垮掉的一代”文化地标
哥伦比亚大学
“垮掉的一代”的开始。
1943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往年有些不太一样,学校的大部分地方让给了海军进行演习,大批年轻男子选择参军从军。哥伦比亚大学的招生数量也因此大幅下滑。在这种环境中,招收进来的学生中,就有一批对国家正在进行的战役毫无兴趣,只是想来听听特里林、韦弗等教授的文学课,同时流连于学校外的街区和酒吧的年轻人。在这一年的哥伦比亚大学,艾伦·金斯伯格和卢西安·卡尔等人相遇,一同参与聚会的还有威廉·巴勒斯、琼·沃尔默、大卫·卡默尔等人。这是“垮掉的一代”最初的圈子。
在圈子的交际中,他们的人脉范围不断扩大,朋友先容朋友,再先容其他大学的同学加入进来。几个月后,凯鲁亚克也加入到了这个圈子中。
科瑞格斯摩尔西115号
琼·沃尔默的公寓,也是在“垮掉的一代”初期男性与女性成员共享的圣地,也背后来的人称为“安乐窝”。
搬到115号公寓居住的琼·沃尔默将自己的寓所变成了派对场。这个圈子里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地来这里,在琼·沃尔默等人的指引下考试测验写作,耐劳,吸毒。在1945年,这里成为了他们心灵港湾。也是在这个地方,琼和威廉·巴勒斯开始同居,凯鲁亚克开始认识尼尔·卡萨迪,各自的人生轨迹开始发生了变革。在当时,不少参与个中的大学生也会选择搬出宿舍,在表面租住公寓。他们选择的地方都是114号或116号——总之都离琼·沃尔默的公寓不远。
巴纳德学院
巴纳德学院是享有文科盛名的女子学院。凯鲁亚克的女友之一、“垮掉的一代”回顾录作者乔伊斯·约翰逊曾经描述,当时的巴纳德女子学院就像一个象牙塔,“校园就像一个城市花园,表面看不出来,除非你走进大门站在墙内,那些墙神秘地建立起一种阔别尘世的错觉”。但随着校外交际圈的扩大,哥伦比亚大学生们的生活办法吸引了原来就沉迷文学的少女们。“垮掉的一代”的女性墨客爱丽丝·考恩也是出身于巴纳德学院的学生。她入学的时候便身穿邪术师一样平常的裙子,气质与这座学院的其他女生截然不同。
在联谊会上,女生们跳起了查尔斯顿舞——一种极为追求即兴与节奏的舞蹈。节拍的和音让两所大学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他们共同模拟着20年代咆哮与叫嚣的传统。此时,这个圈子还没显示出太多与“垮掉”一词干系的迹象。
“城市之光”书店
为相识脱在媒体上沸沸扬扬的“哥伦比亚大学丑闻”,也为了找到朋友尼尔·卡萨迪,凯鲁亚克开始朝着旧金山出发。“垮掉的一代”的最初成员们都希望离开纽约,在迢遥的一侧发掘新的生活,南海岸成为他们神往的所在。
在与卡萨迪来往的几个月里,尚未成为墨客的艾伦·金斯伯格沿着马路闲步,创造了一家在他眼中称得上完美的书店——城市之光。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城市之光书店是第一家只出售平装书的书店。分歧凡响的经营模式迅速吸引了“垮掉的一代”的成员们。
2001年,旧金山市政府将城市之光列为官方文化地标,作为“垮掉的一代”主要的聚拢地,城市之光在本日也成为了追随者们的朝圣之所。
六画廊
本日的六画廊已经变成了一家餐馆,只有门口的一块纪念标牌证明着曾经发生的事情。
1955年10月7日,在旧金山并不起眼的马纳里街道上,艾伦·金斯伯格等人组织了一场读诗会。没想到,当时在一个惨淡画廊中开展的“新墨客之夜读诗会”,会成为美国文化上的里程碑事宜,并由此展开了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
艾伦·金斯伯格在现场朗读了自己的长篇诗歌《嚎叫》,其余参与六画廊读诗会的人还有肯尼斯·雷克斯罗斯(唯一认识所有垮掉一代成员的人)、尼尔·卡萨迪、杰克·凯鲁亚克、迈克尔·麦克卢尔、菲利普·惠伦、加里·斯奈德。值得一提的是,惠伦和斯奈德都是性情极为内向羞涩的人,惠伦的诗歌多以佛陀禅意为主题,加里·斯奈德的诗歌则用词谨慎,偏爱自然风光。但在读诗会上,性情不同的成员们都找到了开释自我的空间。由此可见,“垮掉的一代”并不是人们常日所理解的那样一味癫狂。它以躲避政治,以赤裸办法面对真实自我为终极目的,它所收受接管的人生形式也是多样的。
撰文/陈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