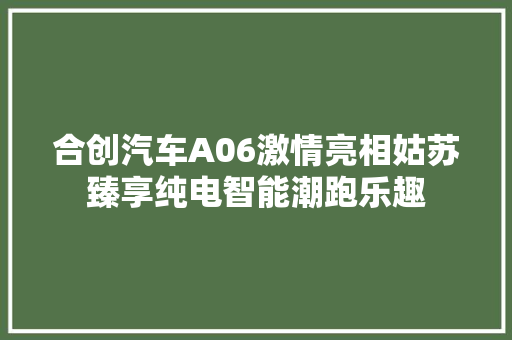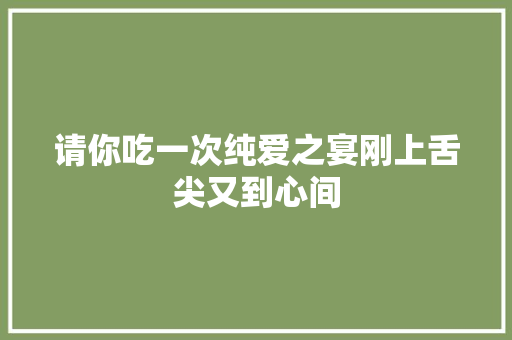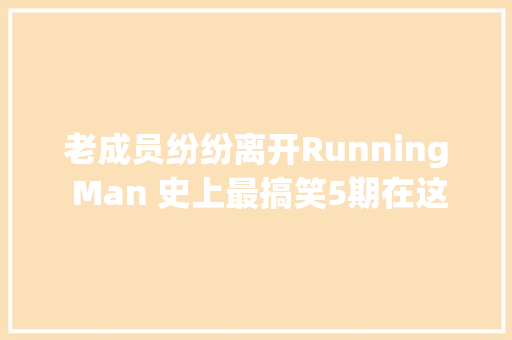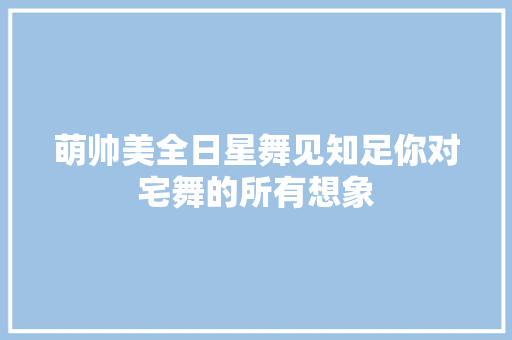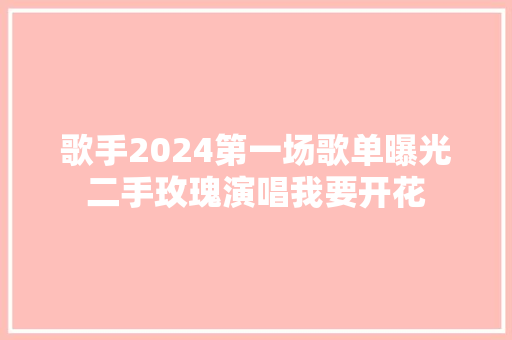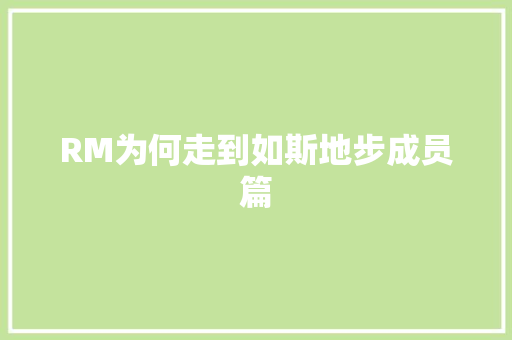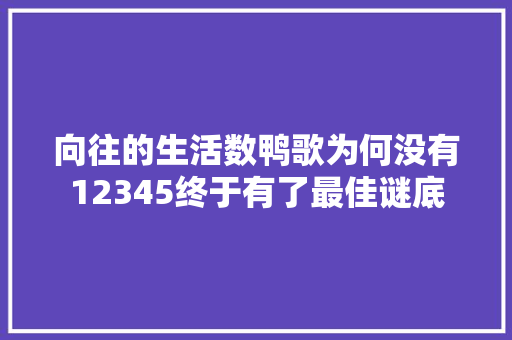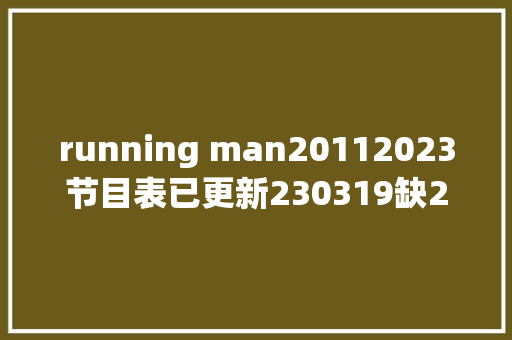各类迹象表明,这个前所未见的“明星没塌节目组先塌了”故事已经不仅仅是综艺界的大事宜。更主要的是,它彷佛昭示着范例粉丝文化的又一次攻城略地和胜利。到底是什么把综艺的不雅观众群体变成了“粉圈”?
不是不雅观众抗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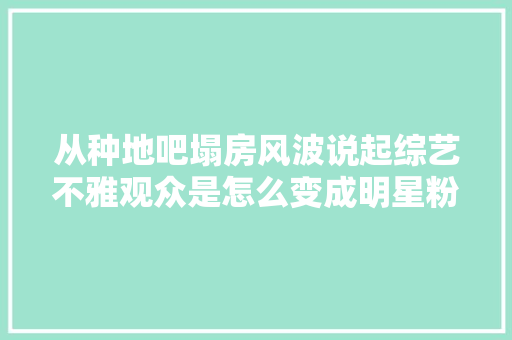
而是粉丝“战役”
《种地吧》是一档讲述“明星下地干活”的节目。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节目组的常驻高朋是十位男明星组成的团体“十个勤天”,他们在节目里耕种运营上百亩的农场。由于节目的立意和内容向来都十分正能量,一贯收成的是社会各界的好评。
风波的起因发生在7月19日第二季的收官日,在末了一期的末了十分钟展现了高朋们的一场会议,会议内容和新人有关。且这个会议跟和前面的场景/内容/感情都比较割裂,有明显的补录之嫌。此外,官方微博发了一条招聘18到30岁男性的缘由,和常驻高朋的哀求匹配,而不是帮忙种地的专家/专业人士。这些举动都让节目组的不雅观众认为,下一季是要招新的常驻高朋来取代或者部分取代“十个勤天”。
事实上,综艺的更新换代是一件非常正常和常见的事。对付已经经由两季的《种地吧》来说,新人的到来不仅仅能够让不雅观众们看到高朋参差的农业水平,重新体验一遍“重新手到老手”的挣扎与努力,还可以在人物关系上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和友情。
《种地吧》(2023)剧照。
然而,这看似存心良苦,有可能带来内容提升的的操作并没有得到叫好,反而激怒了《种地吧》的虔诚不雅观众,他们纷纭采纳行动,取消关注官方微博,在互联网上表达绝不接管任何形式的加新人。此后,节目组和常驻高朋本人接连发声,表达新人加入的合理性,但不雅观众的怒火仍未平息,反而越烧越旺。
公布换人的过程中,节目组自然有很多操作失落当之处,如说话和办法“过于傲慢”,公布信息的人选如果是高朋本人会更得当。但归根结底,双方抵牾的根源在于参演高朋的利益。
“十个勤天一个都不能少”的标语是目前不雅观众最大的诉求。他们纷纭表示自己是男高朋们的粉丝,而不是节目的粉丝,节目能成紧张靠的便是“十个勤天”。换人的行为“就像给初创公司当牛做马累去世累活,好不容易做起来了。结果公司立马就要裁你”;也有人猜想这是“古人栽树后人乘凉”,新来的高朋是“资源咖”,“摘桃子”,来抢走老高朋的资源和镜头。
由此,许多人开始群体性地组织投诉节目,投诉播出平台,乃至跟资助商留言反响。还有甚者开始穷究节目制作组是否是靠这个“赚到钱”了,是否换车换房等,来试图论证高朋只是被作为节目制作方的“圈钱工具”。
这显然已经不可以用“不雅观众行为”来阐明,而是范例的“饭圈文化”。
从“划地”到“圈粉”的
综艺偶像养成
讽刺的是,如今这些“攻击”节目组的粉丝们正好是节目组亲自养成的。
无论在立意上怎么拔高或者狡辩,自始至终,《种地吧·少年篇》是一个“偶像养成”的节目,它的核心看点绝非“种地”,而一贯是“少年”。
节目组一开始选择的高朋便是“少年”,第三季新招聘公告上招聘的18到30岁年轻男性,也是在对标“少年”。
这并不虞味着高朋们只是来作秀或者不用心——他们的至心和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广大综艺不雅观众(80%为女性)便是喜好的看年轻、漂亮、活气勃勃的男孩们。主角如果换成中老年、外表平庸的普通人,这档节目在市场上绝不会受到如此大的欢迎。
为了达成“养成偶像”的目的,节目组可谓打造了一场完美的“综艺景不雅观”:
内容上,节目组冒死呈现出一群近乎无毛病的主角。节目组通过地皮的广阔,“零片酬”的噱头(实际上综艺高朋的收入可以不局限于片酬)、有限的物资创造出了一副堪称“内娱缅北”的景象。而艰巨条件下的他们对社会有极强的名誉感和任务感,少有一己私欲,更多的是团魂,吃苦,拼搏,学习,身上挂满了正面标签。
播出形式上,除了比起其他综艺更长的录播周期,还有频繁的直播,以及团综和演唱会等等形式,可谓是全方位立体式陪伴,培养粉丝的黏性。
更不要说,粉丝们被打上了“禾伙人”标签,与节目内容以及高朋进行深度绑定。只管没有进行公投, “禾伙人”俨然是101中“全民制作人”的另一个版本,为粉丝们带来的是强参与感和造诣感,彷佛这统统成功都“有屏幕前的你一份”。
《种地吧》(2023)剧照。
以上各类标志性的“圈粉”伎俩,本身会回导致养育出的不雅观众是拥有极高情绪浓度的集群化的粉丝。
须要把稳的是,粉丝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大众每每会认为真人秀,尤其是含有直播的真人秀很难造假。一方面,永劫光的拍摄和部分直播让“演绎”变得困难;另一方面,难道这群明星的演技有这么好吗?(如果他们的演技这么好,怎么真正演戏的时候表现不好呢?)
但事实上,真人秀中利用“半真半假”的办法来包装偶像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真实”作为一种养成策略
常年研究东亚大众盛行文化,尤其对付偶像家当有深度见地的日本文化批评家宇野常宽在他的著作《小人物时期(リトル・ピープルの時代)》等分析日本有名偶像团体“AKB48”和“小猫俱乐部”后得到结论,称与其他被严密设定的偶像比较,“AKB48”和“小猫俱乐部”都是通过强调其“业余/素人感”来向消费者们演示其真实和“非假造”的觉得,并取得了成功。
而偶像之父秋元康,正是通过在节目中进行一部分所谓“选拔底细/后台”放送来创造沉浸感。乃至有些镜头会假装是隐蔽摄像机拍摄,来“戳穿”偶像在安歇室的真实面孔,给消费者上帝视角的觉得。有些时候,他们也会额外展现一些无关紧要的偶像小瑕疵,让内容产生真实感,引发更深层的不雅观众情绪共鸣。
宇野常宽认为,这种“半透明”的真实感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小人物”时期的常态,把自己定义为某个类型的人物/角色(即为自己创建的人设)早便是当下应对繁多而不同的社群互换的一部分——我们在(无意识之中)用某种特定的角色身份面对某个群体,就像打出得当的卡牌那样。
也正是在这种“半真半假”的掩蔽之下,《种地吧》的老不雅观众们才会相信一个看似荒谬的结论——这样一群外表精良,签约公司并走上星路的高朋是真的爱地皮,想要长期当农人而不是从事别的演艺事情。
但实际上,所有内容依旧处于制作人掌握之下,无论是从议程、拍摄范畴还是剪辑上,不雅观众看到的都只有他们须要看到的那一部分。
《种地吧》(2023)剧照。
这种类真实天下的仿照就像美国著名政论家、新闻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中所提出“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为了能够对真实环境加以把握,依照简化的模型对真实环境进行重修。而设置得当的综艺就如同一个人类行为与情绪的“实验室”,统统按照导演的哀求运行。不雅观众能够看到镜头里的“十个勤天”在费力耕耘,但看不到镜头外的园地选择、剧情设计、翱翔高朋安排、“外挂”赞助,也无法确定镜头之外,高朋是否全程困在“农场”,是否真的参与了所有种地的流程,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否是真的那么“正能量”,没有妒忌、争抢和龃龉。
更深层的是,不雅观众无法确定他们是否真的收取了“零片酬”,他们参与节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真的纯挚想要吃苦、学习、体验抑或是从各处精良帅哥美女的演艺圈新人中另辟路子,杀出重围。
毕竟,拨开统统被甜言蜜语描述的节目愿景来看,“种地”实在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偶像卖点:他们是明星里最能吃苦刻苦风致高尚的,他们也是种地的人中最有明星相的。粉丝们几次再三夸耀和推崇的辛劳和品质,例如吃盒饭,(相对)简陋的住宿,辛劳的田间劳作……都不过是广大农人的普通日常。而这统统之以是值得被反复夸耀和赞颂,显得那么名贵,正好是由于他们的明星身份。由于他们展现出来的是“明明可以靠脸用饭,却乐意在地里卖力气”。
但,靠“吃苦”和体验“普通人”的职业而红起来,得到大把赞誉和收入的明星,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作茧自缚:
当粉丝开始绑架内容
近几年,由于题材受限,综艺高度依赖招商而受到经济环境影响等等缘故原由,综艺“寒冬”成为业界共识。许多节目为了“活下来”开始走话题路线,即“挂羊头卖狗肉”,并不真正专注于节目声称的内容,而是依赖流量明星或者社会敏感话题来博取眼球。
如一些演技培训类节目,上热搜靠的不是博识的演技和表现,而是靠绯闻八卦、高朋冲突、明星出丑等。这看似“聪明”的做法不仅是在吸血高朋,创造“黑红”的节目口碑,且也将节目和大明星大流量进一步绑定了。由此,一个节目是否能做成,取决于“阵容”如何以及“阵容”适宜不适宜、乐意不愿意“炒话题”,流量明星成为了绝对的话语权掌控者。
而《种地吧》的成功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指明了另一条道路,即通过素人/小明星为主角的节目同样可以吸引不雅观众。
但这场“换人”风波展现了美好故事的另一壁——粉丝和饭圈文化已经显现出对内容进行深度影响和绑架,而与之干系的冲突正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如今常见的事态是,在网络剧/电视剧制作之前,粉丝们就会撕制作组,撕经纪公司/事情室,为自己的偶像挑选剧本,抵制他们以为不得当的演员差错。剧本编写或前期制作阶段乃至播出之后,粉丝们会撕番位,抗议自己偶像的戏份不足,乃至恋爱剧中甜蜜相爱的男女主粉丝都会相互辩论谁的戏份该当更多,谁“偷改剧本”,这到底是“大男主剧”还是“大女主剧”。
在综艺界,这种战火也逐渐燃烧起来。例如23年Angelababy杨颖回归综艺《奔跑吧》(俗称跑男)时,粉丝们创造好不容易回归的杨颖所占片长只有4分钟,另一位女明星白鹿却有10分钟。当时引发了不少的抗议浪潮。
微博截图。
这些征象的共通点是,粉丝们会普遍认为内容制作者/经纪公司/播出平台等对自家的偶像不好,存在悲观怠工、欺凌伤害、资源分配不均等行为,“维权”成为粉丝常见的诉求。
而事实上,这些欺凌的发生频率显然没有粉丝抗议的这么高。尤其是对付《种地吧》这样的节目来说,采取没有名气的新人意味着艺人和节目可以彼此造诣,乃至,从商业角度上来说,还可以涉及到节目制作方参与诸如艺人经纪等后链路收益,可谓是一举多得,节目组绝无“欺凌”高朋的必要。
美国生理学家斯蒂芬·卡普曼曾提出“戏剧三角形”理论,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分别是拯救者、受害者和伤害者。他认为,在冲突情境下,人们内心会不自觉地方向扮演着个中任意一个角色,并合营或勾引他人扮演其他角色。
而越是“养成系”的粉丝,越随意马虎以为自己一步步看顾着偶像的脚步,在精神上是名副实在的“守护者”。在拯救偶像的过程中,粉丝会感到实现了自我代价,一方面保护了“处于劣势”的偶像,另一方面敢于站出来同非正义势力做斗争并表达合理诉求。
于是,正常的内容生产变味了,统统都像KPI(事情绩效)一样是可以被量化的明星造诣和指标:偶像在剧/综艺中涌现多永劫光、站位如何、是被“力捧”还是被“吸血”、是否会得到奇迹上的成功,都是粉丝们考量的工具。
如此逻辑之下,“高朋为内容做事”或者说内容是否好,反而是最不须要考虑的一项——只管所有人实在都该当明白,该当是好的内容和作品来捧出一个个偶像。这,便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困局。它并非一日之寒,也绝非单独某一群体的“功劳”,它既是由向眼球和成本而行的大众文化生产行业所引领,也是由充满热心、心怀憧憬的不雅观众们所打造。
作者/阿莫
编辑/走走
校正/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