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盛行的唐朝,雁门关作为边塞诗的来源地,自然成了诗家竞相咏叹的主题。墨客们有的是到雁门关游历感想熏染过,有的是“虽不能至,但心神往之”,凭借听闻和想象描述边塞的景象。他们或是抒发对功业的渴求、和平的神往和对兴亡的慨叹,或是借助边关景物与战役场面,抒写意象与抒发情怀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诗作描述了关山的险要和边塞的壮景,军旅的艰巨和战役的残酷,既为我们记录了雁门关上的大唐气概,也向我们截屏了大唐时期的雁门气候。
唐代的雁门关,是防御北方的突厥、回纥、契丹等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门户。烽火、狼烟、疆场、厮杀……这些景象始终是年夜方冲动大方的边塞墨客们关注的热点。他们有的是亲历者,有的是参与者,有的仅仅是“道听途说”后的壮怀激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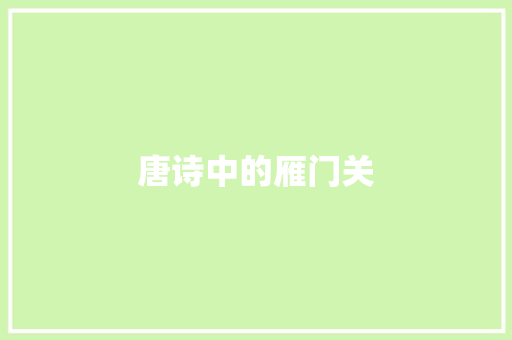
对付那个时期的边塞诗而言,李贺的《雁门太守行》是绕不开的压卷之作,为古今所推崇。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去世!
因众人常按标题误认为诗文描写的是雁门关的战役场景,以是该诗千百年来为雁门关的人文气息与有名度增色不少。实在这首诗作是24岁的李贺约在814年(元和九年)八月前后北游雁门时所作,描写的是唐代名将李光颜在元和年间扫平藩镇叛乱的历史背景,与雁门关无涉。《雁门太守行》虽是古乐府名,但李光颜元和初曾担当代州刺史,李贺以“雁门太守”称誉,可谓一语双关。其时正在潞州(今山西长治)的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帐下做幕僚的李贺未必亲历过那壮不雅观的场景,极有可能是立于代州城头,意象驰骋的遥想之作。
雁门沧桑
《雁门太守行》的同名诗作多以意象取胜,而并非实景描述,但也有例外。比如与李贺同时期的庄南杰所作的《雁门太守行》描述的便是真实发生在雁门关的一场战斗。
旌旗闪闪摇天末,长笛横吹虏尘阔。
跨下嘶风白练狞,腰间切玉青蛇活。
击革摐金燧牛尾,犬羊兵败如山去世。
地府寂寞葬秋虫,湿云荒草啼秋思。
作为一首纪实诗,庄南杰用气度非凡的手腕描述了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发生在雁门关的刘沔战回纥的战斗场景。时回纥一度攻破雁门关,入侵到太原大肆劫掠。武宗命河东节度使刘沔为招抚回纥使,进屯雁门关。气焰嚣张的回纥再次以10万之众入侵云(今山西大同)、朔(今山西朔州)二州,刘沔率兵出关大败回纥,将7裨将斩于关下,回纥大败而归。此战,刘沔不仅击溃回纥,而且将先前远嫁回纥和亲的太和公主(唐宪宗第五女)欢迎入关归朝。
史籍中对此战的记述寥寥数语,而我们从庄南杰的诗文中却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战的伟大声势和场面。由此推断,墨客可能参与或目睹了这一场残酷的厮杀。
“旌旗闪闪”“长笛横吹”写军容之强大,声势之浩荡;“摇天末”“虏尘阔”写沙场范围之广、场面之宏;“跨下嘶风白练狞”写白色战马驰突凶猛可畏,“腰间切玉青蛇活”写宝剑的锋利,寒光如蛇舞;“击革摐金燧牛尾”写金鼓大噪,火牛冲阵;“犬羊兵败如山去世”写战斗过程的残酷,尸横遍野,犹如屠犬宰羊一样平常惨不忍睹;“地府寂寞葬秋虫”写战士的尸体被腐虫吃掉,只剩下累累白骨;“湿云荒草啼秋思”写惨云悲风向众人诉述着战役的惨烈和去世者的哀怨。
墨客以所见、所闻、所感,向我们记录了千年之前的一场决斗苦战。类似这样的决斗苦战在雁门关时有发生、习认为常。以宫词著名的河北籍墨客张祜的《雁门太守行》绝不夸年夜地写出了“雁门山边骨成灰”的景象,为雁门关染上了浓浓的悲情色彩。
城头月没霜如水,趚趚踏沙人似鬼。
灯前拭泪试喷鼻香裘,长引一声残漏子。
驼囊泻酒酒一杯,前头滴血心不回。
闺中年少妻莫哀,鱼金虎竹天上来,
雁门山边骨成灰。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用一首《战城南》则为我们描述了其余一场大战:
将军出紫塞,冒顿在乌贪。
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
雕弓夜宛转,铁骑晓参驔。
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
雁门关旧影之雾锁雄关
公元679年(调露元年),突厥数十万背叛,云、朔二州并为突厥盘踞,唐军屡为所败,边关告急。于是朝廷派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裴行俭率军三十万出雁门关北伐,三十万劲旅,旌旗千里,声势之浩大,唐朝鲜见。大军在雁门关大败突厥,屡战屡胜,将突厥叛乱余党全部平息。高宗李治闻捷大悦,派户部尚书崔知悌为特使代其赴代州劳军。
卢照邻未必到过雁门关,更未必亲历这场战役,可能凭借的是听闻和想象。但墨客的好友魏大的确参与了这场战斗,魏大不仅是卢照邻的好友,也是其余一位墨客陈子昂的朋友。陈子昂的《送魏大从军》即是在这场大战前赠别魏大从军雁门的饯行诗: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
怅别三河边,言追六郡雄。
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
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
魏大是兄弟排行第一,名字等详细资料已无从考证。这首诗不同于一样平常儿女情长,凄苦悲切的送别诗,而是从大处着眼,勉励出征者御边保国,建功疆场,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奋发向上的年夜方壮志。
还有一首赠别诗的主人公与魏大参与的是同一场大战。
北地寒应苦,南庭戍未归。
边声乱羌笛,朔气卷戎衣。
雨雪关山暗,风霜草木稀。
胡兵战欲尽,虏骑猎犹肥。
雁塞何时入,龙城几度围。
据鞍雄剑动,插笔羽书飞。
舆驾还京邑,朋游满帝畿。
方期来献凯,歌舞共春辉。
这首诗是杜甫的祖父杜审言,送给他的好友苏味道的《赠苏味道》。苏味道是唐代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一位墨客,三度位相执掌朝政七年之久,是著名的“模棱宰相”,也是“三苏”的先祖。苏味道从前由于受到裴行俭的赏识,两次北伐突厥,都担当军中管记(秘书一类的文职职员),以是他和魏大一样,也是这场大战的亲历者。
这首诗写于出征前,但已然了若指掌地看到了雁门关的边情——“雨雪关山暗,风霜草木稀。”和一触即发的军情——“雁塞何时入,龙城几度围。据鞍雄剑动,插笔羽书飞。”,更主要的是已经替苏味道预测到了战斗结局——“舆驾还京邑,朋游满帝畿。方期来献凯,歌舞共春辉。”,给人以勉励和振奋。
家在长城下
战役固然是残酷的,但是对付立志报国,特殊是有英雄情结的大唐男儿来说,心有余而力不敷的壮志难酬,才更加叫人惆怅。
以田园诗见长的“诗佛”王维,也写过一首年夜方的边塞赠别诗——《送赵都督赴代州主得青字》:
天官动将星,汉上柳条青。
万里鸣刁斗,三军出井陉。
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
岂学诗人辈,窗间老一经。
诗中记录的是在一次宴席上,一位姓赵的都督即将带兵开拔代州边塞,王维等人为赵都督送行。席间,有人发起分韵作诗生动气氛,王维抓阄抓到了“青”字,于因此“青”字为韵创作了这首送别诗。开头交待了赵都督出征的韶光——“柳条青”的春天;写出了军队的阵容——“万里鸣刁斗”、路线——“三军出井陉”;“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写都督建功边塞的决心;末了一句,赞赏都督的同时,亦抒发了自己亦希望建功立业但却壮志难酬的隐衷。王维济世报国的志向,由此可见一斑。
无论如何,战役都只是和平的插曲。在和平时期,尤其在大唐盛世期间,雁门关也呈现过别样的繁荣景象。
公元730年(开元十八年)至744年(天宝三年)的十余年韶光,崔颢在代州长期担当公务员,可能是从事(主管文书)一类的职务,受到了代州都督杜希望(杜牧的曾祖)的赏识。
崔颢在代州的十余年里,正值开元盛世的壮盛期间,代州地处民族交融前沿,自古战乱频仍,但崔颢见到的却是胡汉和蔼相处的和谐景象。“边民”不仅可以安居乐业,乃至可以歌而忘归。墨客借雁门胡人的歌声,歌颂了开元盛世雁门边塞的民俗民风。
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
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
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
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
——《雁门胡人歌》
而崔颢的好友李颀,在他的约请下,游览了雁门风光后,写下了同样歌颂开元盛世的作品,也写尽了雁门边塞在盛世背景下的壮不雅观景象。
黄云雁门郡,日暮风沙里。
千骑黑貂裘,皆称羽林子。
金笳吹朔雪,铁马嘶云水。
帐下饮葡萄,平生寸心是。
——《塞下曲》
开元年间的著名墨客刘长卿,以五言见长,有“五言长城”之誉。其作品中有《相和歌辞·从军行六首》:
目极雁门道,青青边草春。
一身事征战,匹马同费力。
末路成白首,功归天下人。
倚剑白日暮,望乡登戍楼。
北风吹羌笛,此夜关山愁。
回顾不无意,滹河空自流。
刘长卿赞颂雁门将士为“天下人”太平安宁而“白首”疆场的名贵精神。
还有一类存世量较多的题材是“赠别诗”。送朋侪或上任、或远游、或出征,在表达惜别交情的同时,也截图了雁家声景和边塞风光。
晚唐墨客刘驾,因一位朋侪未中进士,心情忧郁之际,意北游雁门关散心,刘驾作了《送朋侪下第游雁门》以相送。
雁门春色外,四月雁未归。
主人拂金台,延客夜开扉。
舒君郁郁怀,饮彼白玉卮。
若不化女子,功名岂无期。
刘驾的这位朋侪叫李殷,终极考中了进士,并在后唐、后晋官居高位。
同处晚唐的墨客李频的《送边将之雁门》则是为镇守雁门关的边将写的送别诗:
防秋戎马恐来奔,诏发将军出雁门。
遥领短兵登陇首,独横长剑向河源。
悠扬落日黄云动,苍莽阴风白草翻。
若纵兵戈更深入,应闻劳绩得昆仑。
墨客显然对将军出师雁门建功立业充满了期望,并对将军所率的劲旅给予盛赞。既写出了将军行伍的“旌旗”“鼓角”,又写出了雁门边塞“落日黄云动”“阴风白草翻”的秋冬肃杀气候,语气雄壮,浑然天成。
李频送别的这位将军,我们无法得知姓名,但时隔不久,落第后的李频北游雁门关时,与将军再次相逢,写下了《朔中即事》:
关门南北杂戎夷,草木秋来即出师。
落日风沙长暝早,寒冬雨雪转春迟。
山头堠火孤明后,星外行人四绝时。
自古边功何不立,汉家中外自相疑。
墨客由关内至关外,一起上目睹了雁门关南北多民族杂居的社会风情,“草木秋来即出师”写出了自古游牧民族南犯,多在稻熟马肥之秋季,朝廷会在秋季增兵雁门防边,史称“防秋”;“落日风沙长暝早,寒冬雨雪转春迟”写雁北的风沙弥漫、景象寒冷的自然环境;“堠火”指雁门关沿线的烽火台,至今雁门关周边仍随处可见;末了两句是全诗的重点,写出了墨客对战乱不息缘故原由的见地。因将军守边,朝野多疑,同寅排斥,边将不能专务一方,李频以诗作代为陈情,写出了边将的苦闷心结,实在这又何尝不是历代守关边将的同样宿命!
即便是没有战役,雁门关在世人的印象中也总是和肃杀、苍凉、困苦交织在一起,以是对付本就多愁善感的失落意文人而言,雁门关彷佛是倾泻离愁别绪的最佳场所。
50岁才考中进士的墨客许棠,在47岁那年(公元869年),慕名拜会在大同军幕供职的马戴时经游雁门关,作了《雁门关野望》:
高关闲独望,望久转愁人。
紫塞唯多雪,胡山不尽春。
河遥分断野,树乱起飞尘。
时见东来骑,心知近别秦。
由于当时的许棠考了20多次却屡试不第,终日为功名奔波,家境困难,落魄潦倒,常常靠好友接济。听说马戴喜交文友,前往投奔。路经雁门关时,许棠登关独望,看到的是朔雪厚积,断野飞尘的肃杀景象,虽已是早春,但边塞的春色却依然带着寒意,偶尔有巡骑经由,更添孤独之感。雁门关的景象抒发了“愁人”的繁芜心绪。
晚唐著名墨客罗隐同样热衷功名,生逢浊世,十次赴考,未中一第,史称“十上不第”。约在859年(大中三年)—870年(咸通十年)间,落第游晋时,夜登雁门关城楼,感慨而作《边夜》:
光景漂如水,生涯转似萍。
雁门穷朔路,牛斗故乡星。
句尽人谁切,歌终泪自零。
更阑回顾算,何处不长亭。
罗隐以漂流不定的浮萍自比,感叹光阴如流水而逝,自己背井离乡,却难觅知音,报国无门,不禁泪洒雁门,大有英雄末路之叹!
提及唐诗,李白是绕不过去的人物,自号“五岳寻仙不辞远,生平好入名山游”的“诗仙”对付雁门关这样一座北塞名关自然也没有错过。
公元737年(开元二十四年)八月,李白在好友元丹丘的约请下,游历了雁门关。当雁门将军带李白和元演出关打猎,将军跨上战马带着猎鹰,架鹰捕猎。只见将军的飒爽白鹰冲天而起,敛翅而下,猎得兔子便骄傲地献给立时主人,然后又乖乖地蹲立将军的肩头,静候再次奉命出击。持续几次,每发必中,这样的场景令头一次见这阵势的李白惊呼了起来:
八月边风高,胡鹰白锦毛。
孤飞一片雪,百里见秋毫。
兴致极高的李白立时口占出这首五绝——《不雅观放白鹰》,赠与雁门将军,作为雁门之行的回报。
一次匆匆游历,“诗仙”的身影和诗句永久留在了雁门古关,而雁门雄姿、塞上风光也给李白留下了至深的印象。难怪他在《山鹧鸪词》中,竟以鹧鸪自喻,将雁门关视为心灵的归宿。
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
嫁得燕山胡雁婿,欲衔我向雁门归。
山鸡翟雉来相劝,南禽多被北禽欺。
紫塞严霜如剑戟,苍梧欲巢难背违。
我今誓去世不能去,哀鸣惊叫泪沾衣。
这是李白生平中为数不多的一首寓言诗,用富于戏剧色彩的手腕描述了形象生动的故事情节:一只小鹧鸪嫁给了燕山(今北京北部)的大雁,大雁正准备衔着鹧鸪飞向雁门关的老家,而山鸡野雉都来劝小鹧鸪说:北方的鸟儿们总是陵暴南方的小鸟,雁门关的严霜像刀枪剑戟一样锋利,那里纵使有梧桐树也难以栖息。小鹧鸪屈服了劝告,决心誓去世不跟从大雁,说完后无助地嚎啕大哭、泪满衣襟。
该诗约作于752年(天宝十一年),由于这一年,有人约请李白赴幽州入幕僚。李白到了幽州后,创造了安禄山的谋反迹象。于是满心希望落空的李白毅然回归江南,这一年李白49岁。他怀着忧郁的心情创作了这首《山鹧鸪词》,诗中的李白以鹧鸪自比,字里行间充斥着自己无助的心态和伤心的处境。
李白关于雁门关的诗作不只有自己的游历见闻和心情抒发,也有对边地将士和战情的关注和见地。《古风五十九首》第六篇便是这样的主题:
代马不思越,越禽不恋燕。
情性有所习,乡俗固其然。
昔别雁门关,今戍龙庭前。
惊沙乱海日,飞雪迷胡天。
虮虱生虎鹖,心魂逐旌旃。
苦战功不赏,忠实难可宣。
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
北方的马儿不愿意到南方生活,南方越国的禽类也不恋眷北方的燕京栖息。这些都是遗传习气和长期的生活习气所决定。你看边陲的战士们,以前只是在雁门关一带,如今却深入到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埋葬先人的远远的北方腹地。那里的环境更加艰险,条件更为恶劣,有功却难以得到奖赏,忠实却难以得到宣示,墨客借汉朝李广到去世未封侯的凄凉结局,为戍边将士鸣起了不平。
唐代的乐工歌伎与文人之间默契互助,为诗歌的广泛传唱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一些好诗通过乐工歌伎的“二度创作”,可以成为传唱一时的盛行歌曲。
公元726年(开元十四年),西凉(甘肃)都督郭知远向朝廷供献了一套《凉州宫调曲》,个中有一首《凉州歌》,到了785年(贞元元年),此歌经由乐府加工,再此供献于皇宫玉宸殿,可见这首《凉州歌》是当时宫廷高下的盛行歌曲。
朔风吹雪雁门秋,万里烟尘昏戍楼。
征马长思青海北,胡笳夜听陇山头。
琅琅上口地唱出了雁门关的深秋景象。此诗虽为郭知远所献,但作者却是因“口蜜腹剑”有名的奸臣李义府(公元614年至666年),李义府虽做人差劲,但其文才却不容否认。这首歌词能在其身后百年仍旧成为盛行歌曲,曲韵固然主要,但其文辞也很是关键。
而另一首直接出自歌伎之手的作品在当时也是风靡一时:
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
日旰西山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这是唐朝大中年间(847—860年)浙江绍兴的歌伎盛小丛演唱的《突厥三台》。李讷任浙东廉使时,某夜登上越州(今浙江绍兴)城楼,听见有人吟唱“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日旰西山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歌声激切,让李讷为之动容。召来问询后,得知歌者是戏班供奉南不嫌的外甥女盛小丛。小丛讲所唱之音,是南不嫌教授。南不嫌是武宗期间的宫廷歌手,这首《突厥三台》既是南不嫌教授给盛小丛的,解释是那时从庙堂流传到坊间的盛行金曲。
当时侍御崔元范在府幕,打算赴朝廷任监察御史,李讷于镜湖的光侯亭(在今绍兴)为之饯行,命小丛以歌助兴,在座各赋诗相赠,李讷作了《听盛小丛歌送崔侍御浙东廉使》:“绣衣奔命去情多,南国佳人敛翠蛾。曾向教坊听国乐,为君重唱盛丛歌。”
战役从不单单是男人的事,男儿征戍报国的背后,有多少妇人在倚门守望,有多少家庭在祈君归、望团圆。
“花间派”词人温庭筠创作的《蕃女怨》“雁门沙碛”就另辟路子地关注了战役背后无数征人的留守妇女,表现了妻子独守空房,盼夫安归的思念之情:
万枝喷鼻香雪开已遍,小雨双燕。
钿蝉筝,金雀扇,画梁相见。
雁门不归来,又飞回。
一位妇人倚在窗前等着在雁门关征战的丈夫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却杳无音讯。
碛南沙上惊雁起,
飞雪千里。
玉连环,金镞箭,
年年征战。
画楼离恨锦屏空,
杏花红。
想到了雁门关的环境、景象的恶劣和战事的频繁。冬去春来,杏花又红,闺房却依旧“锦屏空”,读来令人柔肠寸断。
唐诗中的雁门关,既有雄浑壮阔、金戈铁马,又有千回百转、离愁别恨,一次次将我们带回那气候万千的边塞烟云之中......P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