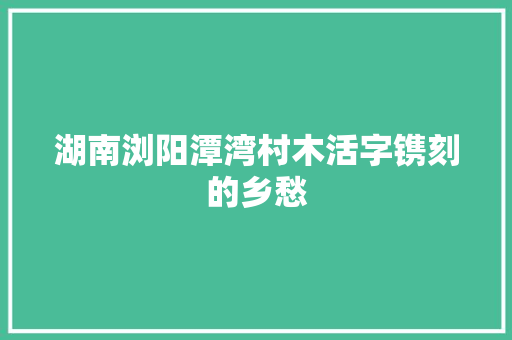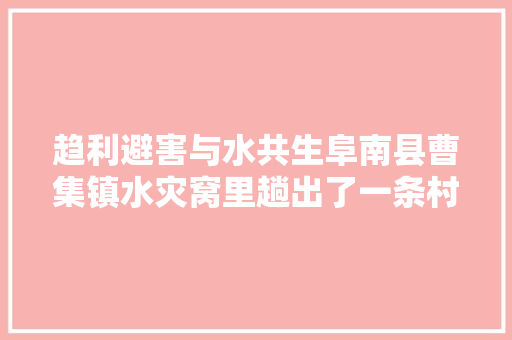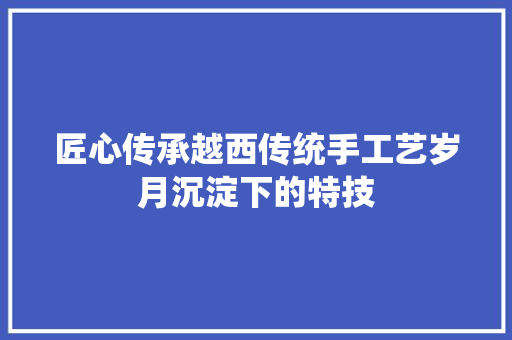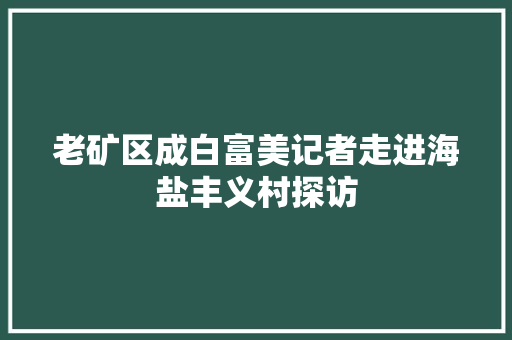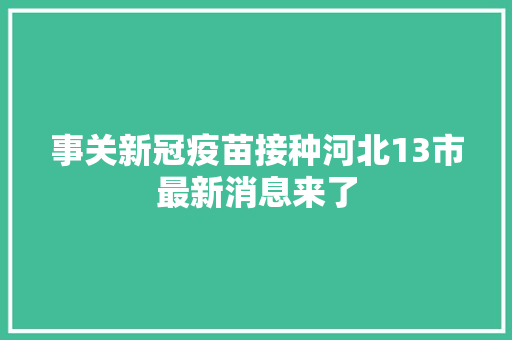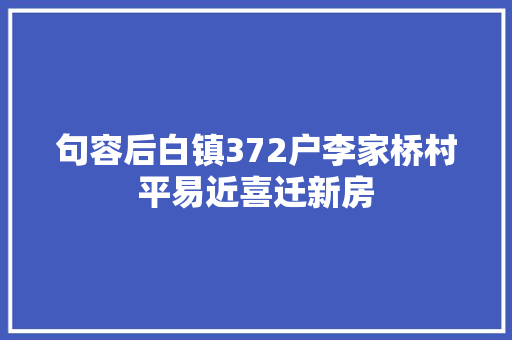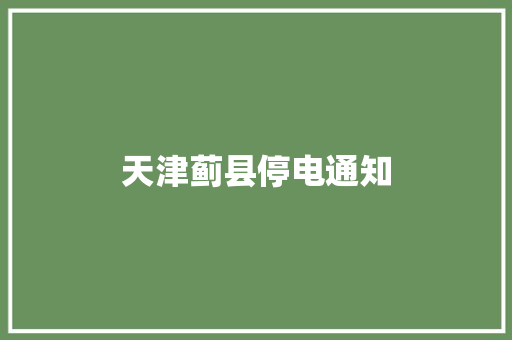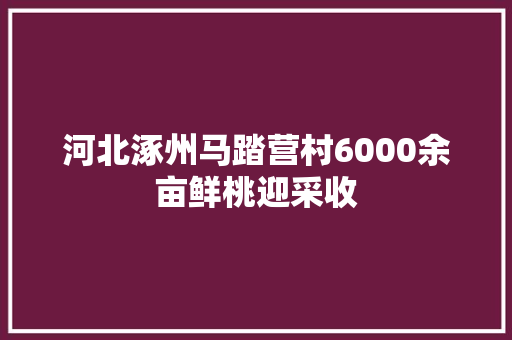海图上找不到的“拥军航线”
六十年、五代船,和平时期的军民鱼水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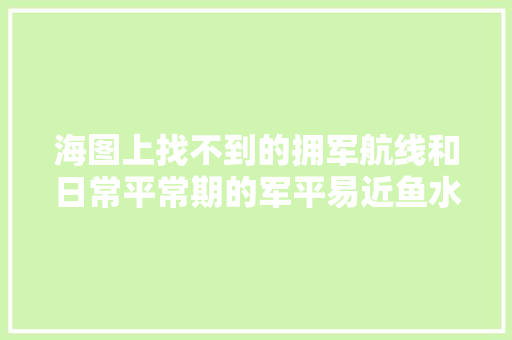
第五任“拥军船”船长钱均堂在驾驶船只。(摄于7月5日)
茫茫黄海的碧波环抱下,苏山岛孤悬外洋,驻岛官兵“与世隔绝”。
间隔苏山岛6.8海里的院夼村落,从1960年开始,就拿出最好的船和最有履历的船长,开辟出一条“拥军航线”,责任帮忙驻岛部队运送职员和物资。
60年来,从最初的小舢板到如今的当代化养殖通知船,“拥军船”的五代船、五代船长“有呼必应”,风雨无阻地航行了近20万公里。
以“拥军船”为纽带,村落民和驻军相亲合作,军民关系坚如磐石;村落集体累计投入拥军资金3000余万元,为苏山岛建成黄海前哨钢铁堡垒供应了主要助力,以无私行动诠释了和平时期的军民鱼水深情。
一条航线
五任船长接力掌舵
时隔4个月,再回院夼村落码头,欢迎刘洪乾的还是熟习的船长和熟习的船。
今年3月转业离开苏山岛之后,这是刘洪乾首次回岛看望战友。跟驻岛时一样,他提前联系好“拥军船”船长钱均堂,乘船上岛。
“这条船是连接苏山岛和大陆的纽带,我们驻岛官兵及家属来往小岛、生活物资的运送,这条‘拥军船’帮了大忙。”刘洪乾说。
一个渔村落、一条渔船,责任分担起驻岛官兵们的保障任务——这份坚持,已经进入第60个年头。
院夼村落党委布告王国明见告,1960年3月,为填饱肚子冒险出海的院夼村落村落民王道伦和王义宽,驾驶渔船在返航途中遭遇大雾和强海流,在苏山岛海疆迷失落航向。没有灯塔指路、没有地方避险。
体力不支之际,村落民们的呼救声被岛上的战士们听到。十几名战士赶到海边,敲响铜锣、挥舞红布勾引渔船靠泊苏山岛。二人被救下后,王义宽发起高烧,官兵们轮流喂饭、喂药,直到他康复离岛。
此后,驻岛官兵又先后救起7名遇险的村落民。“苏山岛来理解放军,解放军是咱的救命恩人”在院夼村落民间口口相传,村落干部专程上岛表示感谢。
登上岛后,他们才创造这个不敷0.5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生活环境十分恶劣,无居民、无淡水、无耕地、无航线,官兵们的补给缺少保障,村落干部们一阵心伤。
“驻岛之初,这里确实非常艰巨。”驻岛连队辅导员张博见告,据连史资料记载,官兵们住的是茅草房,淡水、粮食、蔬菜、日用品等生活物资都须要上级定期用上岸艇进走运输,高下岛也没有日常交通工具;碰着海况不好、物资断供时,官兵们只能吃“海水烙饼”。
军爱民,民拥军,苏山岛的艰巨深深触动了院夼村落。哪能让守岛戍国的解放军亲人缺吃少穿?朴实的村落民们决定为驻岛官兵们做点事情。
“俺们渔家人,最拿手的便是开船!”村落干部切磋后决定,拿出最好的一条渔船作为“拥军船”,专门来回于苏山岛和院夼村落之间,责任供应官兵、支属和物资给养的运输做事,报答官兵们的救命之恩。履历丰富的王道伦自告奋勇成为第一任拥军船长。
“拥军船”的调度归驻岛连队,职员人为、燃油、维修等一应用度都由院夼村落承担。王国明说,只要连队有需求,“拥军船”随叫随到,如今每年来回超过300趟。
每个周五,是驻苏山岛连队例行补给韶光。近日跟随钱均堂来到院夼村落码头。在这里,志愿者们正在将官兵们一周的生活物资搬上“拥军船”。
这批物资里,有饮用水、面条、花生油和10多种新鲜蔬菜,还有院夼村落“夹带”捎给官兵们的带鱼和饮料。看似一马平川的大海上,“拥军船”破浪而行、高下颠簸。不到10公里的路程,却用了一个多小时。
重新颖蔬菜到光伏板,通过“拥军船”运送到苏山岛上的物资,改变着驻岛官兵们的生活。官兵们自己动手腌制的咸菜,曾经是主要的下饭菜,如今成了连队的稀缺“名吃”。
从王道伦到钱均堂,“拥军船”船长已经历了5代;从摇橹小船、小帆船、小机动船、大马力机动船,再到近期刚刚试航的当代化养殖通知船,“拥军船”也不多不少经历了5代。
60载斗转星移、风云变幻,唯一不变的是“拥军船”的名字,沿着这条海图上找不到的航线,日复一日地折返于苏山岛和院夼村落。
“每一代‘拥军船’都是村落里最好的船。”王国明说,刚刚投入利用的最新一代“拥军船”由院夼村落斥资138万元建造,运输能力由8吨提高到55吨,抗风能力由6级提高到8级,装备了GPS和北斗系统双导航系统,基本可以实现全天候航行。
60年来,“拥军船”迎来送往了岛上23任军本家儿官和19任政治主官为代表的驻岛官兵及家属10万人次,累计航行里程相称于绕赤道5周。
一种深情
六十年相濡以沫
登岛时,正值午饭韶光,几名战士亲热地将钱均堂拉进了食堂。
“现在岛上的每一名官兵,大多是泰叔接上来的。”行走在整洁的营区,副辅导员王浩见告,钱均堂小名“福泰”,驻岛官兵们都叫他“泰叔”;上一任船长王喜联,外号则是“岛主”。
苏山岛间隔院夼村落不远,景象好的时候,站在院夼村落码头就能看到苏山岛;苏山岛离院夼村落有时候很远,短短10公里的海程,常常由于大雾、大风、大浪而成为“天堑”。尤其在夜间大雾时,船在岛旁却找不到岛是常事。
随叫随到的五代“拥军船”船长,从没有卫星导航的年代开始,屡屡在苏山岛涌现紧急伤情、病情时驾驶一叶扁舟破浪而至,让“拥军船”成为“救命船”。仅有记录的深夜接送突发疾病官兵及支属离岛就医,就超过50次。
2005年,“拥军船”船长王喜联接到驻岛连队的紧急乞助电话,一名驻岛士官的孩子在苏山岛不慎摔伤头部,伤势严重。岛上医疗条件简陋,孩子须要紧急送医。
当时,海上预报有8级大风,远远超出“拥军船”的抗风浪能力。但王喜联没有丝毫犹豫,来不及加油就带上几名村落民驾船上岛,终于在燃油耗尽前把孩子送到了医院。
或许是习气了一个人开船,面庞黝黑的钱均堂话语不多。2008年担当“拥军船”船长以来,除了一次大病住院,他险些没出过村落。
“我没别的事,便是开船。”他说,不能让部队找不着自己、延误事了。
从一次报恩开始、以“拥军船”为纽带,驻岛连队和院夼村落村落民结下不解之缘,“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的鱼水关系坚如磐石。
1990年6月,时任连长7个月大的孩子在探亲时患上了肺炎,就近在院夼职工医院医治。那段韶光,孩子白天在医院挂吊瓶,晚上就被村落民王进考接到家中照料。在王进考夫妇的悉心照顾下,半个月后孩子规复康健。
两家之间的深厚情意就此结下。连长妻子每到苏山岛,都要去看望王进考夫妇并住上几日。最长的一次,母子俩不知不觉住了70多天。
“连长的工具还帮着我们干农活,像咱自家人一样。”王进考见告。
第一代船长王道伦1997年去世,临终前他拉着老伴连秀珍的手说:“我一辈子最顾虑的便是你和驻岛官兵,我走往后,你要连续替我去看望他们。”老伴含泪应允。
连秀珍老人身体好的时候,年年为官兵们纳鞋垫。如今虽已87岁高龄,视力模糊,可她每年都会委托“拥军船”将家中存放的鞋垫送到苏山岛,用2000多双温暖的鞋垫呵护战士们的双脚。
“我们可以将自己和亲人的生命请托给他们。”张博如是说。
2017年,张博的妻子和孩子上岛探亲,两岁的孩子溘然患上伯仲口病、高烧不退。附近作业的村落民听到岛上的呼喊凌驾来,顶着大风连夜将他的妻子、孩子送上岸。
一代代驻岛官兵,也从未忘却院夼公民的深情厚谊,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回报村落民们的拥护。
“小时候屯子没啥文化生活,苏山岛部队常常送电影到村落里放映。”院夼村落前党委布告王巍岩回顾说,那是他小时候最盼的事情,“跟过年一样”。
院夼村落经济条件不好的期间,渔民上了苏山岛都有好吃好喝招待着;三面环山的院夼村落常常发生山火,王国明见告,只要在岸上休假的官兵听说火情,都是第一韶光赶到现场救火。
院夼村落曾在靠近苏山岛的海疆建有一个养殖场。在养殖场拆除前,参与养殖的村落民长期在岛上和官兵们“同吃同住”。驻岛连队的第一盏电灯是养殖场的发电机点亮,官兵们也常常帮着村落民收割海带。
钱均堂的手机通讯录里,大多数号码是历任驻岛官兵的。他见告,小女儿出嫁,前任连队主官都凌驾来了;他肺出血在威海市住院,连队干部也在周末赶过去探望;术后不到一周,惦记着官兵们的钱钧堂就急着出了院。
时至今日,苏山岛仍在为附近海疆从事海产品养殖的村落民们供应着尽可能的方便:村落民在海上碰着恶劣景象时,有苏山岛的码头可以避风;村落民在岛上过夜,部队也有房间留给他们。
村落里为官兵送戏剧、送物资,妇女专门纳鞋垫送给战士们……荣成市公民武装部政委王志伟说,在持续的互帮互助中,驻岛官兵和村落民亲如一家,驻岛官兵把院夼村落当成第二故乡、将村落民当成亲人。
一份初心
演绎军民鱼水深情
改革开放以来,院夼村落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从一个贫瘠的小渔村落变成了一个富余的新村落庄。“富了海边人,不忘戍边人”,成为院夼村落发展新的座右铭。
沧海桑田,初心不改;航程万里,矢志不渝。
院夼村落的村落办招待所前,有一块刻有“军人之家”的石头。王巍岩见告,过去驻岛官兵和家属高下岛等船期间,都被村落民接到家里免费吃住,从不谈条件和报酬,官兵、家属常常过意不去。1988年,村落里投资300万元建立“军人接待站”,由村落集体接过这部分任务。
厚厚一沓泛黄的餐票见证着这段历史。王巍岩说,驻岛官兵和家属来了,到院夼村落可以直接领餐票免费就餐;招待所开设了军人专用房间,供官兵和探亲家属免费住宿;驻岛官兵来陆地办事所需车辆,安排免费利用;驻岛官兵到村落里打电话一律优先,并且免费;军人和优抚工具求医问诊一律免费……就连院夼村落开在镇里的酒店,驻岛官兵的支属都可以免费入住。
随着营区条件改进和部队管理的日趋规范,官兵和家属须要到村落里吃住的情形越来越少,但至今“军人之家”还发挥着应急保障功能。
在拥军的无偿投入上,院夼村落从未打算本钱。原村落委会主任王宁靖易近等人先容,为保障上岸艇到村落里提取物资,院夼村落建筑了专门的“拥军码头”并两次翻修,累计投入400余万元,可供部队多种型号的上岸艇停靠。
2007年至2009年,驻岛连队培植新营房,院夼村落主动放行重型运输车辆,导致码头道路全部被轧坏,维修用度超过400万元;因部队演习和培植须要,院夼村落拆除了靠近苏山岛的养殖举动步伐,直接丢失靠近800万元……
据不完备统计,院夼村落用于拥军的无偿投入已经靠近3000万元。仅看似不起眼的“拥军船”每年的燃油本钱就已超过20万元。
“这几年院夼村落渔业转型不顺,经济实在不如往年。他们还能这么大力度增援国防培植、支持苏山岛驻军,格外难得。”张博说,苏山岛60年艰巨创业,从零根本发展成为战备举动步伐完备、生活举动步伐完好的当代化、信息化海防前哨,院夼村落的拥军支持功不可没。
韶光的流逝让院夼村落拥军的形式有了改变,但拥军始终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行为准则。当了20年村落党委布告的王巍岩说:“哪一届村落两委班子把拥军船停了、把拥军的传统丢了,便是院夼村落的犯人!”
“院夼村落拥军行动已经沉淀为传统文化和生命影象。”荣成市委布告江山说,它源于胶东革命老区的赤色基因,源于渔民豪迈淳厚的真脾气,更源于党领导下的公民军队的作风优秀,表示了共产党执政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急部队之所需、解部队之所难,对驻岛连队的拥军行动已从院夼村落向更大范围蔓延。副辅导员王浩先容,当地政府出资帮驻军通了市电,正操持新修环岛公路;岛上的空调、电脑、除湿机、冰箱等生活设备,很多也是地方政府或当地企业捐赠的……
说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当年的船长王道伦、王义宽等老一代“拥军人”早已逝去,但院夼村落的拥军情意始终未变,它承载着几代军民可歌可泣的业绩,沉淀为一种拥军文化和一种生命的影象,水乳交融、亲如一家的鱼水深情仍在这片苍茫的大海上延续……(赵新兵、陈灏、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