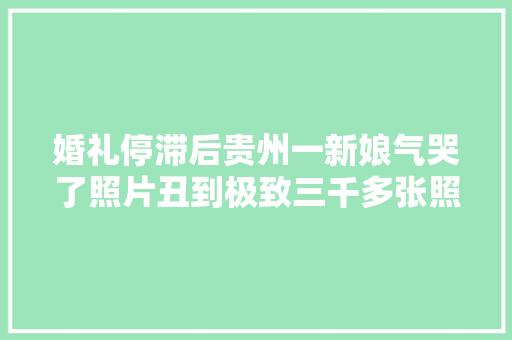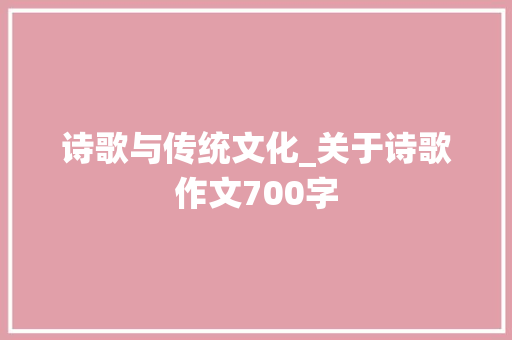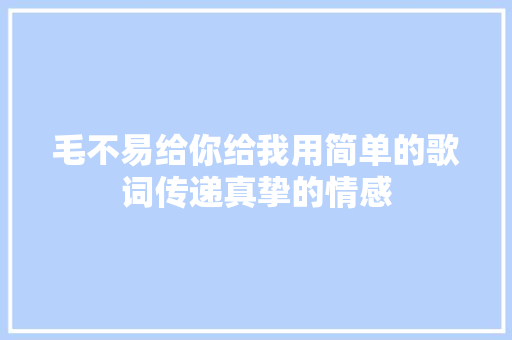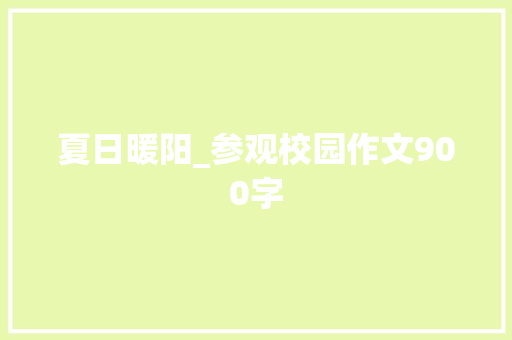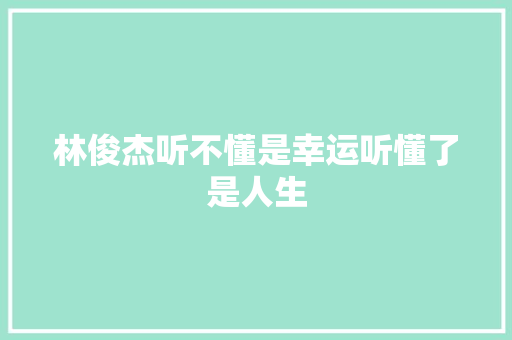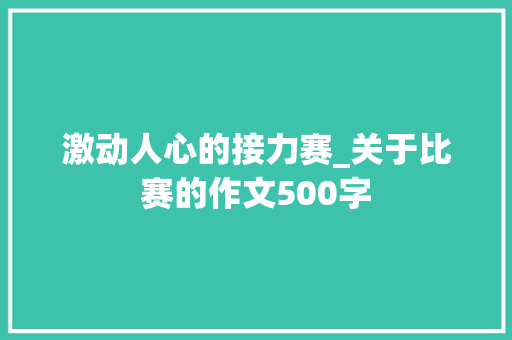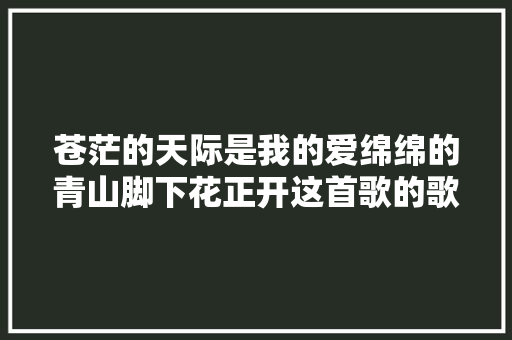那时能人也多,你像现在假如有个什么大型活动的,提前且准备呐,征稿、评比,找个机会演唱演唱,让全国公民听听,别管行家生手的再评论评论。那会儿不介,谁也不知道老人家头天夜里说什么?夜里庆祝完最高指示揭橥后,第二天就有能人给谱上曲子,老师很快就拿到音乐课上教我们。
我们学校就有一教音乐的女老师,也属于能人圈儿里的,自己也为最高指示谱了几首曲子,开始激情亲切挺高,后来说她出身是成本家,被打倒了,没少受罪,我在《我的文革经历》中写过这位女老师。那会儿我虽然岁数小,但也听得出来哪首歌好听哪首歌不好听。刚出样板戏时,我们院儿高音喇叭里每天每的播放,我就特烦,老跟我们院儿的孩子说,这唱的什么呀?真难听!
关键是听不懂。

架不住每天听每天学,到末了你不喜好上都弗成。我到后来,《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险些能从头唱到尾,都成了我的儿时影象了!
便是好多词儿不理解。到了七四、七五年,我们院儿一孩子都多大了?得有十五六了,有一次还特朝气地对我提及《长征组歌》里的一段儿唱词:操!
你说这歌儿编的多泼皮,仇敌眼儿下有眼枪。
我当时没细琢磨过这句歌词儿,但我以为肯定不是这词儿,我说,可能是说仇敌眼下就光瞥见烟枪了,光想着抽大烟了,把打仗这事儿忘了,以是我军才能乘胜赶路程。后来我哥听了一笑说:什么他妈仇敌眼儿下有眼枪呀?人家是仇敌弃甲丢烟枪!
后来这孩子当了。 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常常恍然大悟,奥~那什么什么词是这个意思。
那会儿我们学唱歌都倍儿负责,唱歌能表达我们热爱老人家,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
我们当时还跟大孩子学过《红卫兵战歌》,最爱唱的便是末了一句滚他妈了蛋!
每当一帮孩子玩儿得正欢势的时候,谁假如提出想提前回家,我们就用这段儿送他。后来听说,这是刘辉宣兄为参加一场辩论会前写的,很快就传遍京城。(辉宣兄算得上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我在《听刘辉宣兄讲“九歌”》里有过先容。)
我第一次学的跟文革不沾什么边儿的歌儿是一首扫墓歌儿,翻过小山岗,走过青草坪,义士义冢前来了红围巾,举手来宣誓,献上花圈表决心。想起当年风雨夜,山岗铁镣响叮咚,不是你们洒鲜血,哪有本日的好光景?我们要踏着义士脚印,永久革命向提高!
这首歌儿的曲子挺悠扬,有《让我们荡起双桨》的那个味儿,像小孩儿唱的,不像那种战斗曲。它唱到了山岗、草坪、风雨、叮咚,就以为跟别的歌儿不一样,当时特爱唱。但歌词有所改动,你像把“红围巾”改成了“红小兵”,还有,我忘了。
随着文革的高潮过去,一些老歌翻唱,还有一些新创作的歌儿在电台里开始播放了,你像《我爱祖国的蓝天》、《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之类的。就以为这类歌儿挺好听的,唱起来带拐弯儿,不像原来歌儿似的,唱起来直不楞登的。那会儿唱这类歌儿,一个是以为好听;再一个是以为唱起来分歧凡响,不是在学校里学的。
我真正听到的第一首所谓黄色歌曲是在我十二三岁时。那时我家搬到了民族宫前边儿的一条街的胡同里,鱼找鱼虾找虾,没多永日子我和我哥就跟当地的几个不良少年混的烂熟。实在我所谓的不良少年也便是爱打个架,有时凑一块儿抽个烟什么的;那会儿的有良少年也不怎么学习,有的便是怂,不招事儿,谁陵暴他他就躲着。我不知作别人家什么样,反正我爹我娘彷佛跟我们有种默契,便是我们在社会上不管怎么混?便是别陵暴老人,别陵暴女孩儿,别陵暴小孩儿;别偷、抢、流,基本上就不管。这些彷佛都成了我和我哥生平的原则,我们很少跟我爹我娘顶撞,现在都这样。
那时胡同里的孩子老爱上我家玩儿去,白天我家大人都不在家,他们就吸烟。晚上大人都放工了,他们就拽着我们哥儿俩出去抽。胡同里太窄,又是常年住在一起的老街坊,几个孩子凑一块儿,有大人途经扫一眼就知道是谁家孩子。我跟我哥不怕,我爹我娘跟胡同里的老住户谁也不认识,我们院儿平时别人也进不去;可那帮孩子弗成,备不住就有老街坊跑到他们谁家告状去。以是他们每次吸烟都跑到象来街抽去。
象来街那会儿正在修地铁,路两边儿码的都是大砖垛子,我们就躲在砖垛子后边儿吸烟。我那时小,他们都比我大。我开始不抽,可架不住他们每次都跟劝道的似的,说抽一颗,没事儿,怕抽完了头晕就别往里吸。就这么着,逐渐的我也学会了。没法弄,搁着谁在那个坏境中也得抽,你不抽这帮孙子挤得你,说你胆儿小不敢抽。
大砖垛子后边儿除了我们在那儿躲着吸烟,还有好多躲在后边儿搞工具的。当时我们一块儿吸烟的有一孩子,比我大个三四岁,他一见到有搞工具的就冲着人家那边儿唱,你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偷偷看着我不声响。我开始以为这都是他们瞎胡编的在那儿瞎胡唱呐。后来我哥见告我说,这是《莫斯科郊野的晚上》里的一句,叫他们丫给改了。
有几次我们晚上去象来街大砖垛子后边儿吸烟,被工公民兵捉住了,实在他们紧张是抓躲在砖垛子后边儿耍泼皮的,也便是搞工具的,无意中把我们给勺进去了。教诲了几次,还恐吓我们说,再逮着你们就找你们家去,要不就找你们学校去。吓得我们再也不敢去了。
后来我以为这歌儿挺好听,就开始学这类的歌儿。可词儿和调儿都不是很准,有一天我哥不知从哪儿找了本《外国民歌200首》,他识谱儿,每天一没事儿就在家里照着歌本学唱歌儿。我也随着他学了好多歌儿,像什么《莫斯科郊野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小路》、《红河谷》多了去了。有一次我们在家引吭高歌《喀秋莎》,我爹一声吼: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跟我哥一吐舌头,敢情老头儿听得懂呀。
那会儿学校里对唱黄色歌曲这事儿抓的挺紧,这每每是坏学生的罪状之一,叫老师听见了有时就被带到工宣队去,后来还流传着说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一工宣队的老工人,外地人,说话有口音,批评学生时说:你们老唱着莫斯科郊野的晚半晌儿,张口便是你爱我来我爱你,便是不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后来这都快成了我们的口头禅了,只要谁唱黄歌儿被老师抓到,我们就用这句话批评他。
我上中学时,我们学校和别的学校都传唱着不同的泼皮小调儿。你就听吧,一下课,教室里、传授教化楼的台阶上、操场的篮球架子下,到处都是哼唱的。这类歌儿没什么准调儿,也没什么准词儿,这类歌儿唱出来不是让女孩子脸儿热、心跳、含羞的那种,是让女孩子听了有种受辱的觉得,你像什么你爸爸清晨上班去,你在家里找男地,回家一看斑斑的血迹,你他妈是怎么搞地?还有什么打去世你我要打去世你,打去世你这臭不要脸地,打去世了你往后,我跳进了黄浦江,咱俩一起玩儿蛋去。还有就跟对唱似的:交个朋友是可以地,便是有个小问题,如果有了小宝贝,咱俩一起进分局;进了分局没紧要,你说你是志愿地,小宝贝呀留给你,与我一点儿没紧要......还有好多好多。这类歌儿我从不学,也不唱。我以为太土,是真正的泼皮小调儿,是小地癞子唱的。有些孙子眼睛滴溜乱转,专门盯着人家女孩子唱,倒唱得人家无地自容。我之以是能记住这些词儿,便是由于那会儿在学校里哪哪都有唱的。
还有些孙子瞎胡乱唱,他不是像我似的,有时随意马虎唱错了段儿,他能把这首歌儿唱的差出了国,差出十万八千里,差到姥姥家去。有一孙子便是,唱《俏丽的哈瓦那》,随着英雄卡斯特罗回到了阿尔巴尼亚。这都他妈哪儿跟哪儿呀、谁跟谁呀?
还有一种歌儿我不唱,便是那种太颓废的。我们后来学歌儿都用手摇留声机学,有时家里放着两三台,现在都忘了是从哪儿弄来的了。听的唱片都是那种黑胶木的,三十三转。拿来留声机后我学的第一首歌儿是一老电影《凤凰之歌》里的插曲山中的凤凰为何不飞行,当时就以为这类歌儿听不出什么问题来,内容挺好的。后来找了好多三四十年代的歌儿,有首歌儿就特颓废,歌词大概是红的灯绿的酒,红灯绿酒醉悠悠,无限的创痛在心头,轻轻地一笑忘我忧.......红的灯绿的酒,花样的娇艳柳样的柔......是烟云是水酒......当时那种老唱片听着都有点儿刺刺啦啦的,有些听不大清楚,再一个韶光太长也忘得差不多了。我就以为这首歌儿里充斥着资产阶级腐烂思想,反响了资产阶级腐败的生活,武断不唱!
到七五年旁边出了好多挺好听的革命歌曲,也灌了唱片,但是那种七十八转薄塑料的唱片。我们也买也借,但我们的唱机听不了,磁头太重。把磁头往唱片上方重点儿,扑哧就扎一个眼儿;假如轻轻地放上去,等唱片一转,呲的长长一声儿,磁针就跟唱片上剔起一道儿长丝,就跟刨子刨出的刨花似的,还打着卷儿。那会儿真没少毁自己的和别人的唱片。
后来一帮老知青返城探家,也带了不少他们的歌儿,你像《俏丽的南京我的家乡》、《从北京到延安》等,特殊是《从北京到延安》,流传甚广,不管是从哪儿回来的都会唱,只是把北京或延安的地名改本钱身插队的地名,内容基本一样。实在歌儿里紧张唱的是知青如何赞颂家乡、如何怀念家乡,陈说插队生活如何艰巨之类的。但这类歌儿那时绝对不让唱,老师说是反动歌曲,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还有一首歌儿叫《伴随》,我们院儿一孩子最先唱这首歌儿时,院儿里的好多小孩儿都不理解伴随是什么意思?这孩子就把歌词写了下来,可他把伴随写成了半遂,恰好这孩子他妈那会儿正患半身不遂,我估计他可能也不会写伴随那俩字,就跟他妈的病历上或药方上摘了半遂这两个字。歌里边儿有一句:“失落去了伴随的人生活是苦难的”。
开始院儿里有的孩子还以为是写他妈得半身不遂这事儿的呐,可很多孩子理解不了,说听这歌儿的意思,该当是他妈把他爸抛弃了,“失落去了半身不遂的人”,这歌儿里唱得明明白白!
他妈半扇儿都不能动了,干嘛还要抛弃他爸呐?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大点儿的孩子说,你们丫会断句吗?该当是“失落去了,半身不遂的人生活是苦难的”。大家彷佛是明白了。可还是挺纳闷儿,说他爸没去世呀?也没跟他妈离婚呀?有的说,听这歌儿的内容,估计是在家里他爸对他妈够狠的。咱谁也看不见,他看得见,知道,要不怎么唱得这么情真意切。还真有当面儿问他的,后来等原形大白,他骂人家傻逼!
人家骂他傻逼!
我跟我哥那会儿回老家,屯子的青年也有唱不三不四的歌儿的,虽然里边儿也有哥呀、妹呀的,但都是老戏里的词儿。我们哥儿俩唱的歌儿他们都以为挺新鲜,就让我们教他们唱。冬天,我们就躲在场院的秫秸垛旁教他们;夏天,就躲在“看青”的窝棚里点着蒿子教他们。他们学的倍儿上瘾、倍儿负责。有时邻村落儿演电影,他们就哼着《莫斯科郊野的晚上》、《喀秋莎》这类的歌儿,用眼瞟着过往的姑娘,显得倍儿牛逼!
后来弄得我们哥儿俩一回村落儿,恨不得全村落儿高下传喜讯,奔忙相告,老潘家那儿哥儿俩又回来了!
直到我当了兵,没事儿也老教老兵唱老歌儿。特殊是我回北京后,有时科里开会前或遇上年节什么的,领导就让我唱几首老歌儿。听的时候大家愉快、鼓掌,喊着再来一首;等听完后下来,就有人开始议论了,一看小潘小的时候便是个小玩儿闹。反正不是什么正经孩子。吃饱了就骂厨子,都什么人呀?你说我冤不冤?我九八年回部队,正在办公室里跟人谈天,这是我小二十年第一次回部队。没一下子就来了一帮人,男女全有,个中一位领导说,我来看看大名鼎鼎的潘小京!
几个小女兵在边儿上嘻嘻笑,我听那话茬儿不像夸我呐,都快二十年了。零八年,我回医院办事儿,我到一科室找我认识的一位年夜夫,她不在。她同科室的一位女大夫问我尊姓?我刚说出我姓什么,她就说出了我的名字。她说老有人提我。都快三十年了,不知道他们还记得我什么?大概记住的正好便是那个爱唱“黄色歌曲”的小男兵。
那会儿我跟我们医院里的一俊秀女孩儿搞工具,就有好多人不解,说那谁谁谁那么诚笃一小女孩儿怎么看上小潘了?也有那么几个对我印象好的,就问,人家小潘怎么啦?那会儿恰好有一部电视剧《有一个青年》,有人说,小潘多像电视剧里的那个青年,整天点儿了游荡的。但人挺仗义,挺有正义感。
后来我想买把吉他,可那会儿没地买去,吉他是紧俏商品。八零年,我们后勤部一离休的副部长的儿子,把他那把八成新的吉他十八块钱卖给了我。我带着蛤蟆镜,抱着吉他,更不像正经人了。
没辙!
她就有人喜好这样的。八九年,有一特有文化的俊秀女孩儿特殊喜好我,我问为什么?她说自从看了《本命年》就一下喜好上了我,说我特像里边儿判了刑的那个人。你瞧瞧,有文化的俊秀女孩儿都有个性!
无奈,我那时已经结婚了。那一天、那少女,忽然间化作天仙,从此就像一段珊瑚恋。那女孩很好,悄悄地离开了我。
再后来,就有了邓丽君。我第一次听她的歌儿脸是如何发麻;小王是如何刺激的直要尿裤子,在我的《三十年前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里边儿全写着呐!
(文章来源:京哥讲故事)
阅读往期内容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