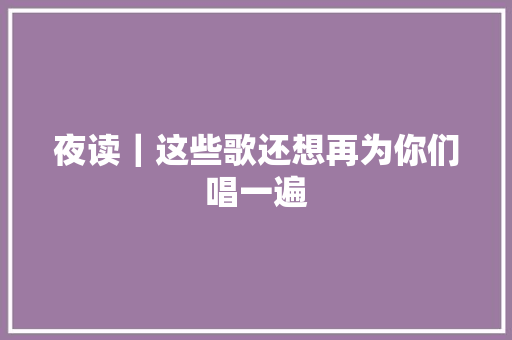写着写着又长了。好吧,献给与音乐、绘画有关的青春,用这十四节。
(一)

罗大佑刷屏那天晚上,我不是没空看。
对我来说,罗大佑是“火车火车行对佗位去”,是“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不是“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也不是“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他是静水流深,偶起浪花,但那时的我们,更多是在滂沱大雨中。同一期间,台湾的忧郁是灰色的,大陆的摇滚是黑白分明的。
那是我们的青春——也不都是,也不是都。
(二)
很多年前,某美术学院一间教室的日常:16个人每人面前一张整开大画板,大家站着画画,四五个小时也不腰腿疼。教室在顶楼,没有空调,汗如雨下,为了不弄湿画面,我们小心翼翼,不让肢体的任何部分打仗纸张,包括手指尖。同学们轮流用暖瓶到卫生间打自来水,再轮流不讲卫生直接抱起来喝。画板挡住了人,只听见一首又一首难听又亢奋的合唱。我们唱郑钧、张楚、窦唯、何勇,唱唐朝、循环、零点、黑豹、指南针。老师也不管。
魔岩三杰,左起张楚、何勇、窦唯
前几天我在车里放郑钧的《甜蜜蜜》,孩子道:“这是什么阴间歌曲?”唉,这首,我是真的喜好。
她倒认可《无为》,这令人惊异。
(三)
抱着暖瓶喝了小半个夏天的自来水,我得了慢性阑尾炎,满肚子乱疼,说不清楚。年夜夫一按右下腹,我:“嗷!
”
很多年后,我终于切了反复生事的阑尾,麻药过敏,还未进入晕厥就溘然呼吸抑制,在我用仅存的意识剖断自己急速要归西的时候,一边在心里抱怨啧啧啧去世得太丢脸,一边有隐约的音乐穿时空而来。
那是我们的青春——也不都是,也不是都。
当年的循环乐队
不久前,我在车里播放《烽火扬州路》,第一句便是嘶吼“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跟孩子讲,这是29年前中国摇滚顶峰期间循环乐队的作品,即便放在现在,这种水平的重金属依然是国际范。
《烽火扬州路》还有个用途是帮助我们背诵古诗词,清晨好,辛弃疾。
(四)
彷佛有个规律,学美术的爱音乐,搞摇滚的爱画画,新裤子乐队好几个人都是画家。
那时候,我们看电影就不仅仅看剧情、看演员了,还热衷于剖析配乐、舞美等其他项目,就跟奥斯卡评委似的。我们仔细地看序幕上的制作名单。《红河谷》上映时,买不到好位置,大家坐在第一排梗着脖子看完了,估计我的左眼外斜能增加好几度。我们创造编剧、导演、拍照、音乐……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冯小宁,就崇拜得弗成。那个钢琴配乐到现在都记得,犹如“007”、《加勒比海盗》《末了的莫西干人》《泰坦尼克号》《菊次郎的夏天》一贯到后来的《指环王》乃至“魔兽”的配乐,都刻在了鼓膜上。
《红河谷》,被俘的宁静笑着唱祝酒歌,藏语,什么拉索什么拉索的,把我唱哭了。不过我说的配乐不是指这个。
有个同学见告我,他学音乐的朋友为了保护声带,从来不吃瓜子。不知道为啥,到现在我一吃瓜子就想起这事儿,担心会不会坏了嗓子。然后连续吃,吃成了瓜子牙。上周看牙医,问可不可以把我那颗瓜子牙磨平了,年夜夫谢绝了。
我属兔,但不一定具备啮齿类动物的本事,比如牙可以磨了又长,长了又磨。
(五)
磁带封面
那时候唐朝乐队的张炬已经去世了,我们买了盘磁带叫《再见张炬》。他去世时25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我们不理解他,也无法想象那一晚,全北京的摇滚人都出动探求闹事车的场景。唐朝乐队我以为最有觉得的不是《梦回唐朝》,而是《国际歌》。乐队创立者丁武,2010举办了个人油画展,这个值得赞。
丁武
对任何一种事物,我们都很难通盘接管,我尤其不想看到扎着马尾穿着花裤衩的胖男人在舞台上弹着贝斯蹦跳。
中国新摇滚是如此鲜活、如此刺目耀眼,以至于那时候,国外乐队的光都很难照进来。有个一贯怀旧、坚持听披头士的人,他是贾宏声,演艺、成名、吸毒、悔悟,赞许张扬给他拍自传电影。那部电影叫《昨天》,他的爸爸妈妈演他的爸爸妈妈。当看到爸爸被儿子逼着穿上紧得不能再紧的牛仔裤,去音像店买披头士磁带,怎么也说不清名称时,我的心碎了。2003年旁边,我恰好做一个影评栏目叫“碟碟不休”——影碟的碟,曾经用当时浅薄而全部的认知写过这个电影。2010年,贾宏声自尽了。
贾宏声自己,也不会希望世上有第二个自己。
这险些是能找到的唯一一张贾宏声的笑颜
(六)
很多年之后读了一篇洛兵所写有关罗琦的长文,忍不住又把《回来》《选择倔强》《我没有远方》找回来听了又听。《我没有远方的》的前奏是《草原上升起不落地太阳》。绝不夸年夜地说,罗琦当年的嗓音,至今无人匹敌。华语盛行歌坛中,张惠妹、苏芮、黄绮珊和张韶涵算爆发力比较强的,但罗琦才叫真正的炸裂。“当灵魂迷失落在苍凉的天和地,还有末了的倔强在支撑我身体。所有停下的风,所有破碎的梦,都奔向烈火的怀中,对我说,当灵魂赤裸在苍凉的天和地,我只有选择倔强来拯救我自己,所有奔驰的风,所有猖獗的梦,全都在痛楚中复活了我的心。”不得不说,词曲者洛兵真的厉害,也真的懂罗琦。
唱《选择倔强》时,罗琦即是去世而复活,只是那只左眼,永久也找不回来了。
当不可避免地经历人生中的挣扎时,当久病不愈精疲力尽时,我开车唱罗琦,唱不上去,唱到咳嗽,唱到哑。很治愈。
(七)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一个人,本来可以成为内地女摇滚中的一团烈火、一杆大旗,然而她主动退隐了。尊重她的个人选择。但我永久忘不了她似男似女理着短发穿着花衬衫闭眼抱着麦克风唱《爵士鼓手》:“勇往直前的鼓手,不屈不挠的爵士鼓手!
”她是毛阿敏。那首歌现在很难找了。我听她歌的时候用的随身听,电不敷了会变成老头目的声音,可吓人了。过了一些年,她涌如今央视春晚,一身黄裙优雅地唱《思念》,表情自持、动作舒缓,我是接管不了的。
(八)
是的,那时候我们不唱罗大佑,由于有更震荡、更直接、更靠近那个年事内心渴想的东西,也跟经历有关。并且有些时候,人拿不了太多的东西,只能取舍。如果重来一次,我会选择都要。
当我给孩子放鲍家街43号的《小鸟》时,她大致以为我是在行刺她。二十六七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乐队,那个戴眼镜、头发有点长的主唱一开嗓,我就愣住了。我跟同桌说:“现在所有的乐队中,这个不算突出,但我以为这个最有未来,他们想法多,比较高等。那个主唱,他唱歌的时候,站得很稳。”
那个乐队2000年就终结了,但是主唱一贯生动,他是汪峰。
(九)
年轻的张楚和现在的张楚
快大学毕业的时候,难免大家彷徨。我们重新又唱“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张楚是个面相又丑又纯的人,那种冲撞感让人难熬痛苦,无法形容。我们更喜好他的“蚂蚁蚂蚁蚂蚁蚂蚁蝗虫的大腿,蚂蚁蚂蚁蚂蚁蚂蚁蜻蜓的眼睛,蚂蚁蚂蚁蚂蚁蚂蚁蝴蝶的翅膀,蚂蚁蚂蚁蚂蚁蚂蚁蚂蚁没问题”,也不知道啥意思,就以为轻松开释,一唱就笑。《蚂蚁蚂蚁》收录在《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里面,我们不太懂也不太认同这个专辑名,孤独为啥可耻呢?
但这很酷。
实在早在高中,有的同学就已经在唱《无地自容》了。在学校里,打仗最前沿音乐的总是美术生。呃……我彷佛对更偏盛行的零点乐队不太有兴趣。这些年有时在电视上看到当年的主唱周晓鸥,常常演个坏坏的或者搞笑的配角,就跟腾格尔一样没有偶像包袱,挺好的。
周晓鸥演坏人很不错
(十)
大学时除了听摇滚,我们还听喜多郎和Enigma的纯音乐。尤其Enigma的《谜·西元一九九零年》,是从未见过的音乐形式,神秘悠远,美且诡异,彷佛故意与人的听觉习气进行对抗。有个男生表示听了难熬痛苦,说,怎么一那个一那个的。
喜多郎这个日本老头很迷人
《谜·西元一九九零年》磁带
我们竟然都明白“一那个一那个”是啥意思,反正是介于惊艳与受罪之间的一种间歇性的、强烈的不适。20多年后,孩子让我听lost rivers,苍天啊,这才是真的不适,我魂都吓掉了。
我们乃至还听过一阵子《笑脸》,并不在乎谢东长得丑。只是溘然有一天完备抛弃了他。印象深刻的还有两首恐怖的歌,《孟姜女》和《杜十娘》,不说了,提起来就以为在侮辱自己。
后来有了个词叫“口水歌”。
我永久谢绝口水歌,并非自命清高。而是,本来生活中大部分声音都已是聒噪,如沿街犬吠、蚊蝇哀鸣,重复地听更聒噪。我有个本事,在一大群谈天说地的人里面呆着,可以自始至终听不到他们在讲什么。
耳朵可以分辨好听和不好听,也可以选择听或不听。
(十一)
必不可少的还有高晓松,我们反复听他《青春无悔》那盘磁带。尤其他给顾城写的三首歌,《白衣飘飘的年代》《玉轮》和《反应》,由叶蓓和老狼演唱,刻骨铭心。
“大雨如注,风在林梢,海上舟摇,楼上帘招。你知道他们终于来到,你是唱挽歌还是祈祷?有一天孩子们问我,那本书写的是什么?我说什么我说什么!
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唱起了歌,我唱起了歌!
”——《玉轮》
高晓松(右)和老狼
我们也听老鹰乐队,乃至有几个同学在教室门上贴了张纸,写着“一高事情室”,一高谐音eagle。那张纸被辅导员熊了一顿撕了。很多年后,老鹰乐队的《加州旅社》依然是音响店的紧张试音曲目。听见时会容身,想起一群年轻人围坐,一点一点愉快地剖析里面乐器搭配。多么纯挚的好光阴。
(十二)
我们很少听罗大佑。他真实地唱出了当年很多人的无力,以及淡淡忧伤下的小美好,但不知去世活的我们选择破碎、倔强、奔跑、回来。
我们也很少听崔健。缘故原由无非是,我们太小了。老支见告我,崔健在省体育馆开演唱会的时候,他进不去,站在高架桥那里听,很多人都在体育馆表面站着听,随着唱。和对待罗大佑的态度不同,当我们上了一点年纪,再转头,果真不可避免地被崔健击中、打倒了。而罗大佑,过去了便是过去了。大约跟地域也有关系,生在粗放的北方,变革冲撞的大陆,更接管北系音乐,里面很多符号乃至暗示都比较随意马虎明白和共鸣。
没有踩低罗大佑的意思,这只是某个时期某个群体的真实经历和感想熏染。或许在某些关键点,我们遗憾地错过了他;亦或者,我们这批物种真的迥于众人。这一次,由于罗大佑的提醒,我影象的潮水溘然翻涌,很多事连自己都忘了原来都没忘。感谢他。
(十三)
毕业设计展结束后,我们的作品被搬回教室。不知道谁先动的手,它们被瞬间砸了个稀巴烂。我实在是心疼的。高中毕业撕书,大学毕业砸作品,愤怒的工具又是谁呢?窦唯《高等动物》里那些词汇,年轻的我们只懂字面,在体内冲撞导致疼痛的,只是无法掌握剂量的荷尔蒙。待到中年、趋近老年,看了太多又挨打太多后,懂了那些词,我们又不说话了。
年轻的窦唯和51岁的窦唯
设计专业的学生会经历一些尴尬,明明苦苦地画了那么多年,头破血流考进美院,末了却可能成为一个不画画的工薪族。考学前或者在校时的奇装异服、夸年夜举止都逐渐消逝,该干吗干吗,但与音乐的链接却不会断。
大学毕业三四年后,我在报社当娱记、做编辑,并连续兼做版面设计,个中有项事情是一周三篇影评。感谢大学时期奥斯卡式的看电影习气,也感谢妈妈海量的藏书让我自幼阅读。又过了一些年,我回到与艺术本身更近的地方,做字画宣布、评论和编辑。如此甚好,在我眼里,世上的东西加倍大略,不是画便是歌。
没那么随意马虎,也不是消遣,都是有丑有俊、有悲有喜。
(十四)
后来看一些国际音乐节的演出,嗑药症状明显,就光彩自己经历了多么好的时期,那时的中国重金属,不是纯挚的发泄式嘶吼,而是有文化、有批驳、有旋律、有理智、有技能含量和审美追求,且充满了信心和愿望的,是大格局的,我们听《梦回唐朝》和《烽火扬州路》,知道他们歌唱的是盛世,关注的是家国,正能量。
他们老了之后回顾往事,大约会有几分羞涩,为当年的稚子冲动、大略粗暴,但多数不会后悔。
唐朝乐队
我们喜好摇滚,也乐意听眇小的声音,听风、听雷、听心,听天下也听自己。我们喜好看画,看山、看水、看心,看人间也看结局。
罗大佑回来了,我们也老了,反而可以像普通朋友一样看他、听他,问他还想去哪儿,再一起带着眼睛和耳朵上路。路上不是画便是歌。
壹点号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