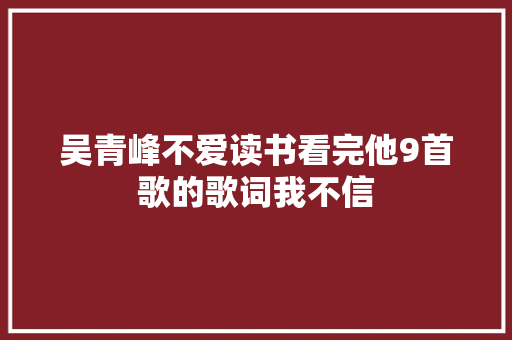上世纪50年代,这部音乐剧最初的作者戴尔·沃瑟曼(Dale Wasserman)在动手创作一部《堂吉诃德》改编作品时就定下了调子,他认为小说的构造很明确:一个总把一样东西算作另一样东西的企图症老头的故事,而他在个中创造了作者塞万提斯的影子。同样出身底层,投身行伍,即便命途多舛,也没有丧失落乐不雅观又正派的骑士精神。于是他决定将两者的形象领悟,写一个塞万提斯和他笔下的堂吉诃德的故事,“用塞万提斯创造的文学人物来表达他的精神——他的勇气、他的诙谐和他对抱负是生命存在根本的信念”。
这种戏中戏的形式源远流长。在塞万提斯之前的莎士比亚,就已经闇练将其利用于创作中——为角色构建一个平行天下,在个中寄寓角色的意图,推进故事的戏剧性进展,想象性地办理现实中的难题:《哈姆雷特》中王子自编自导了一场“捕鼠器”戏中戏在御前上演,这是试探叔父与母亲的“机关”,要从他们的愠怒和惶恐中证明他们的罪过;《仲夏夜之梦》中公爵夫妇化身林中的仙王仙后,借用乱洒爱情花汁的癫狂梦境来重整现实中的雅典秩序,叙事也在真实与梦境的切换中推进。《堂吉诃德》中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戏中戏”,然而主人公时而复苏,时而疯癫,时而是没落贵族阿隆索·奎哈纳,时而是他抱负出来的游侠堂吉诃德骑士,变换的身份也形成了一种近似戏中戏效果的互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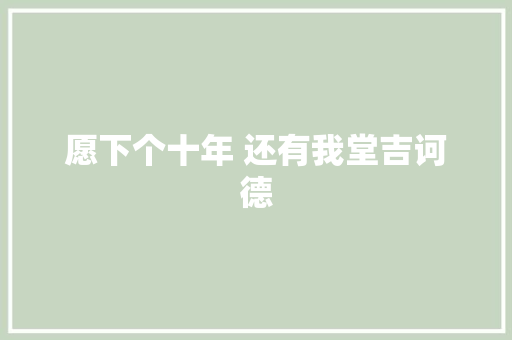
这是莎士比亚时期更为青睐的戏中戏形式,它是向内的、属于剧中人的,而沃瑟曼在《我,堂吉诃德》中嵌套的戏中戏,是作者和他的角色之间的互文,这也是现当代剧作家更自觉利用的关系形式——我们本日会意识到并且指明,莫扎特便是唐·璜,塞万提斯便是堂吉诃德,这种将更多的指涉投向外部文本的优胜之处在于文本的语意如层层荡漾一样平常层层外扩,再想想沃瑟曼对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精神的认可吧,从剧本中的这段台词里我们也容许以理解他的致敬——
公爵:你们诗人为什么都那么喜好疯子?
塞万提斯:大概是由于……我们太像了吧。
公爵:你们都不肯面对现实。
塞万提斯:我们都会选择现实中让我们快乐的部分。
沃瑟曼对《我,堂吉诃德》的意旨如此明晰武断:讴歌而非娱乐,因此让这部出身于1965年的音乐剧具备了独特的气质,年轻的词作者乔·戴律昂(Joe Darion)充分虔诚原典,险些所有的歌词都是从戏剧文本中直接扩展出来的,这在当时仍算创举。戴律昂一眼就意识到《不会成真的梦》(The Impossible Dream)是全体剧的关键词,是“不雅观众对这个角色从笑话到共情的关键点”,故而环绕着这个进行扩写。顺便提一句,剧中唯一一曲全新创作《小鸟飞》的灵感源自一则舞台解释,旋律轻快,很好地勾勒了底层骡夫们游荡快活的气质。曲作者米奇·李(Mitch Leigh)广泛采取了气质上旷达自由的弗拉明戈曲风,这在故事发生的期间、16世纪的西班牙并非主流;《不会成真的梦》自然是那首经典大歌,这次《我,堂吉诃德》10周年纪念版返场彩蛋中也播出了天下各地艺术家演唱的版本,从盛行歌手珍妮弗·休斯顿到百老汇男星乔什·葛洛班,从法剧“老航班”洛朗·班到中国音乐剧演员郑云龙……你可知它的传唱之广。
当然还要说一说制作。作为10年前初入戏院,刚好遇上了《我,堂吉诃德》英文版在今已不存的木马戏院里上演,彼时导演约瑟夫还在台上扮演着堂吉诃德,我眯着眼看模模糊糊的竖屏字幕条,“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在简陋而漆黑的小环境里十分贴切。经历中文音乐剧市场从无到有的10年,《我,堂吉诃德》升级大戏院制作,地牢与天梯的逼真实景,带着做旧工艺的讲求衣饰;个中一组演员阵容,饰演堂吉诃德的刘阳和饰演桑丘的卞佳平都是2015年中文版的首演卡司,对角色把握的进步有目共睹;中文翻译采取半文半白的形式,来匹配原作中塞万提斯的普通口语和堂吉诃德文绉绉的古英语,韵律亦十分风雅千锤百炼。
“他要不是世上最睿智的疯子,便是那最猖獗的智者。”《我,堂吉诃德》仍有的异质感是什么呢,不是来自于空想主义在现实天下中总有的不合时宜,而是空想主义者所讴歌的空想和聪慧是否真的完美无瑕、经得起考虑。实在,从这一版制作的预报片来看,已经模糊约约提及了阿尔东莎的视角,但我以为还不足。堂吉诃德至去世不承认阿尔东莎是阿尔东莎,至去世希望阿尔东莎接管自己的新身份杜尔西内亚,这就很有问题——该当是堂吉诃德承认阿尔东莎的身份,承认身份的低微,不妨碍灵魂的崇高与自由。
在时期中前行,《我,堂吉诃德》或许到了该有所颠覆的时候,这种做法无愧于一部精良作品的伟大。下一个10年,希望《我,堂吉诃德》依然还在,证明依然被讴歌的空想主义,而下一个10年,堂吉诃德也该当意识到复苏与疯癫的临界点可以再提高一寸,那便是认清现实仍旧能奔赴仍能热爱的空想主义。(不言)
来源: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