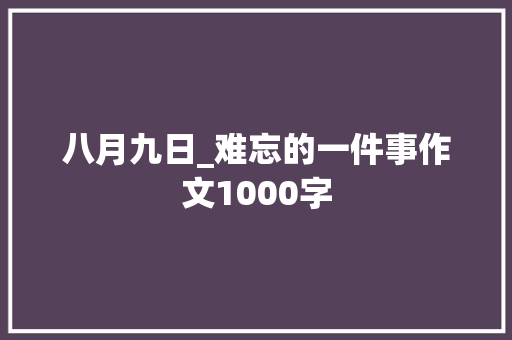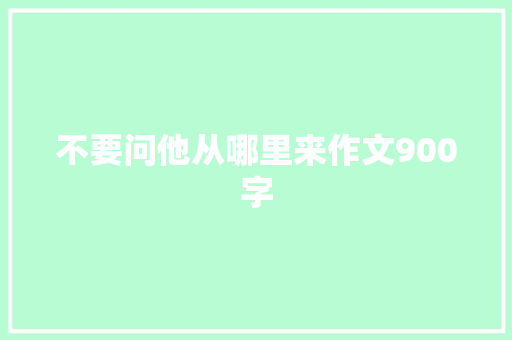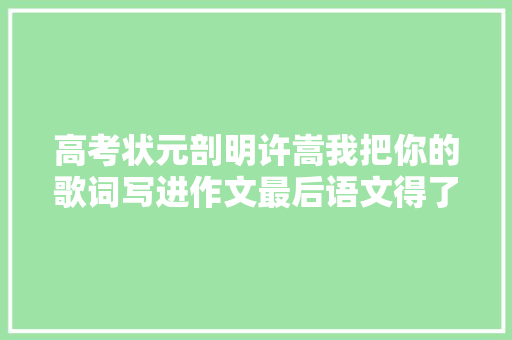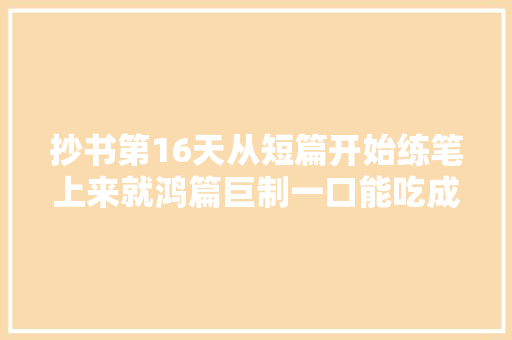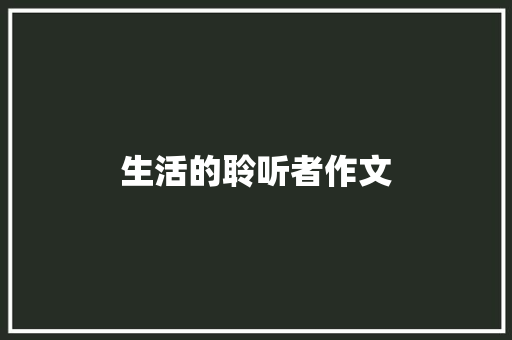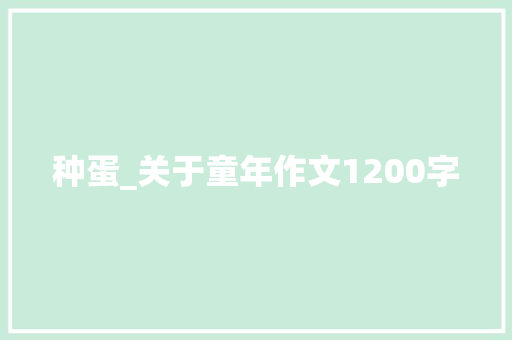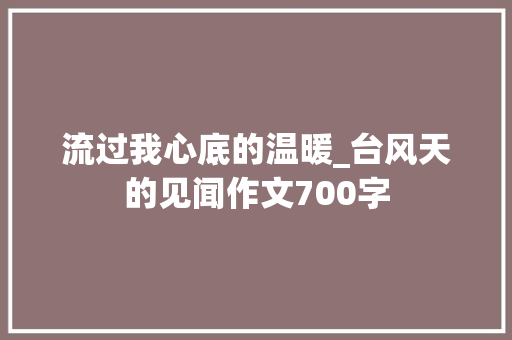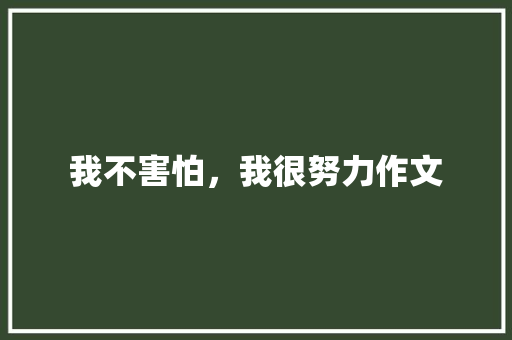作者|刘晓箫
瞅一眼题目,骇自己一跳,彷佛是个饱灌经籍的书虫,彷佛是个游学列国的贤士,彷佛是个著述齐身的写手,实在什么鸟都不是,和一批文氓朋友比,写的之少,如秃顶之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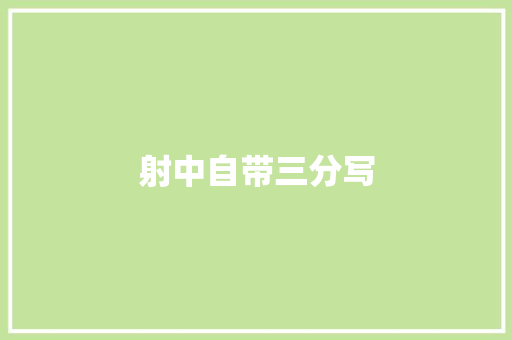
写得少是真的,命中自带三分写,也是真的。
在有影象的年事里,用写来表达对天下的欢畅、茫然、模拟、讨厌、疼痛,是必不可少的。少割了猪草,被妈老汉一顿暴搓,奔到山坡上,一边痛哭,一边用树丫在石板或泥土上狠力的写;河水里泡澡泡得眼花缭乱,跳上岸来,用石块或荆条在沙滩上狂写;放学的路上,用木炭或偷来的粉笔在墙上在同学的背上、书包上乱写。那些叉叉勾勾、大家马马、鸡鸡雀雀,风一吹、雨一打、浪一冲,随童年的悲欢,已不复存在。
再羸弱的肉身,青春依然是头猛兽,在体内疯长。那些年代,对异性的初爱,羞于口齿,写是必不可少的。一封情书,写无数十遍,某个标点用错了,某个笔画写长了,某一行排列歪了,某一个语意浅了,无数十遍重写。写得睡着,醒来又写;写得手指发麻酸痛,歇歇捏捏又写。这样的结局是,信石沉大海,字越练越好,写越来越狂。
以至于,后面想用写来混口饭吃,想用写来博取名声,出人头地。
村落里一户人家因小孩划火柴烧了屋子,自认为是有警示意义的,写去县报上登了。几天后,失落火人家找上门来冒死,我吓得站在秧田里不敢上来。原来,失落火人家瞒报事件缘故原由,本来可以得到乡里好几块钱的民政救助,被我写脱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好几块钱,比我现在拿几百万还难。我拿不出钱赔,自认理亏,结了子孙仇,每次赶场途经失落火人家,大气不敢出,还必须要有大雾罩着。
骇是骇惨了,命中自带的东西,是骇不掉的。
住家的地名在仰天窝,阁下有匹坡叫牯牛坡。传说仰天窝是牯牛踩的脚印,又传说牯牛是大闹天宫时摔来世间的。那年县上有人来搜集民间故事,我写去县报又登了。这次没犯天神,壮了胆,连续写了好些篇。搜集民间故事的活动中,我认识了一个大人物,他鼓励我多写。我翻着白眼想,他那副金丝眼镜,那身米白色风衣,一定也是写来的。这是我影象中见到的,第一个比我会写的人,县上的。多少年后,知道他叫李嘉良。
命中自带的东西不但骇不掉,也苦不掉、打不掉、痛不掉、穷不掉。
家里没钱买石油,我就争着去生产队看保管室,在月光下写;栽秧打谷、犁田耙田、薅草淋粪,纸笔藏在腋窝下,趁歇息时写;妈老汉睡着了,躲在被窝里写,电筒,也是妈老汉枕边偷的。自然少不了被打骂,妈老汉乃至威胁,再这样写,就分家,再这样写,婆娘都说不到。也是多少年后才知道,有人来提过亲,姑娘听说我身体软弱、斜眉瓜眼只会写,撇撇嘴,田头土头又写不出粮食,哦嗬了。
由于写,后面认识了好多比我会写的大小人物,一个个像光彩互异的瓜,结在一根叫“富顺县文学爱好者协会”的藤上。我出门闯荡,当时并没想挣钱,内心不服气的,便是想让自己这个瓜要比别的长势良好,比别的个头要大。表面呢,也附庸风雅,以与会写的人相处为荣。2000年初,县上文协那帮会写的人要办异地笔会,我把他们邀来重庆,吃喝拉撒两三天,除脱一万多。那时公司初创亏着本,一万多大部分是借来的,名声倒留了个好,可真痛了好几个月。想想痛了也值,不是这个好名声,恐怕后来的后来,家乡那个文化名人故乡行“文化守望者”的奖杯,是光荣不到我头上的。
细细想来,写真是一门妙手艺,没写出粮食,没写成作家,没写出人头地,但能写高情操、写硬意志。在重庆流浪,卖小菜、送报纸、当棒棒、冲茶水……衣食不保居无定所,写是去世不甘心的。那些诗歌、那些散文,在《重庆晨报》、《重庆》、《重庆商报》、《青年报》、《公安报》以及《四川日报》、《经济日报》等报刊持续冒个泡,持续获点奖,持续引起了更多会写的媒体人的关注。接下来的故事便是,人出了名,钱还是没有。后来我加入了重庆市散文学会。一年接一年的会费,一贯是一个写成了名家的叫邢秀玲的老师代交的。至今我没还过,像一个“机会”老赖。
九十年代初,像我这样的劳苦大众,匍匐在神往幸福生活路上的最底层,想靠写来改变命运的人,除了有汗气,还叫有志气。全国媒体从地方到中心,以及港澳台、日、英、法、美、意、韩等坚持不懈地追踪,2012年初,受喷鼻香港凤凰卫视约请去北京参加《一虎一席谈》节目访谈,一起上过安检,以至于在北京街头打出租车,他们都认出我,抻起大拇指说,你这个会写文章的“棒棒作家”,凶。搞得我一愣愣的,真有点由由然,有点国际范。
现在叫正能量,那时叫前辈业绩。我的业绩被范例了又范例。重庆市委宣扬部、团市委把我的材料报送中心,由团中心、培植部、公安部、法律部、全国妇联、国家工商总局等八部门联合评比,付与我“中国第二届精良外来务工青年”名誉称号。证书送来那天,重庆市区领导陪同团中心副布告杨岳一行来到我公司兼住家的所在地,面对这个更大的大人物,面对他的鼓励,我忘却了问他是不是也会写,竟多少有些哽噎了。
偶尔算来,这些年拉杂下来揭橥的小说、散文、诗歌也是上三位数的了,有些也当选进这个海内、那个国外的选本。在外飘荡居无定所,搬家的次数比岁数多,那些写有自己名字的报刊被收垃圾的一次掳走几本,已所剩无几了。五年前一个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留美美女,说要给我一个贵重的礼物,便是要把我这些年来写在报刊的文章和国内外报刊上写我的文章以及电视宣布等影像资料,搜集整理后正式出版,送我。我惊喜了好多年,偶尔邮局一个包裹,我都认为正是那个礼物,打开却是一份理财产品的先容或催收贷款的公函。
这些上三位数的书稿,出两本集子还是绰绰有余,列为60岁之后的远景方案吧。有点伤神的是越来越不会写了,但总想为越来越会写的家乡人做点事,以是准备撺掇今年的《诗刊》、《公民文学》、《十月》、《小说月报》等名刊名家进富顺,这是家乡文学史上的一次盛会,政府领导十分重视,现万事俱备,只欠良辰。
人生的良辰,一贯在路上,命中自带的写,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