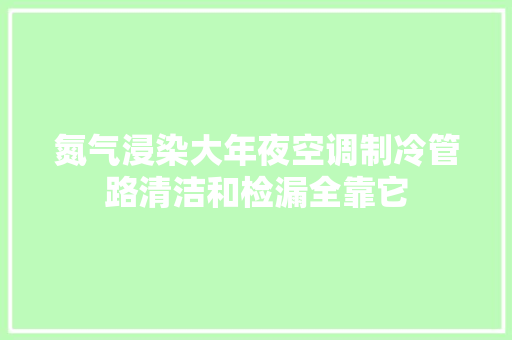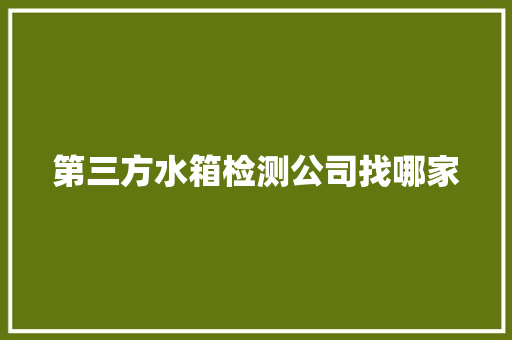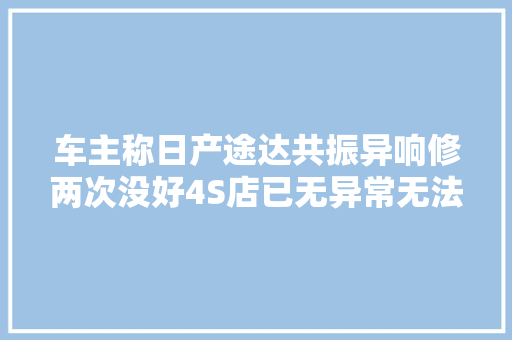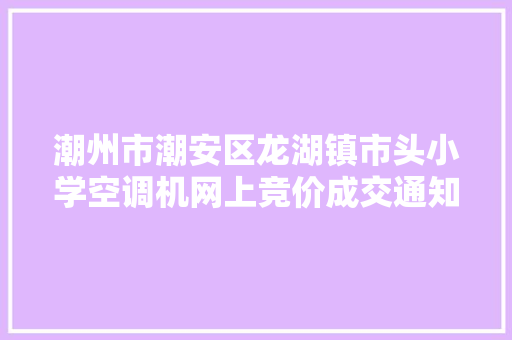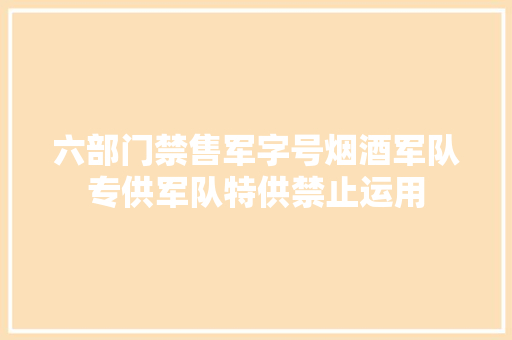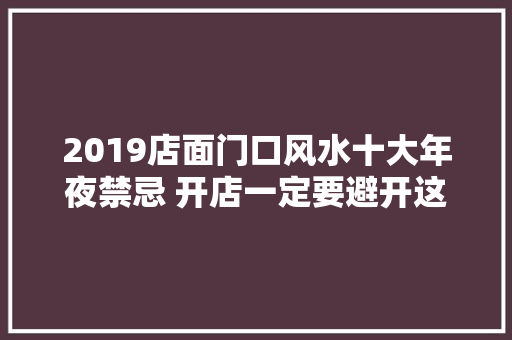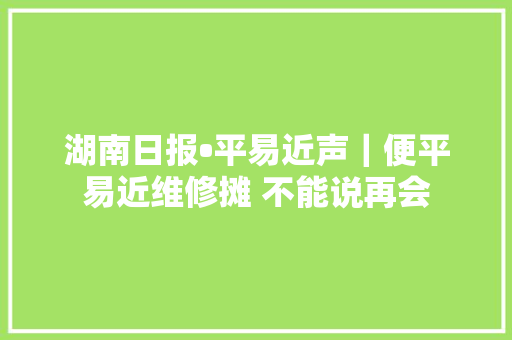译者:Issac
校正:易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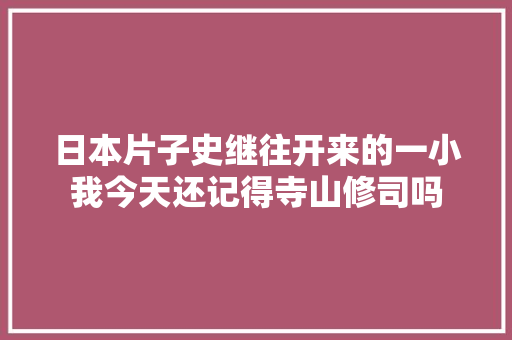
来源:Asian Movie Pulse(2021年1月27日)
《抛掉书本上街去》这天本新浪潮中最引人瞩目的电影之一。这部影片改编自寺山修司的同名小说,是作为先锋派作家的他在转行成为电影人之后的处女作。
只管他接着又创作了《去世者田园祭》(1974)和《草迷宫》(1979)等其他精品,但这部关于实验性无政府主义的大师之作,仍旧是寺山修司无可否认的原创艺术影像的典范。
《抛掉书本上街去》
寺山修司紧跟让-吕克·戈达尔的步伐,同时又预示了大卫·林奇的非线性的超现实主义。他布局了令人难忘的画面,这些影像以其传染力让不雅观众感到头晕眼花。评论辩论这部电影的情节险些是毫无意义的,由于当面对潜在的精神痛楚时,韶光和因果关系是显得那么地微不足道。
在一段精彩纷呈的开场独白中,主人公向我们先容了自己,他直视着镜头和我们的眼睛。「没人知道我姓甚名谁。我的名字从没上过报纸。我无名无姓,身无分文,全身尘埃,」他承认道。「没人知道我是谁。」
这便是《抛掉书本上街去》的中央主题:在一个冷漠的天下里,永久注定要寻求认可。随着影片故事的发展,我们忘却了他那不主要的名字,他只是被认为是普遍意义上的「我」。
寺山修司向我们呈现了主人公跌跌撞撞地从一个悲剧走向另一个悲剧,冒死地探求某种主不雅观性的过程。他那穷得叮当响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性变态,性侵了妙龄少女;他的妹妹与她的宠物兔子被困在一种近乎兽性的关系中;他的祖母是一个谎话连篇的商店扒手,除了她自己,谁也不在乎。
这部电影以反复地陵犯、轻渎的办法,营造了一种焦虑的氛围,这种焦虑纵然在影片结束后也不会消逝。主人公梦想成为一架「人体飞机」,好逃离令人窒息的生活,飞向许下了虚伪承诺的美国。然而,他在自己的弗洛伊德式的噩梦中挣扎,并目睹了他的家庭的缓慢解体。
《抛掉书本上街去》的最大造诣是它能够与艺术形式进行聪明机动的对话。拍照师锄田正义用引人入胜的视觉叙事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这部电影在彩色拍照的现实主义和单色镜头的迷幻和哲学意义之间游走,由此成为了对电影叙事传统的抗议。
此外,当作为背景音乐的摇滚乐响起,主角试图逃离某些东西时,镜头在某些场景中猖獗地转向。这种能量是如此俏丽的无政府状态,以至于它威胁着媒介本身的稳定性。
由于寺山修司的艺术之旅深受文学天下的影响,他的电影实验在实质上也非常具有文学性。他利用了「戈达尔式」的插入字幕的办法,来引用符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安德烈·马尔罗和埃里希·弗洛姆等人的话,但这些例举并不是对法国新浪潮的盲目模拟。
寺山修司见告他的不雅观众,「这座城市是一本开放的书。在其无限的页边空缺处书写吧!
」因此,他在足球场、街道和墙壁上潦草地写下了他的字幕,作为对当代性造成的存在真空的一种反抗。这是他坚持自己存在的办法。
相反,他也通过记录看似随机的人们的自白来哀叹个人身份的损失,这些人有着同样的反常的希望和平庸的思考。寺山修司通过细致入微的创作手腕和前卫新潮的处理手段,证明了作者导演是超越统统的作家。
毫无疑问,扮演无名主人公的佐佐木英明带来了精彩绝伦的演出。他是否真的是主角,或者迅速变革的东京城市景不雅观才是故事的紧张角色,只管对付这一问题,人们可能存在着一些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佐佐木英明成功地成为了抱负破灭的年轻人的完美代表,他在影片中对70年代的日本社会及其对美国的盲目迷恋进行了严厉鞭笞。
更有趣的是,他常常踢开第四堵墙,用歧视的语气对不雅观众讲话。他提醒着不雅观众,这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他将在银幕变成空缺的那一刻不复存在。「电影很快就结束了,没有人会记得我,」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但事实并非如此。
只管寺山修司的这部精品问世已近50年,但它仍这天本电影史上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电影界跨界的元虚构作品的缩影。《抛掉书本上街去》令人难忘地批驳了冗余的公共机构,同时敦促我们拥抱现实天下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