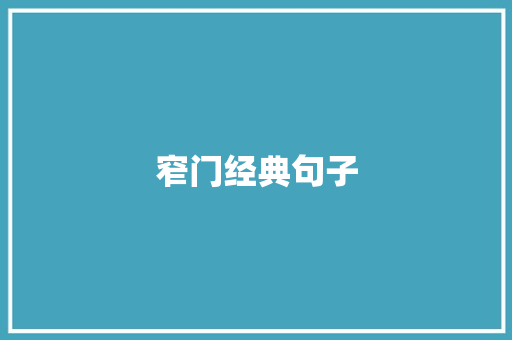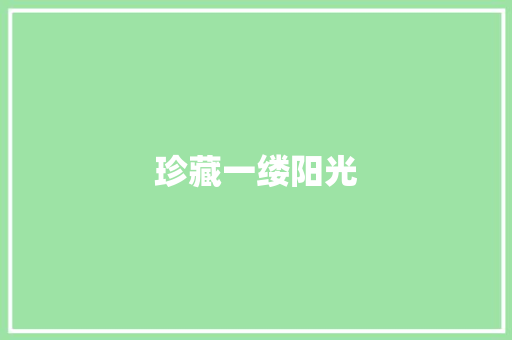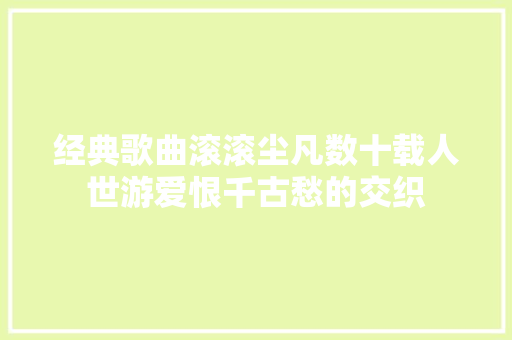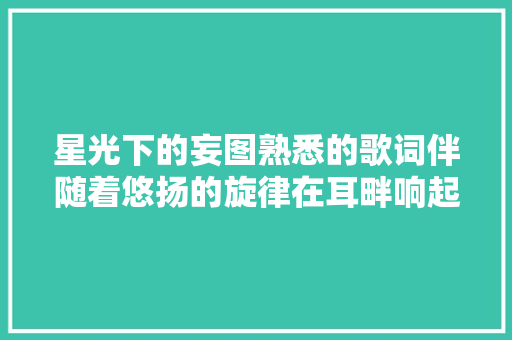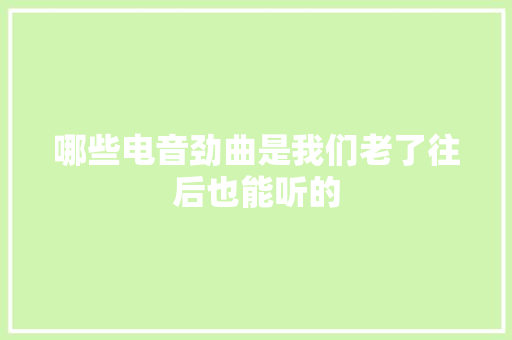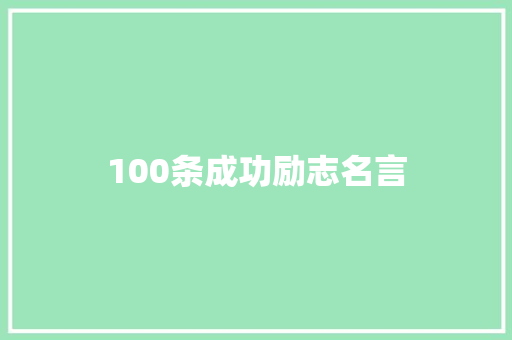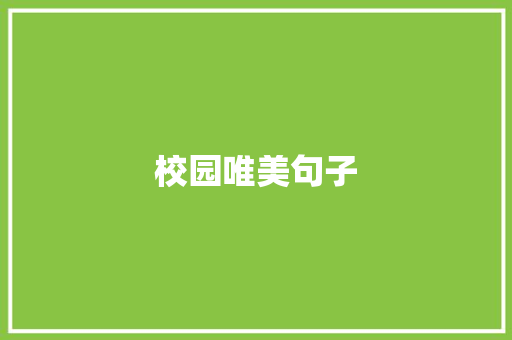“赋比兴”之说从何而来?我们搞清楚起源,就知道了原来的详细含义,再看一些在诗歌中的运用实例。
关于“赋比兴”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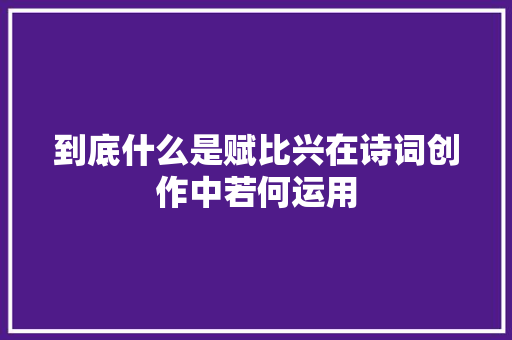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这是不是诗的六种形式呢?非也。《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
故诗有六义焉:风、赋、比、兴、雅、颂。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阐明说: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这里就阐明得比较清楚了。《诗经》从内容和音乐的乐调上来划分,分三个门类,便是“风、雅、颂”,是为“《诗》篇之异体”。
“赋、比、兴”,是创作诗的三种不同修辞方法,“《诗》文之异辞耳”。用三种不同的修辞方法,写出来三大门类的诗歌作品,共同称为“六义”。
由于中国诗词以《诗经》为万世之宗,这三种修辞手腕被总结出来之后,一贯沿用在诗词创作中,成为写诗的最基本的几种手腕。虽然不断有新的手腕涌现,但并不影响,也无法离开这三种基本手腕的范畴。
赋,便是说事。比,便是打比方。兴,便是遐想。
由于是从《诗经》而来,我们就举几个《诗经》中的例子,至于后来诗歌中的赋比兴实在太多,大家可以自行分辨。
赋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子之于归,宜其室家。
——《诗经·周南·桃夭》
翠绿繁茂的桃树啊,花儿开得红灿灿。这个姑娘嫁过门啊,定使家庭和顺又美满。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句诗前面写景,后面写事情,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大概有,但是联系失慎密,这里紧张的是把景致和事情说清楚。赋便是铺陈直叙,是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看到由于桃花的残酷,产生了这个女子旺家的想法,这里面隐蔽了类比吗?是不是由景致遐想到女子的性情和当家才能?都有可能。
以是,赋、比、兴,特殊是赋和比、兴一样平常是共同存在,相互浸染的。
这两句还是以赋为主。
比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国风·魏风·硕鼠》
大田鼠呀大田鼠,不许吃我种的黍!
多年费力奉养你,你却对我不照顾。起誓定要摆脱你,去那乐土有幸福。那乐土啊那乐土,才是我的好去处!
诗歌创作者从一开始创作这首诗的目的,就不是唱给大老鼠听的。这里非常明显的有所指代,也便是用硕鼠来比喻贪得无厌的剥削者。但是又不敢直言,以是才会有这种“指鸡骂犬”的讽喻诗歌的涌现。
这里便是范例的比喻、类比。孔颖达曾言:
“比”者,比托于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惧,故云“见今之失落,取比类以言之”。
古代老百姓对统治者、臣下对君上,都有很多不敢言的时候,这个时候用打比方来让人明白,不失落为一种婉转的劝谏办法。
当然,到了本日,我们的比喻就更加丰富,利用场景也就更多。
兴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国风·周南·关雎》
《关雎》在艺术上奥妙地采取了“兴”的表现手腕。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遐想。
那么“兴”和“比”有什么不同呢?便是思维先后的不同。如果我们这里改写成: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君子都爱淑女啊,就彷佛雎鸠在河中相向和鸣。
这便是“比”了。也便是说由事物、景致引发遐想、思考,我们称之为“兴”。而主动的选用事物、景致来类比我们的心思,则是“比”。
当代例举
总的来说,赋比兴是最根本的三种诗词修辞手腕。这个并非诗词独占,我们在写文章、说话中都会利用,只不过古人很早就把这几种方法总结了并提出来。
纵然在本日的当代诗歌中,也是一定利用到的。
比如我们说“伟大祖国的山河壮丽”,这便是“赋”。我们高歌“祖国山河美如画”这便是“比”。我们看到山河壮丽,说“山河多娇,祖国伟大。”这便是“赋”中带“兴”。
这样说,是不是更直接明白了呢?
(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