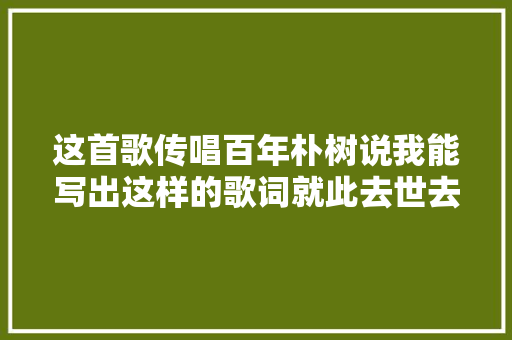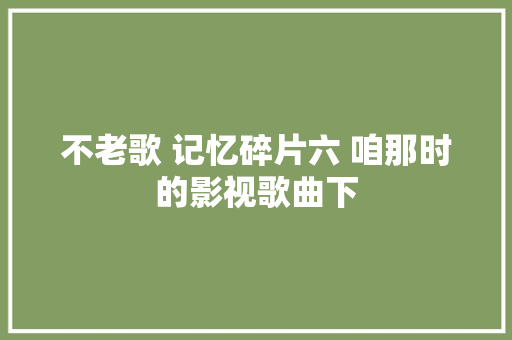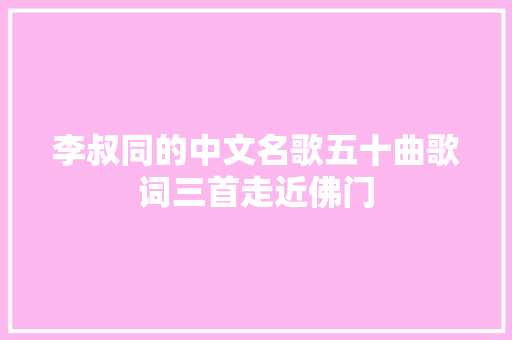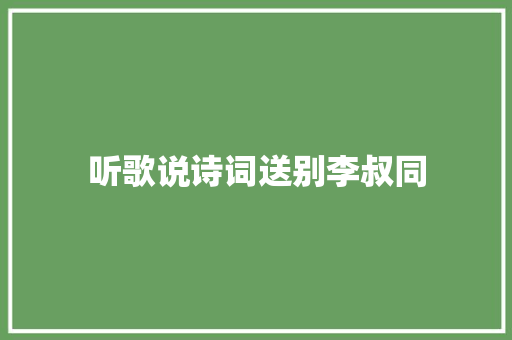师铤
冬奥会闭幕上听到了《送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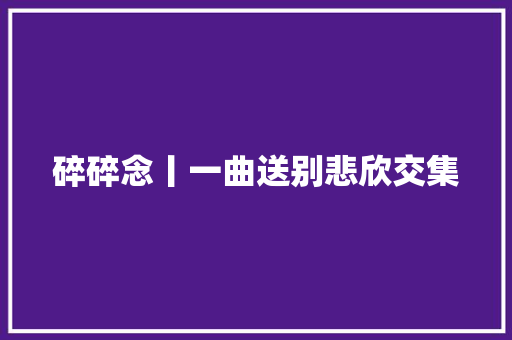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深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深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这首歌作于1915年,掐指一算,已经百余年了。
歌词极为大略,又极为繁芜。大略的是,上过几年学都读得懂,繁芜的是,它凝聚了千年来墨客们关于送别的瞬间:
长亭外,有李白的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连天芳草,有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晚风拂柳,有刘禹锡的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残笛声里,有赵长卿的行客易销魂,笛飞何处村落。
一壶浊酒,有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端人。
天涯地角问归期,有苏东坡的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深交零落,有孟浩然确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李叔同的作品,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原作者是美国人约翰·奥德威,原名《梦见了家与母亲》。详细创作韶光与创作背景已经很难考证,历史学者估计创作于南北战役前的1851年旁边,歌词的第一段写道:“梦到了家,亲爱的老家。童年和母亲的家——当我醒来时常常以为很甜蜜,我一贯梦想着家和妈妈。家,亲爱的家,童年快乐的家!
当我和姐姐、弟弟一起玩的时候,当我们与母亲翻山越岭嬉戏时,这是最甜蜜的快乐。”
李叔同去世后,丰子恺在老师故居前,见到他生前亲手种下的杨柳,心中触动,将此景入画,并题字:“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这首歌在当时引起军人的共鸣,风行一时,但随着美海内战的结束,它也逐渐被人忘掉,现在险些没有什么人还记得它。令人惊奇的是,南北战役结束半个世纪后,这首歌却在大洋彼岸的东亚火了起来。1904年,日本墨客、歌词作者犬童球溪将其重新填词,名为《旅愁》,揭橥后在日本广泛流传。1907年,它当选入日本《中等教诲歌唱集》。
那个时候,李叔同正在日本留学。
李叔同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天津。李家凭借经营盐庄与银号买卖富甲一方,并与当朝仕宦多有往来。李叔同的父亲是同治年间的进士,是清末重臣李鸿藻的部下,与李鸿章交情密切,他去世时李鸿章亲临主丧。
兼具商业与政治背景的李家权势显赫,但随着父亲去世,年幼的李叔同与婢女出身的母亲地位着落,15岁便发出感怀:“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能在年幼时写出如此老辣的诗句,除了人生经历,还有李叔同坚实的学术根底。
当然,官宦家族的出身,让李叔同曾致力于科举,他两度参加县学考试,指望文章立命。在策论“论废八股文兴学论”中,他年夜方陈言:“窃思我中国以仁厚之朝,何竟独无一人能体君心而善达君意者乎……”答卷针砭时弊,却“胆大妄为”,结果名落孙山。
戊戌变法后,李叔同备受触动,曾刻下“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后来,由于这枚印章,他受到牵连,母子二人避走上海。
在上海,李叔同加入城南文社。他与文社的盟主,当时上海新派诗文界领袖人物之一的许幻园惺惺相惜,他俩与袁希濂、蔡小喷鼻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他与画家任伯年等设立“上海字画公会”;他入南洋公学就读经济特科班,还与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从学于蔡元培。在上海短短几年,李叔同便蜚声字画诗文界。后来,母亲去世,他改名李哀,远渡日本。
去之前,他曾作一首《金缕曲》:
散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整顿?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瘦削。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顾。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
听匣底苍龙狂吼。永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百年后再读这首词,个中的英气满胸、爱国激情亲切依旧炽热。
学生丰子恺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我曾在照片中瞥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头抬得很高,漂亮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
李叔同虽是在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系专攻泰西画,但同时,他也在学音乐和戏剧。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音乐刊物,揭橥了最早先容泰西画知识的文章,又将话剧引进中国。
在话剧《茶花女》中,他男扮女装,为贴合角色,节食数日以求身形更贴近女性。故意思的是,他演《黑奴吁天录》的时候,同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还特意去看过。这大概是两人殊异的人生里,间隔最近的一次。
良久往后,鲁迅得到了李叔同一幅字,深感光彩,忍不住写道:“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能让迅哥儿如此夸奖的人,不多。
在日本几年,李叔同诗、画、戏、乐的水准几近精绝,被誉为天才,其后返国任教。
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李叔同填了一曲年夜方冲动大方的《满江红》: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去世,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爱国激情亲切,溢于字间。当老师的日子里,李叔同收起了曾经放浪形骸的风骚才子习气,成为一个终日粗布麻衣的谦谦君子。好友夏丏尊曾写道:“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统统都好,小旅社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这是何等的风光啊!
”
1915年某一日,石友许幻园来见李叔同。曾经有百万家私的许幻园,在纷乱世事中家业无存。他来找李叔同,却门也未进,二人在门口相视一笑,许幻园说:“叔同,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便转身拜别。李叔同望着许幻园的身影,心中许久不能沉着,回屋便写下一首小词,配上他曾在日本听过的《旅愁》一曲,便是流传百年的《送别》。
几年后,李叔同在杭州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
“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绅士,像个绅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这是丰子恺对他平生的勾勒。
李叔同在文学、音乐、字画、戏剧等多个领域首创中国的先河,他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是他,把当代的话剧、油画、音乐先容到中国来,为中国近代的艺术界、教诲界、文化界和宗教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2年,已经是弘一法师的李叔同,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
晚晴,是由于他晚年号晚晴老人,大概是出自李商隐的《晚晴》: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圆寂前,他曾手书二偈给夏丏尊等故人故友:“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而床边的矮几上,一张旧信纸上留着他末了的墨迹:悲欣交集。
前几年,我去泉州嬉戏,特意去拜会这位百年前的文化通才,但不幸的是,遇上了施工。
那个阳光残酷的岭南冬日,我站在密密麻麻的脚手架前,沉默良久。那一刻,大概,便是大师所谓的悲欣交集。
本文来自【渭南日报】,仅代表作者不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供应信息发布传播做事。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