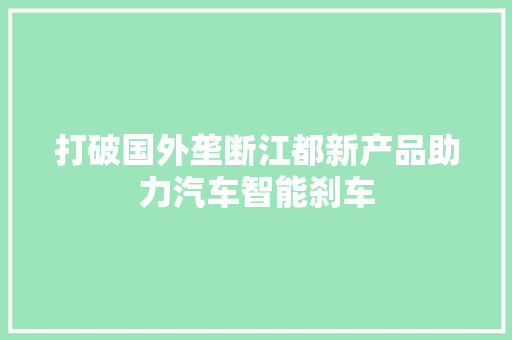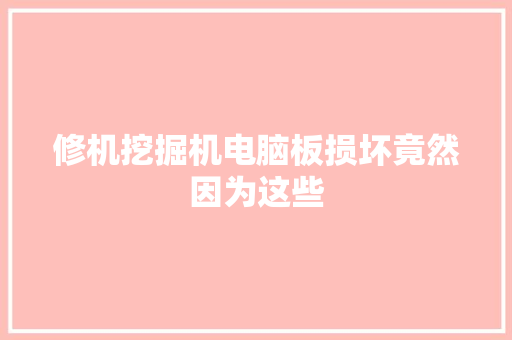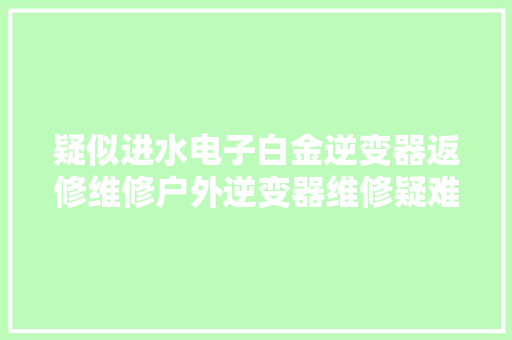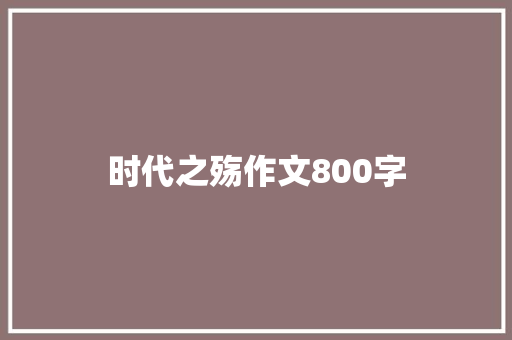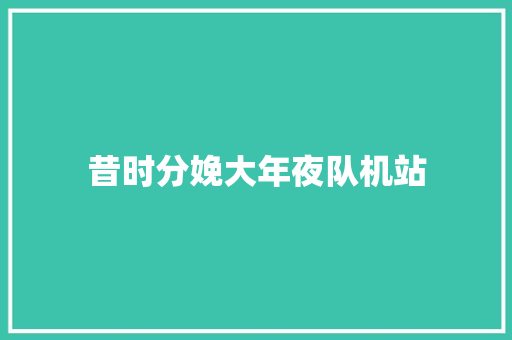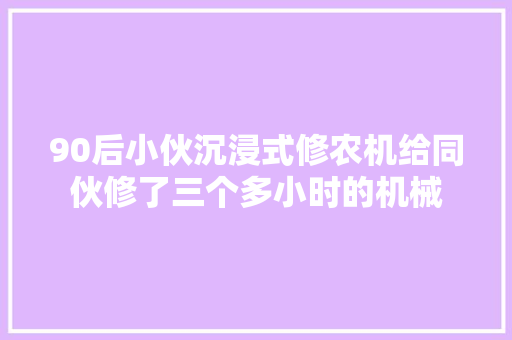癸卯清明节,笔者与再兴伯父以及堂兄弟们一起踏上了重访岩头下旧亲之路。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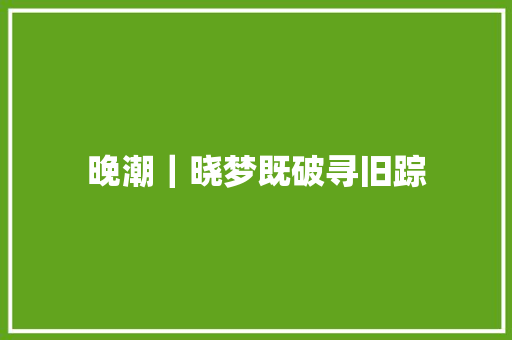
出晒台县城往西,到达平头潭的标志便是瞥见了被平头潭人称为龙头的小山岗。起先这一带松林茂密,山塘相连,山涧泉水丰富。山岗和周边的景物都被陆蠡写进了文章里,陆蠡在书里详细描写了当年一些好赌钱的女人将山坡那棵老樟树奉为树神,在树底下挖洞祈祷的趣事。贴溪坡道的踏步和石板栏杆年分久远,镌刻着捐造者的名字;坡顶的路廊是陆蠡的父亲陆宗兰师长西席出资建筑的,以是,路廊两侧的厢房曾经全部是陆家的财产。很长一段韶光,陆蠡的三弟考金就在路廊做烧饼。
在始丰溪上游建成水库之前,溪水浩浩荡荡,水面宽阔,岩头下边的大溪潭泛着巨大的漩涡,“碧澄澄的潭水”深不见底。陆蠡在书里这样描写溪边情景:“沿溪的一带岩岗,拍岸的‘黄梅水’涨平了,沿伸到水里的石级,上高下下都是捣衣的妇女。阳光底下白的衣被和白的水融成一片。韵律和砧声在近山回响着。”
陆蠡笔下的水潭边充满了生活气息。纵然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雨季里,下贱始丰溪与崔岙溪汇流的毛狗洞峡谷来不及泄洪,大水依然会涨到岩头下巷,也即陆蠡祖居的檐阶下,这个位置便是现今平桥镇始丰路街面房二楼顶的高度。
陆蠡故居。
那时的平镇与东林南北岸通畅,虽然有独木桥,但多数情形是在旱季时才用得上,由于河面太宽,一发大水那桥就被冲毁,以是多数情形下利用木船和竹排过水。彼时,源自屯桥王里溪的文溪还是水势彭湃,它在平头潭的下街那座平坦的石板桥位置拐了九十度的弯,翻卷着汇入始丰溪的深潭。以是,关于平头潭所指的位置至今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岩头下村落龙头下的始丰溪大水潭,一说是文溪不才街的拐弯处。在村落庄公路涌现之前,始丰溪的水路交通非常繁忙。上至晒台最西面区域的积石乡三十七都(田芯、寺岙、方前一带),下至晒台县城直至临海,大量的运输都走水路,特殊是山区砍伐的木头、柴火等货色。我相信《竹刀》里的故事就发生在岩头下一带的溪岸上。
陆蠡21周岁于(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机器系毕业,被付与工学学士学位。国民党政府以劳动大学首届毕业生有“赤化”嫌疑,被遣送回原籍。这该当是陆蠡自己说的“游罢归来”,陆蠡在《溪》一文里接着写道“自从泛迹彭蠡,五湖于我毫无介恋,故乡的山水乃如蛇啮于心萦回于我的影象中了”。少年沧桑的陆蠡颇有倦游之意,随后更是把异域的湖沼比做“醉翁呕吐出来的唾沫”,因此,“我如怀恋母亲似的惦记发迹乡的山水了。”由此可见陆蠡是一位不掩饰笼罩自己爱憎的人,他眷恋故乡山水,热爱故乡的人。就像蔡庆生师长西席在《陆蠡传——在劳大》文中写的“陆蠡对故乡的爱,对故乡山民的爱,是既深奥深厚且十分动听的,很分外的,这有他的大量散文作证。”
陆蠡对付家乡的情绪有一个详细化的行为,那便是在1928年,亦即他尚在国立劳动大学就读中间,他为家乡购进了“一架碾米机”。对此,陆蠡在他的散文《哑子》中做了明确阐述:
“在一九二八年的年头,我们乡间第一次进了一架碾米机。这是摧毁人力劳动的第一机声吧,这是第一次伸到屯子里都邑的触角吧。大桶的石油作美元成本侵入的先驱,而破人晓梦的不是鸡声而是机器的吼声了。”
这是一则信息量极大的笔墨,九十多年前,全体中国村落庄还是完备依赖人(畜)力的原始农业生产办法,人力播种、人力灌溉、人力收割,栽种业还没有病虫害防治和化肥技能,农人完备靠天用饭。稻谷加工采打水碓或者畜力的碾子,大多乃至用捣臼和舂杠舂米。当时采取柴油机动力的成套碾米设备,是原始生产办法向当代生产办法的一大超过,不要说在晒台乡间平镇,便是在海内都是前辈的、罕见的。
2
陆蠡同情底层的劳动者,正如他在作品《竹刀》里写到的整顿松针累去世的少女、刺去世欺行霸市的木行老板的山里年轻人;《水碓》里被石杵捣成肉酱的童养媳;《嫁衣》里不堪劳累和侮辱,去世于火中的堂姐……以是,他要让“都邑的触角”伸到屯子里,让“机器的吼声”来“破人晓梦”,即用当代机器代替繁重的人力劳动,从而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当然,陆蠡的思维是敏锐的,他有复苏的民族意识。在给家乡购得碾米机的同时,他也想到了随着机器设备的引进,“大桶的石油作美元成本侵入的先驱”。只怪当时中国各方面太掉队了,所有新技能、新设备都依赖“洋货”。在仰仗入口技能来改变传统生产办法的同时,又要担心外国成本对付中国人的剥削,陆蠡的内心是抵牾的。
给家乡引进碾米机除了陆蠡的外语上风、上外洋埠的信息上风,还有一个关键成分显然是陆蠡懂得机器事理。我们现在的印象陆蠡是个文化人、作家,实在陆蠡两次大学读的都是工科。陆蠡在16岁那年考入之江大学机器系,由于仗义替同学汤独新承担了烤火烧焦宿舍地板的任务,而被劝退学。而在1927年,陆蠡转而考入由吴稚晖、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的国立劳动大学,读的又是机器系。无疑,专业背景是陆蠡能够为家乡引进机器设备的技能立足点。本日的我们已经无法理解近一百年前的交通条件下,成吨重的碾米机器设备如何从上海口岸运输到山乡的晒台平镇,这在当时当地一定是个引人瞩目的重大事宜,晒台民谚“洋货洋麦磨”指的便是入口的新式粮食加工机具。
陆蠡故居。
有关碾米机后续的故事,陆蠡在《哑子》一文里这样写道:
“虽则是一九二八年的机器,虽则在一九二八年的内燃机是十二分完美了的,但是我们乡间的机器是笨拙不堪。以是机器来了,结果不是人使令机器,而是机器使令人,两个人般高的飞轮摇动时是须要两个壮汉的力量。
主人为了开车的事情央人受了不少的麻烦。而哑子在这地方便显出他的神力了。他只要一个人,飞轮摇动了,机器做起工来,大家都满意。
从此,哑子便专在此间摇车了。三餐饭食有人送来。主人也大量的,每天收入的铜元随手拿几十个给他,叫他积起来买几件衣服。”
打仗过柴油机的人可以推测这台“两人般高的飞轮”、“摇动时是须要两个壮汉的力量”的设备,它的动力少说有几十匹马力。陆蠡认为虽然一九二十年代国外的内燃机技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出口到中国的机器还是过于笨拙。《哑子》一文中,那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肌肉强壮的哑子成为启动柴油机的不二人选。
末了,机器运行的情形不是那么乐不雅观、那么大略,“为了机器的窳劣,碾米不久也就停顿了。哑子又过原来的生活。排水,舂米,牵磨了。”
这座村落庄的碾米房机器化的生产办法没有持续多久,又回到了原始的舂米办法。激情亲切、天真的陆蠡试图用入口技能改变屯子生产力的欲望彷佛落空了。事实上,这种设备直到三四十年后,即新中国建立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在村落庄大范围推广。陆蠡那个年代利用这种设备实在是技能超前。
《陆蠡传》作者蔡庆生于1981年6月9日下午,去平镇岩头下村落采访了陆蠡的小弟陆考金,陆考金师长西席对陆蠡购买碾米机一事影象犹新,他说:“《哑子》这篇文章中写到的碾米机,便是我大哥圣泉买进来的,是我们平镇置办的第一架机器。后来,他又为家乡购置了第一架抽水机。”
陆蠡帮助家乡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据陆蠡女儿陆莲英在《我的父亲——陆蠡》一文之“外地归来”章节记载:
父亲从外地回家,常常带来许多画片分赠给邻居的孩子,教他(她)们看图识字。他对穷苦人家的孩子特殊关心,回上海后,还寄书给他们,亲自写信辅导他们看书学习,有时还寄钱给他们。此外,还爱把外地的植物种籽带回家,向邻人宣扬选用优秀品种的好处。
父亲还考虑家乡缺医少药,治病困难,因而每次回家总要带回许多外地的殊效药品。有治霍乱的,治痢疾的,治疔疮的……只要有人上门要药,不分嫡亲朋好还是陌路生人,一概免费赠予……
父亲还从外地带回许多革命书本给大家看,个中有马克思的《成本论》,有《列宁的平生》和《共产党宣言》等等。
可知,为了帮助家乡、乡亲,陆蠡从物质到精神都尽力而为。而且,从文中也可看出,无党派人士陆蠡已经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自觉、主动地成为了马列主义的传播者。根据陆莲英的文章,父亲陆蠡寄到家里的这些书还给家里带来麻烦,曾经驻扎在陆家的国民党军队职员看到这些书本,疑惑陆蠡的父亲是共产党,把他抓起来并扬言要枪毙,亲友们费了许多周折,才将其祖父保释出来。
3
上世纪二十年代存在于晒台乡间的机器粮食加工厂是绝对让人稀奇的;身强力壮、以一当二的哑子一时风光地成为碾坊的柴油机“摇手”。
陆蠡认为“笨拙不堪”的机器对尚处于原始农耕模式的晒台乡间乃至全国,实在过于前辈了。除了坚持机器运转的柴油须要用美元入口,还有机器日常运行的掩护、维修的技能让谁来辅导、培训?其余,易损配件如化油器、滤芯等去哪里采购?运行韶光长了,活塞等核心部件也会磨损。在当时,恐怕只有大上海才有可能买到这些零部件,这对付机器利用者来说确实太未便利了。说穿了,彼时中国根本不具备机器化大环境。而无法掩护、维修和更新的机器设备是不可能长期正常运行的,只管陆蠡将其归咎于“机器的窳劣”。
《哑子》一文中,屡次提到一个“主人”,便是碾米作坊主,这个“主人”仅仅为了“开车”——摇动柴油机,已经“央人受了不少的麻烦”,遑论维修等其他事变。这位每天将收入的铜元拿几十个给有“神力”的哑子,“叫他积起来买几件衣服” 的“大(气)量”的“主人”——即这个碾米作坊的经营者是谁?
起先听两位伯父提起过他们的父亲其纬公年轻时,在平头潭经营过碾米作坊,人累得“黄胖”(浮肿)了,却没有赚到钱。大半个世纪前的事情让我们以为太迢遥了,想当然地以为难以追寻它的踪迹,尤其到现在已经由去近百年的岁月。
陆蠡祖居。
2023年清明节,前山葛村落葛姓尚存的历史见证者86岁的再兴伯及我们堂兄弟一行到陆蠡老家岩头下、岩头背寻访,在陆蠡故居和祖居与管理员陆师长西席见面,意外地使葛陆两姓所知的部分历史事宜对接、复原。
令再兴伯和堂兄弟们欣喜的是,二十几年不见的陆蠡故居修复如初;令他们惋惜的是陆蠡祖居“瑞气东临”宅院倾圮破败。
而这一趟寻访之行,一个意外的收成是,在陆师长西席的带领下,大家找到了那座传说的的碾米作坊旧址。它位于岩头背东岳宫正门口道路下方,修葺过的屋子外不雅观尚好,薜荔藤爬满墙头,这是陆蠡文章中的遗迹,也是其纬公创业的旧地。而它的斜对面坡下,便是面对文溪的陆氏宗祠。
正如蔡庆生师长西席在《陆蠡传》开篇“仙山佛国一小镇”中所说的“如今,平(桥)镇已经成为晒台县第二大镇,有著名的筛网市场,它的当代化该当还有陆蠡的一分功劳。”这话绝不夸年夜,适可而止,蔡庆生师长西席同样列举了陆蠡为家乡引进碾米机和抽水机的事例。新中国成立初期,晒台西乡最大的碾米厂——国营平桥米厂,就建在此碾米作坊隔壁的东岳宫内。而平镇最大的水利灌溉翻水站就设在岩头背,它的渠道蔓延到平镇周遭七八里村落庄,灌溉面积数万亩,因此,岩头背翻水站曾经为四近村落庄粮食稳产、高产立下汗马功劳。在岩头背的山坡上依山蜿蜒的围墙内,还有当年平桥农具制造厂、翻砂铸造厂等等一些企业的旧址。
可以说,九十多年前陆蠡为家乡引进的各种机器设备,希图“城市的触角”伸向屯子,为今日平桥镇成为工业化州里、晒台西乡的城市化撒下了种子。这是作为作家、文化人、抗日义士的身份之外的陆蠡为家乡所作的另一种贡献。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