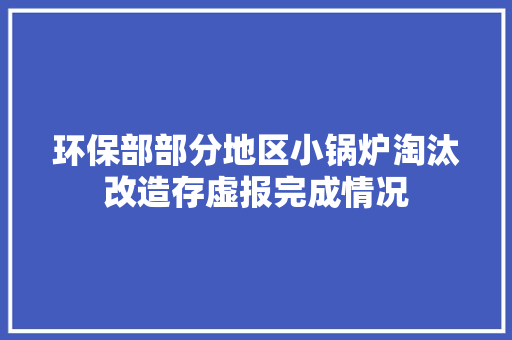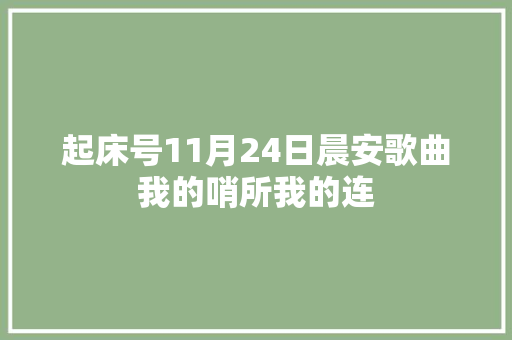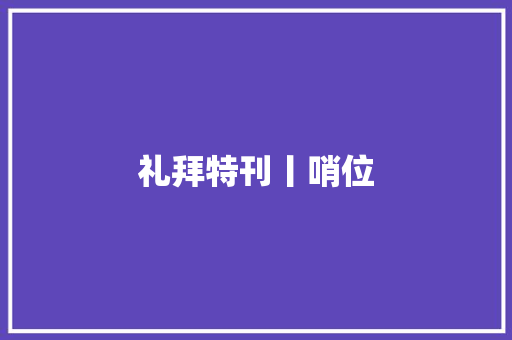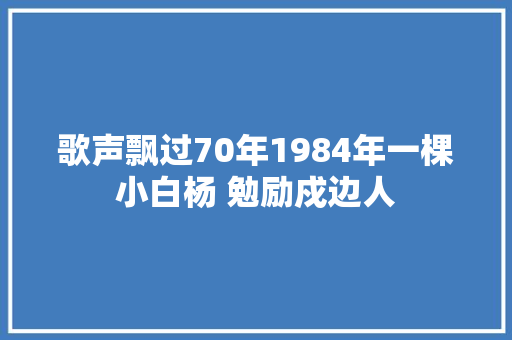解放军报特约 王钰凯
特约通讯员 梁晨 曾思源 杨锋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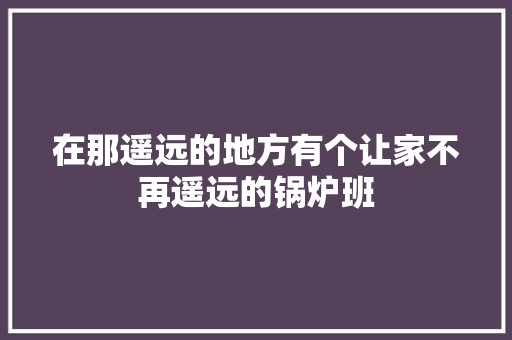
支普齐,藏语意为“在那迢遥的地方”。
“迢遥的地方”有多远?打开电子舆图,输入北京和支普齐的位置,连接线险些横穿全体中国大陆,显示约4800公里。这是个迢遥的间隔,相称于113.8个全程马拉松。
由于迢遥,鲜有人到过支普齐。关于支普齐哨所的艰巨,26岁的中士何光荣可以列举出很多证据:2021年的第1个月,油机和太阳能发电依旧是这里的紧张供电办法;前些年,昔时夜部分边防连队都换上第5代营房时,支普齐哨所官兵住的依然是活动板房;物资运到支普齐的本钱每每大于物资本身,在这里,饮用水是从河里抽的,菜是温室里种的,畜生是自己养的……
一群年轻的士兵被授予了一项分外任务——保障支普齐哨所的水、电、暖。“在支普齐长达8个月的封山期里,他们便是这个哨所最主要的支撑。”上尉俞湘剑说。
仿佛在两种身份之间来回切换,他们有时是战斗班,有时又会成为勤务班,而支普齐的官兵更习气称他们为“锅炉班”。
作为一班之长,何光荣认为烧锅炉这项“副业”还有个更主要的意义——让支普齐的官兵在这里安心扎根,让这个离家很远的地方更像一个“家”。
支普齐哨所“锅炉班”在国旗和星空下进行晚点名。亢红然、赵靖松摄
锅 炉
戴上露指手套,下士贺永玺将手指粗的铁棍捅进高高的锅炉,双臂同时向下发力。
在杠杆事理浸染下,大块炉渣被撬起,黑赤色的焦炭露了出来。贺永玺将炉渣捣烂、钩出来,又添了几锹焦炭。锅炉重新燃动怒焰。
这是贺永玺最常烧的一个锅炉。他用指尖轻轻触碰锅炉壁,以判断锅炉盖的开口角度——作为最关键的一步,开口大小决定全体支普齐哨所热水和暖气的温度。
贺永玺今年21岁,青海人,来到支普齐哨所已经3年多,烧锅炉一贯是他的“副业”。贺永玺很理解面前这几个大铁罐,“天冷了锅炉随意马虎闹感情,尤其是晚上。”他说。
由于常常照看锅炉,贺永玺所在的班被称作“锅炉班”。对付这个称呼,贺永玺并不反感,“只要经历过支普齐的冬天,大家都会明白烧锅炉的主要性。”
前些年,支普齐哨所还没有板房。入冬后,帐篷外的温度计被冻坏。官兵推测,最冷时温度能降到-50℃。“睡觉时要穿棉衣、戴棉帽,再盖两床被子。”贺永玺说,有了板房和锅炉后,生活条件才好起来。
每年6月,支普齐哨所才“开山”。那时,官兵对锅炉的需求还不大。“平时有热水用、周末能沐浴就行。”班长何光荣说。
但这并不虞味着夏天的锅炉就好烧。何光荣常常会听到战友的“抱怨”——
“最近锅炉有点反常,热得身体扛不住啊!
”
“温度怎么又低了?何光荣,你们还能不能烧?”
锅炉的温度不好掌握,更多是凭履历。何光荣当兵前是大学生,来支普齐哨所前没打仗过水、电、暖的维修保障。2019年,他接任“锅炉班”的班长。“演习时,我是他们的班长;维修上,他们很多人都是我的师傅。”何光荣说。
每晚睡觉前,何光荣会检讨一次锅炉,摸一遍管道,感想熏染一下温度。有时,他以为这个巨大的锅炉,就像是支普齐哨所的心脏,管道便是血管,心脏源源不断地向四面八方运送血液。
凛冬来临,“血管”随意马虎出问题。“如果暖气管道冻爆了,就要关闭锅炉,立即维修。”马永辉说,“不然一晚上过去,全体管道都会冻坏。”
下士马永辉参军前有过修车的履历,现在算是“锅炉班”的维修大拿,无论是锅炉、油机或者水泵都能修。
马永辉记得,几年前的一个夜里,管道上的碟阀冻炸了。由于短缺工具,马永辉从锅炉上拆下钢板,从轮胎里卸下内袋,两者加到一起,才止住管道漏水。
“根本想不到,那么粗的管子竟然会冻炸。”马永辉说,“在支普齐,你要有预见性,提前把第二年须要的工具准备好,不然有了紧急情形根本没法修。”
一次,大雪封山后,水泵的起动机烧掉了。官兵端着脸盆、提着桶从河里舀水,一天下来往返好几趟。这种原始的运水状态一贯持续到上级派直升机将新的起动机运进来。
对付锅炉的质料焦炭,“锅炉班”的兵都会有种分外的影象。何光荣第一次来支普齐哨所,是重新疆叶城出发,随着汽车兵上山的。他将行李放在后车厢的篷布上。篷布之下,是满满一车厢的焦炭。
到了支普齐哨所后,官兵们开始卸焦炭。四周扬起的炭灰将每个人都染成玄色。“只有牙齿是白的。”何光荣说。
烧锅炉前,他们会将这些“烦人”的炭灰用纱窗筛掉。“炭灰会压灭炉火。”贺永玺阐明。去灰的过程会弄脏迷彩服,但他不会急速洗濯,“太累了,坚持穿到周末再洗”。
只管又脏又累,贺永玺还是喜好烧锅炉这项任务。夜里,寒风被阻挡在屋外,贺永玺会在检讨锅炉的间隙,偷偷点一根烟,或者泡一包方便面。最令他愉快的是,早上还可以补一下子觉,一贯睡到开饭前一刻。
下哨后的哨兵和贺永玺一样,喜好躲进锅炉房取暖和。“那里有种家的温暖。”他说。
界 碑
“嘟嘟嘟……”
清晨,紧急凑集的哨音在支普齐哨所响起。
马永辉扛着迫击炮冲在最前面,贺永玺和何光荣提着炮弹箱紧跟其后。
目标点位是山顶的哨位,中间隔了103层台阶。台阶是官兵们自己修的,马永辉喜好称它为“绝望坡”。
在均匀海拔4500米的阿里高原,一口气爬完“绝望坡”绝非易事。平时哨兵上哨,都会在“绝望坡”中段的位置停下歇一下子。
为了抢韶光,他们沿着台阶旁的土路向上跑。冲到距山顶一米旁边的位置时,贺永玺腿一软,直接跪在地上。
空气溘然安静下来。何光荣听到弹药箱里传出“咚咚”声响,那是迫击炮弹相互碰撞的声音。瞬间,何光荣觉得手心渗出汗水。他右手牢牢抓着弹药箱,左手拖住贺永玺的屁股。
几十米外,已经进入掩体的上等兵马鹏忠也惊出一身冷汗。
好在,一行人顺利到达山顶哨位。
山顶的哨位,仿佛是一个无形的界碑。何光荣时常会想起那句盛行于阿里高原边防的一句话: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便是在没有界碑的地方,耸立成活界碑。
有时,何光荣以为自己真的变成了“活界碑”,“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守在了支普齐”。
2015年6月,何光荣从黄冈师范学院毕业。看完学校播放的征兵宣扬片,何光荣萌生了“携笔从戎”的动机。他很快报了名,并通过征兵体检。
何光荣记得,当时院长建议:要去就去最远、最苦的地方磨炼,把诗人气变成男子气。
于是,何光荣来到最迢遥的支普齐当兵。
班长何光荣在检讨排水设备。亢红然、赵靖松摄
山顶哨楼的墙壁上,写着“提高当心,保卫祖国”8个大字。站在这里,军人的义务意识会格外强。
“锅炉班”修了铁丝网,围在哨楼附近。一些羊毛涌如今上面,那是企图穿过铁丝网的山羊留下的。
一天夜里,哨兵听到山谷中传来了叮当声——一群境外的牛闯了进来,它们脖子上的铃铛不断扭捏。
士兵们急速出动,骑着马冲进山谷,将牛赶了出去。
支普齐哨所的狗,领土意识很强。它们大体分为3个“部落”:连队的军犬、山里的野狗以及和人类混熟的野狗。
那些和人类混熟的野狗,彷佛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主人。白天,它们和哨兵一起站哨,守望着支普齐;夜里,它们冲进山里,和野狗、狼斗殴,守卫自己的领地。
士兵们乐于收养这些野狗,乃至给领头的那只野狗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天狼”。
“天狼”有时会帮着士兵们放牧,早出晚归;有时,它会躺在哨兵们的脚边,纵然身上被哨兵恶作剧般堆满了石子,也
“军马、军犬,还有每名边防军人,都是支普齐哨所的一分子,都是‘活界碑’。”俞湘剑说,“守卫这片国土,很光荣。”
俞湘剑相信,一旦有情形,这里的每个兵都能往前冲,都能捐躯奉献自己的统统。
支普齐哨所的中央,是两层楼高的国旗杆。这个旗杆也是营区最高的标志物。“国旗在这儿,便是宣示主权。”俞湘剑说。不过支普齐的国旗不大,只有天安门广场上国旗的五分之一。
2019年9月,支普齐迎来第一批军事。他们为支普齐带来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壁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过的巨大国旗。这面国旗至今珍藏在支普齐哨所。
夜里,晚点名在国旗下进行。这时,何光荣喜好举头望一眼星空。在支普齐哨所的5年里,他已经学会通过不雅观察星星来判断隔天的景象——如果满天繁星,第二天会阳光明媚,太阳能发电基本可以知足供电需求;反之,光伏板得不到足够的光照,须要用发电机赞助发电。
入冬之后,这里的晴天越来越少。官兵们愿望着来年“开山”。“汽车开进支普齐的那一天,便是‘开山’的日子。”何光荣说。
这,并不随意马虎。从最近的边防哨所到支普齐哨所,要翻越2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达坂,驶过361个转头弯。纵然在夏季,这段路途也要耗费一些韶光。冬季,道路被冰雪粉饰,车辆、职员无法通畅,“开山”变得尤为困难。
到了5月尾,哨兵会望着东边的山头——当山顶的雪逐步溶解,货车会跟在推雪车后面,驶进支普齐。
货车驾驶员聂小波,是每年最先来到支普齐哨所的人之一。“哨兵就像界碑,看到他们就知道,支普齐到了。”他说。
冷 暖
每年的1月到3月,是支普齐最冷的时候。穿着羊皮大衣的哨兵,会在哨位附近跑步取暖和。“如果有热水,就可以进行‘泼水成冰’的游戏。”马永辉说。
即便是夏天,昔时夜多数战友换上丛林迷彩时,这里的边防军人依旧穿冬季作训服……
为了抵御寒冷,“锅炉班”战友站哨时会在棉手套里再加上一副小手套。即便如此,在值班日志上具名时,他们常常冻得抓不稳笔。
不过,马永辉以为,真正“冷”的是四五月份,“由于储存的零食基本花费完了”,很难熬。
马永辉喜好喝饮料,“锅炉班”所有战友也是如此。一定程度上,这成了年轻边防官兵的分外消遣办法。
“锅炉班”的事情范围很广:焊接杂货间门锁、铺整房顶棉被、接续菜窖电线、维修军用器材……
韶光久了,马永辉有些迷茫。他担心家人不理解,认为自己只会烧个锅炉、铲个焦炭、清个炉渣、焊个电焊。
“我们的事情,更多是围着哨所生活转。”何光荣知道,实在大部分人都很认可“锅炉班”,“我们实实在在办理了哨所很多问题”。
2019年年底,何光荣胸前多了一枚三等功奖章。“锅炉班”每个人心里都暖暖的。
刚到支普齐,何光荣感想熏染到的只有“冷”——条件艰巨、路途迢遥、荒无人烟、没有旗子暗记。“服役期满就退伍。”他想。
一个冬天过去后,何光荣的想法变了。
一次开饭,上尉祁存年创造,自己饭桌上摆着刚出笼的热馒头,而阁下桌上是有些塌的凉馒头。何光荣记得很清楚,祁存年大发雷霆,餐盘顺着窗户飞了出去。
此后,这里的每一任司务长都坚守一个规矩:所有饭桌上的食品都一样。
让支普齐哨所全体官兵铭记在心的一个日子是2019年9月20日。
这一天,“锅炉班”正在维修板房。中国移动的技师来了,他们安装好了旗子暗记吸收器。
俞湘剑凑集了所有战友,给每个人都发了手机,“旗子暗记通了,大家快试试。”
“激动的心,颤动的手。”马永辉愉快地叫了出来,蹭着俞湘剑的手机热点,登上了微信。
这是支普齐第一次有了移动旗子暗记。马永辉换上便装,拨通了家里的视频电话。
没有人接,马永辉有些焦急,又拨了过去。
这次,母亲接了。当时,母亲正在家中菜园种菜。
看到屏幕中的母亲,马永辉忍不住哭了——他已经一年多没见过母亲了。
“这间屋子里的人特殊讲感情。”何光荣说,如果在“锅炉班”待得足够久,就会创造这是一间特殊热闹的宿舍。
熄灯后,他们光着膀子、打动手电、蹲在床边,泡着当下流行的火鸡面,为放多少辣椒争得面红耳赤。
上一个冬天,全班共吃掉50箱泡面。调料吃腻了,他们就加入火锅底料煮着吃。今年,泡面换成了火鸡面,口感有所提升。
安歇时,“锅炉班”会进行扑克大赛。打到白热化阶段,每个人都开始藏纸牌。有人藏在毛毯里,有人坐在屁股下,还有人塞进衣服里,时时用眼睛顺着领口偷瞄。
在支普齐的日子总是温暖的。这些年轻小伙聚在一起,逐渐把这里当成了“家”。
2019年,2名上等兵面临退役。何光荣趁货车来的机会,给两人各买了一条烟作为礼物。“班里就属他们吸烟多。”他说。
烟盒的包装上印着蓝色星空。这个牌子的烟,何光荣也没抽过,只是以为那星空和支普齐的银河有点像。
终极,两名上等兵谁也没舍得走,都晋升了士官。
下士张健在掩护氧气设备。亢红然、赵靖松摄
扎 根
在支普齐,暖和的时令只是白色冰雪中的一个逗号。
由于大雪,很多生活中极为大略的事,在这里变得非常繁芜。
那年农历八月十五,大雪突降,山路被堵。
3天后的夜里,送菜的货车才载着月饼开进来。那天晚点名就一个流程——领月饼。在贺永玺印象中,那是最短的一次晚点名,也是最迟的一个中秋节。
上尉俞湘剑第一次参加支普齐巡逻时,也碰着大雪。
那年6月,山谷间落了半米厚的积雪。看到马道被遮住,俞湘剑意识到,自己被困住了。
“当时我们只穿了秋衣秋裤,又冻又饿,真怕就撂在这了。”俞湘剑说。
好在同行的民兵找到一条通往附近村落落的路。在那里,官兵和修路工人朝夕相处半个多月后,被直升机接走。
从空中俯瞰支普齐的群山,俞湘剑明白,要在这里扎根,就必须自给自足。
于是,官兵们开始建筑温室。葫芦瓜、四季豆、黄瓜、西红柿、蒜苗、小白菜……开始在支普齐哨所的大棚里成长。
一级军士长杨发红尝过一根温室里结出来的黄瓜。“有点甜,水分不算很多。”杨发红说,“咬一口以为很幸福,舍不得下口。”说话间,他连黄瓜蒂一并吃了。
后来,上尉祁存年和战友们开始在河谷里种青稞。第一年平整地皮,第二年捡石头、施肥、浇水,第三年秋日,青稞终于长出来了。
绿色,在支普齐尤为宝贵。这里土壤稀少,草和树很难活下去。
官兵们想了个办法,从河沟里将草皮和土壤铲出来,移植到营区。现在,野狗们喜好躺在草坪上晒太阳,跟不上羊群的小羊羔会留在这里吃草。
羊险些是支普齐食品链最底真个动物。“羊会被雪豹攻击,也随意马虎被狼群叼走。”边巴桑布说。
边巴桑布是“锅炉班”唯一的藏族士兵,也是支普齐哨所骑术最好的士兵。他顺理成章,承担了放牧的任务。
这是个辛劳活,一不留神,羊群就会到处乱跑。
即便如此,边巴桑布还是喜好放牧。他喜好在山谷里飞奔着追赶牛羊,指着周围的崇山峻岭,大声地说:“这里全是我的脚印。”
对边巴桑布来说,最难的是背记法规。“短的还好,长的怎么也记不住。”他挠着头说。
凌晨3点,朦胧的月色与微弱的路灯交汇,映照出边巴桑布那张武断的面庞。“我们坚守在这里,国家才能安定,家人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他说,这是每名边防军人的职责。
前不久,边巴桑布写了份留队申请书。他的汉字写得不好看,却很工致,一笔一画,方方正正。
戍边守防,要把根扎下去。边巴桑布总听俞湘剑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义务,我们要给下一代人留下点东西。”
“锅炉班”每名战友都栽了一棵属于自己的树。上等兵马鹏忠种的是红柳。这种树很有“韧性”,但在支普齐也很难熬过第一个冬天。
马鹏忠将维生素片化在水里,浇到树根上,再撒一点羊粪,树基本就活下来了。
这个22岁的男孩称自己是“支普齐最靓的仔”。参军时,他在志愿书上填了边远艰巨地区。
支普齐哨所草地上的石头、板房内的墙壁,都印着“快乐守防”字样。
“心态很主要。”马鹏忠说,周末可以跟家里通个视频电话,还能和战友们一起打打游戏,日子就有了盼头。
支普齐哨所的演习器材基本都是官兵自己做的。马永辉的得意之作是室外的健身器材。“我们自己用角铁、方钢、水泥焊接成的。”他说,“设计图是俞湘剑画的”。
新兵们用这些器材演习,成绩有了提升。马永辉充满自满:“没有的东西,我们造;坏了的东西,我们修。”
晚饭前,支普齐哨所迎来难得的惬意光阴。值日员忙着打饭,将一盘盘热菜端到餐桌上。食堂的电视切换到音乐频道,屏幕里的歌手正唱着《怀念青春》。一名战友站在电视前,盯着屏幕。不一会儿,他哼着曲子,身体随着扭捏起来。
“饭菜按时出炉,房间温度恰好,供电也没问题……”看着统统运转正常,何光荣笑了。
这,该当便是家的样子。
(本文刊于《解放军报》2021年1月29日第5版)
来源: 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