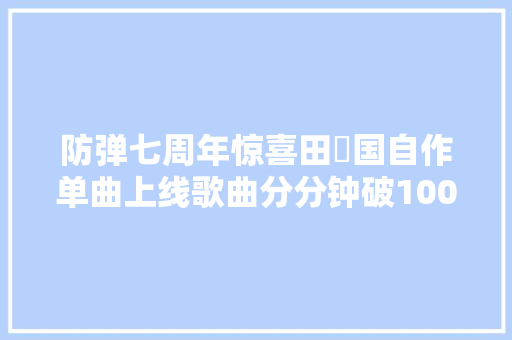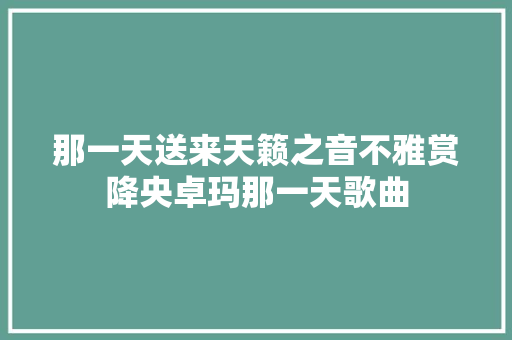除阿飞那优柔、绵延着的声线外,让人遐想的通感,可能还是源于情歌背后的那段熟习的故事。仓央嘉措曾位居极顶,作为宗法谱系中的大活佛,作为世俗眼中的情僧,身染尘凡天下,他同样旁边不了自己命运。
读仓央嘉措,实在最让人唏嘘的大概便是那飘忽的命运感。这份唏嘘,也为后世的音乐供应了难得的灵感与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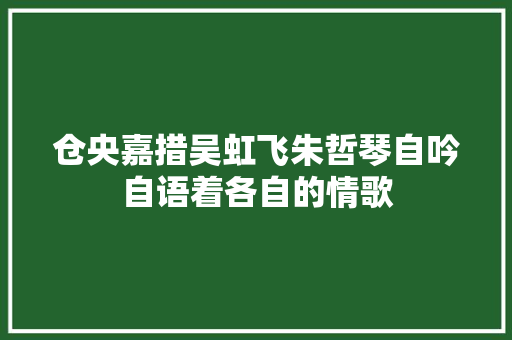
几年前我去了西藏。浩瀚先容藏传佛教、西藏地理的书让人花眼,回来时,除了几张舆图外就背回来一本书——《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及秘史》。这是一本汇总书,西藏公民出版社把约十种版本的仓央嘉措情歌的汉译集结成册。
归途,五月初的藏北高原、可可西里刚刚泛出一丝青色,便把剩下的胶片都交给了青藏铁路沿线的牧民、村落舍,把余下的大部分韶光交给了情歌秘史。公元1707年,也便是康熙主政的第46年,25岁的仓央嘉措被押解前往北京走的也是这条路吧?大体方向该当是同等的,经青海湖、西宁转道汉地。三百年的众说纷纭,无论是那年仓央嘉措客去世青海湖畔,还是他耸身一摇逃离桎梏云游天下,三百年的历史云烟都让我以为迢遥。就像我的这次西藏之旅,同样有种缥缈感。西藏展示给我的还不能说是“神秘”,它仍在我的“形而下”,路遇等身叩拜的朝圣者、在扎什伦布寺乱七八糟的僧房间徜徉、稀里糊涂折进木如寺听经、在大昭寺前坐在朝拜者中间他们抢着来合影、在纳木措气喘吁吁地爬山览景……每天总能碰着些陌生,让你置身快乐的轻盈之中。这便是云游的快乐吧?三百年前,仓央嘉措也该当是快乐的吧?无论是肉身圆寂,还是连续浪迹尘世,他终于从胁绑着他的政治旋涡中宽余出来。
布达拉宫一角(心花小记/摄)
“喇嘛仓央嘉措,别怪他风骚落荡,他所追寻的,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仓央嘉措悲欣交结的生平映渲染一个时期的动荡。作为藏地权力的一极,他位及“圣王”、“佛王”之尊,却未及获至其威,便在时期政治力量的竞赛中如一片掉入旋涡中的落叶,荡几荡,漾几漾,又被抛至不复之境。他出生前一年,五世达赖去世,摄政西藏的第司(官名,管理政务)桑结嘉措认定他为转世灵童。五世达赖去世,桑结秘不发丧,直到15岁那年,在清廷的册封下,仓央嘉措才开始坐床。大概便是这15年的民间生活经历,让仓央嘉措与史上的列位达赖喇嘛有极大不同。桑结,五世达赖对他极为看重,大天子康熙后来还诏封他为“土蕃特国王”,是个握有实权的人物,可以说仓央嘉措一贯在他的掌控之下。
历史每每又不是一个新王年幼、辅臣暂且主政的大略故事,围城之外每每也还有其权数的垂涎与参与。当时对西藏同样享有法定监护权的还有准噶尔和硕特汗——拉藏汗,更何况在所有的相互管束之上还有身在北京的大清帝皇。桑结嘉措与拉藏汗的抵牾在五世达赖去世后日益激化。仓央嘉措一开始就作为一个政治斗争中的筹码被推上了繁芜的政治舞台,而他自己并未觉察。坐床后,这个15岁的已经自由惯了的少年在严格的监督下开始学经,开始了高墙深院、戒律森严的宫廷生活。
话题说到这儿,还有浩瀚细节须要我阐明,比如斗争升级到拉藏汗杀掉了桑结嘉措,比如仓央嘉措由达赖喇嘛跌为囚徒,比如各类他逃逸的另类传说……但这已超出了我的本意,我更想谈的是情歌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几段音乐。关于仓央嘉措的放浪形骸,是短缺担当还是更接本真,关于诸多历史细节,早有多重解读,我不再绕舌。
八阔街上的黄色的玛吉阿米(心花小记/摄)
本日,盛行文化早已经使仓央嘉措的传奇得以遍及。在拉萨,我特意去了有名的“玛吉阿米”,一栋因风骚而留名的屋子,一栋因诗歌而有名的旧迹,在八阔街上,这栋漆成黄色的屋子很好找。在江湖牛人温普林的描述中,玛吉阿米这家酒巴很格调,是收容全天下浪子们的家乡。遗憾,2007年5月的下午,玛吉阿米在我眼里并不亲切,稀散的几个同类与鬼老,各怀苦处地歪在那里,晾着他们的脚丫子,午后的阳光里,八阔街上的善男信女们在我们脚下贱过,阴影中的我们远没人家温暖、惬意。这里是间名叫玛吉阿米的酒吧,和人家名叫玛吉阿米的少女没啥关系,光阴早就消弥了仓央嘉措留下的蛛丝马迹。
三百年前,白天,仓央嘉措是庙堂上的密法佛徒;晚上,则从布达拉宫偷偷跑出来,戴上假发,化身为宦游于酒肆、民家及拉萨街头的浪子宕桑旺波。大类艺术天子宋徽宗,六世达赖身后留下的遗产,最生动的,也是这个宕桑旺波的篇篇《情歌》。“在那东山顶上,升起了皎洁的玉轮。玛吉阿米的脸庞,浮现在我的心上。”这大概是仓央嘉措写下的情歌中传唱最广的一首,很多选本都把它列为了第一首。睹月思人,你我俗人亦不免,在林芝那天刚好月圆,刚好升起自东山上,那时才理解这首诗的慰帖。玛吉阿米,这个词用汉语很难直接表达,有人译作未嫁少女、佳人、未生娘等,个中未生娘的说法很贴切。对此,庄晶老师理解得好:玛吉阿米并非指“没生养过的母亲”即少女,而是指情人对自己的恩典像母亲一样,虽然她没生自己。诗歌每每是不可翻译的,比如唐诗译成英文,韵致全消,你只能加强想象去预测理解了,以是翻译藏诗存在很大的多意性,仓央嘉措情歌的汉译版本极多。我先挑两个此诗很汉化的版本列示一下。曾缄师长西席是这样译的:“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宛如彷佛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有种叶芝《当你老了》尾句的意味。而刘希武的是:“明月何玲珑,初出东山上,少女面庞儿,油然萦怀想。”读来颇含古意吧?
吴虹飞,当年贵州的高考状元,清华理科生,幸福大街主唱,南方系主流,网上的口不择言者,一个充满话题
该转头说说吴虹飞了,三百年后,吴虹飞站在2008年又唱了一遍《情歌》。
春天的时候,幸福大街出了第二张专辑《胭脂》。有趣的是,那年三月《南方人物周刊》在点评当代有影响力的跨界人物时,把自家旗下的吴虹飞列入,身份是作家兼摇滚歌手,呵,举贤不避亲。从声音,话语权这个角度,作为一个歌者,幸福大街主唱吴虹飞一贯徘徊于边缘之外,仅停在一小部分好事者的耳旁;可作为一个,吴虹飞却是南方集团的一部分,在中国话语体系中占了一席。搞独立音乐的文艺青年,客不雅观记录的访谈,这两个身份融在一个人身上,是不是有些分裂?很多评说者把《胭脂》冠以幸福大街的转型之作。实在,真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歌唱是很难的。原来她们就真正地有什么“型”吗?“胭脂”,古里古气的,是个已经快消逝了的词语,胭脂是阴性的,胭脂是女为悦己者容,又是女人的自我保护,厚厚的胭脂涂在脸上,女人就可以躲在了后面,浩瀚胭脂都要被岁月之水洗掉,不再年青的女人大概要用更多的胭脂包装。以“胭脂”命名,幸福大街落在了哪个点上?《胭脂》不难听,没啥子野心,像老歌翻唱一样。吴虹飞是侗族人,但估计她不会唱侗族大歌,很多人说她“带着南方口音与湿气”,我以为她彷佛很童稚,又彷佛往事苍老。《胭脂》的语意依然晦涩,但在旋律上却有些刻意地舒缓、流畅、一波三折。
《仓央嘉措情歌》收录在《胭脂》里面,原词曲作者是个西藏的年轻的时髦活佛——至尊日波益西仁波切,吴虹飞系翻唱。日波益西仁波切是个“80后”,上网,出唱碟,照酷照。要搁在三百年前,也算是放浪形骸了,可现在是公元21世纪,这叫与时俱进。仓央嘉措受人崇拜,是带着宗教意义上的顶礼,而日波益西仁波切受更多人喜好,和喜好帅哥蒲巴甲在理儿上差不离。小活佛的藏语版《情歌》很磁性,节奏明快,吉它与曼陀铃两件西器伴奏;小活佛的汉文版的繁芜了些,用了古筝等汉族乐器,加了室内电子合成,译词也用的是曾缄师长西席的古意版。吴虹飞翻唱的《情歌》软软的,浅唱低昑,是她的小女人优柔面,是对发出过《嫁衣》、《现场》、《泼皮》等狠恶声音的平衡、勾兑。
年夜家唱着年夜家的歌,吴虹飞对自己评价还是到位的:“借尸还魂”。无论是小活佛或女阿飞,他们唱着仓央嘉措,但还原出来的实在都是那个与自己跬步不离的隐形之“魂”。
吴虹飞修正了小活佛的歌词组合。全词如下:
“那一天,我迁徙改变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不为来生,只为你的温暖;那一世,我转山转水,只为途中与你相见,转山转水转佛塔呀,只为途中与你想见。天上的仙鹤借我,借我一双洁白的翅膀,我不会远走高飞,飞到理塘就返回。山顶升起皎洁的玉轮,你的面庞浮在我心上,你那俏丽的面庞悄悄浮在我的心上。”
必须一提的是,前边那几句,绝对不是出自仓央嘉措的情歌,看风格便扞格难入。在我的阅历里,这句最早涌如今朱哲琴的《信徒》中。何训田在作《信徒》时,是引用或改编,我不知道,也可能是陆忆敏写的。《信徒》的歌词是:“那一天,闭目在经殿的喷鼻香雾中,蓦然听见。你诵经的真言;那一月,我迁徙改变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呀,不为修来世,只为在途中与你相见。”如此歌词,是心性的祈祷或告解,往小了说,可以说是爱情,往大了说,却是悲悯的大情怀,是对终极的追求。网上也有人翻改过段词,加了好多进去,从这一刻开始,加了玛尼堆、风马旗、修德等很多成分,切实其实是狗尾续貂,大煞风景,还枉称仓央嘉措所作。
朱哲琴,Dadawa,是心花
《信徒》曲风的基调是印度风格,节奏性强,和仓央嘉措并无太大干系,倒是《信徒》所在的《央金玛》专辑里,另有一首真正献给这位先师的情歌——《六世达赖情歌》。终于引到朱哲琴或者说何训田这对双子星出场了。喷鼻香港回归那年,我初听《六世情歌》,只能用震荡来形容!
前面说过年夜家都唱年夜家的歌,“借尸还魂”,那么朱哲琴与何训田呢?
听朱哲琴的音乐,我从来不用去管歌词,关注的只是音乐中包括人声在内的各种声音,听它们琴瑟合鸣。彼时,对仓央嘉措及《情歌》也略知一点点,在那往后的好多年里,我一贯不太理解何训田在音乐的后半程何以做那般黄钟大吕的恢宏表达。何训田彷佛也
何训田从浩瀚情歌中选取了七段,组合起来,使它具备了线性的表达。下面我想考试测验一下能否用措辞还原这首歌的情境,“说”出我听它的感想熏染。
吱呀呀,木门被推开了,乐曲从这里拉开帷幕,然后是迎面而来的风,低低地啸着,一波一波地从远处吹过来,浪子宕桑旺波出门去会情人了,咯吱咯吱,脚步踏在了雪地上,沙沙地走得有些急,好安静啊,好安静,汪汪,阁下传来了狗叫声,哦,这是一个冬天的雪夜。从迢遥的天边那里,音乐渐起,伴着近处的狗吠,很低地升起……“哦嘛呢嘛”的箴言声中,朱哲琴的声音登场,同样是轻轻的,“在那东方山顶,升起皎洁玉轮,年轻姑娘脸庞,逐渐浮现心上……”浪子的心呀,还是拴在温顺的玉轮与姑娘那儿。情歌与箴言混着,我们一块儿来到了雪域佛界,人界与佛界也殽杂着的吧?一点点地,我们的耳朵在室外醒来,各种声音也就随着一点点醒来,加入到乐音里,敲击金属片的细碎的节奏声,低低鼓声,长长的电子主音……“薄暮去会情人,黎来岁夜雪飞扬,莫说瞒与不瞒,脚印已留雪上……守门的狗儿,你比人还机灵,别说我薄暮出去,别说我拂晓才归”,仓央嘉措诉说着,这时诉说有了回响,在朱哲琴带着紧匆匆的平叙中,箴言依然一波一波地回响着,而回应她的伴唱,旋律是悠扬的,女声是和声,男声是单音,男声高亢,男女声之间是有层次的。音乐至此,已经通亮了许多,深宫外的天下不是冷色调的了,是有温度的,一只笼子里的杜娟回到了林中,能不愉快吗。“人家说我的闲话,自以为说得不差,少年我轻盈脚步,曾走过女店主的家”,女店主便是玛吉阿米吧?“常想活佛面孔,从不显现面前,没想情人容颜,时时映在心中……住在布达拉宫,我是持明仓央嘉措,住在山下拉萨,我是浪子宕桑旺波”。仓央嘉措的独白说到这儿,乐曲进入了迁移转变。在朱哲琴不断的重复声中,“嘛哩嘛哩……”乐音渐次升起,升起,渐强,渐强,越来越亮,越来越亮,高潮终于到来,化作一道白光,那是闪电,已经不再置身阴郁了,乐曲跳到了白天,已经不是圣城拉萨的市井了,乐曲跳到了藏北广阔的高原,已经不再是那个身心分裂的布达拉宫的双面圣主了,历经磨难、虚幻的仓央嘉措在被押解到藏北的时候得到了真正的解脱,他变得轻盈、高蹈。闪电后,雷霆轰隆隆地炸响,雨声中,何训友的高亢的男声响彻草原,那该当是场太阳雨。大合唱的舞蹈中,朱哲琴的声音也陡然拔高,用多种措辞唱:“喇嘛仓央嘉措,别怪他风骚放荡,他所追寻的,和我们没有两样。”雨后的阳光里,高原回荡着一片金色的欢快之光。
在一种大欢畅的结局中,何训田完成了他的礼赞,对自由对生命对本真的礼赞。
成都府南河,那时她们那么班配,黄金差错
于
仓央嘉措情歌到底有多少首不得而知。在浩瀚乐与苦、爱与憎、沉伦与升腾的小调中,有一首亦格外抢眼:“白色的野鹤啊,请你借给我翅膀,我不去远方久歇,只到理塘就转回。”吴虹飞在翻唱时,也把它引用了。藏地三塘,理塘是我的最先神往之地,那里有稻城,有圣山,有夏诺多吉,有央脉勇,有仙乃日。这首小调可谓仓央嘉措短暂传奇的生平的写照,乃至说是生命留下的绝唱,它包含着一则寓言。听说,仓央嘉措圆寂后,人们探求转世的七世达赖不得要领,就去噶玛沙那里请示。那里的护法神附了人身后,只拿出一壁铜锣来敲了一下。当时人们都不明白喻意。等到达赖在理塘转生的传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做锣的铜在藏文叫Li(理),若把锣一敲就发Tang(塘)的一声响,这不明明白白地说达赖要在理塘转生么。以是,仓央嘉措的浩瀚情歌,你一定要放在藏传佛教的宗教氛围中,多从开悟、聪慧着想,若仅仅把它理解为狭义的男男女女,那就太过偏狭了。
情歌唱完了,仓央嘉措转身离开了,七世达赖又循环到人间,之后有八世、九世……【心花社出品】
时髦的至尊日波益西仁波切
附日波益西仁波切汉文版《情歌》歌词,用的是曾缄的译文: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宛如彷佛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我与伊人本一家,情缘虽尽莫咨嗟。清明过了春自去,几见狂蜂恋落花。跨鹤高飞意壮哉,云霄一羽雪皑皑。此行莫恨天涯远,咫尺理塘归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