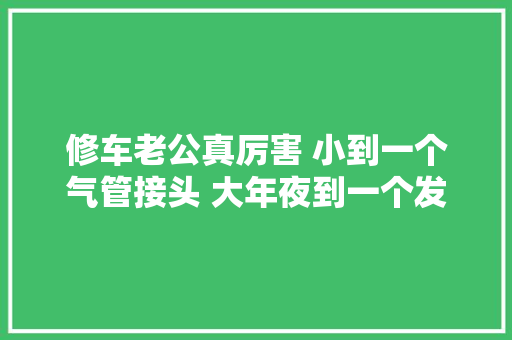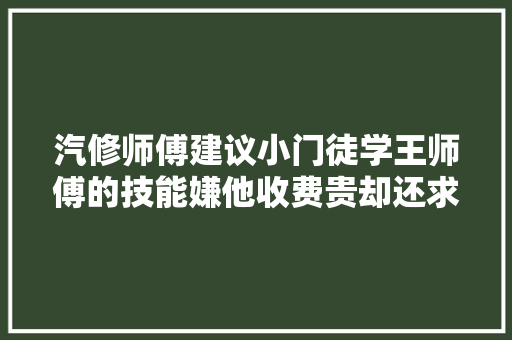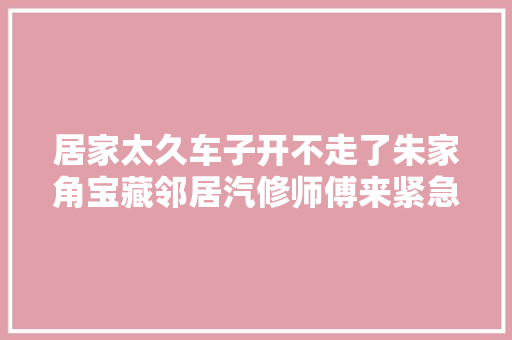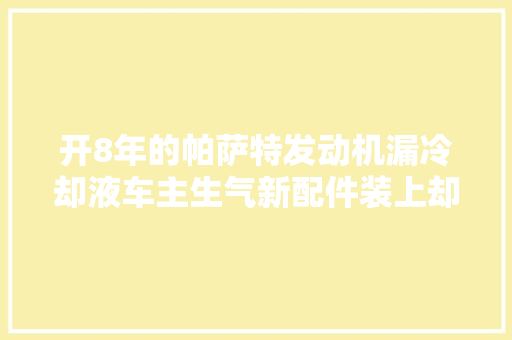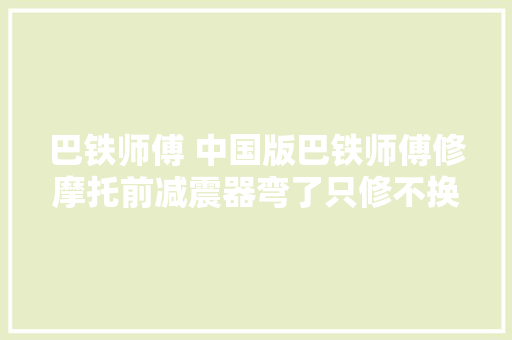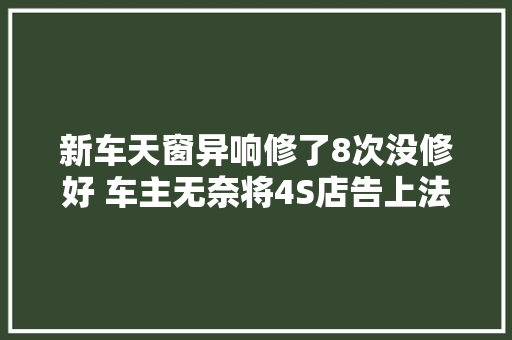老城修车匠
文丨甬上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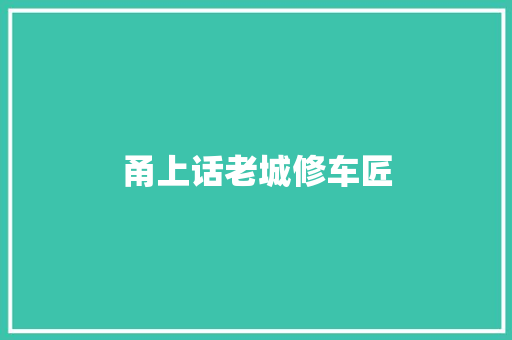
宁波老城区一个菜市场对面的犄角旮旯里有个修车摊位。摊上有位修车匠。
这位修车匠怎么看怎么有趣。
大家别误会,我说的修车匠,绝不是修汽车的。
这是一位修脚踏车、也便是修理自行车的师傅。並且是老板兼修理工。
先前在军队时,由于怕出车辆亡人事件,高层严令非体例驾驶员动车、开车。领导们说:“安全便是政治”!
一旦创造你不是驾驶员而开车,轻者大会小会狠批,重者挨一个处罚。
政治问题可不是小事情,不讲政治是当代中国军人之大忌讳。以是,很听领导的话,很讲政治,绝不开车。
正由于绝不开车,以是也不学开车,以是也从不会开车,只会坐车。只会坐别人开的车。
等自己成了短序导,在一亩三分地有话语权和决策权时,也严令别人绝不能开车。以身作则,自已也从不动车。
到思想比较解放的高层领导掌权,放开了非驾驶职员开车的禁令,提倡军官自已开车的时候,却退休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成了专用交通工具。
十年用下来,车子除了铃不响,哪哪都响,到处生锈。十年换了两个铃,于是铃也响。尤其是后轮刹车,蹬一圈响一圈,骑一起响一起。
十年间,修了无数次车。修车只能到就近的小摊去修。附近先后有三个修自行车的路边摊,都去修过“永久”。
前几年的时候,城市的街头,自行车修车摊作为和每个骑自行车的人都息息相关的摊位,很频繁得涌如今城市的各个十字路口、小区角落。仅在老城区短短的一条咏归路上,就有三个修车摊点。但是这两年骑着车走在路上的时候,每当车子涌现了小问题,须要补胎或者打气,乃至是换闸线,车把,车座什么的时候,去世活找不到修车摊了。
许是由于公共自行车和随处可租的自行车多了,拥有私家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险些没有。因此,自行车修理这一很火爆的职业黯然退出大街小巷,基本上消亡了。最近两年,常去的三个点位,有两家也撤摊不干了。剩下了一个仍旧坚持的小路边店。车有缺点了,小毛病自己搞掂,有点技能含量的只能去找他了。
听口音,这是个从大西南到沿海地区来打工谋生的师傅。
不雅观长像,这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小平头,矮个子,小圆脸,瘦瘦小小。五官布局很“西南”。
看表情,总是板着小圆脸,很严明的样子,从来没见他笑过,或者是稍有笑意。
论派头,这绝对是个昔时夜领导的人,时运不济,无奈沦入小手工业者的行列。
一次去修车,摊上无人,师傅正蹲在店里用电炉做早饭。你见告他有个小毛病,赶韶光,麻烦帮忙修修。他却蹦出三个字:吃完饭。从做好到吃完,最少半小时吧。实在等不起,无奈只好走人。
一次去修车,师傅问:怎么了?答:到处响,声很大。问:你自己的车,你不知道什么毛病?!
答:不懂。师傅说,这破车,凑合着骑,还修它干嘛?看来他不想接这单小买卖。
一次去修车,师傅问:怎么了?答:到处响,声很大,尤其是后轴齿轮磨擦的厉害。师傅看了看,仰起小脸,煞有介事地说,没事,不用修!
一次去修车,师傅问:怎么了?答:老毛病,到处响,声很大,尤其是后轴齿轮磨擦的厉害。师傅顺手操起一把长长的螺丝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知在哪里撬了一下,然后掂起后座,迁徙改变后轮,说:“好了”!
居然真的是不响了。问:“多少钞票”?答:“5元”。不花本钱、不换零件、不费功夫、顺手一下,不敷3秒钟就赚了5元。这便是吃技能饭的好处,谁让人家身怀绝技呢。
一次去修车,是后轮的毛病,一根幅条断了,想换一根。师傅的办法是,把断了的这根缠在阁下没断的一根上,说,没事,只管骑。哪就这样,连续骑着罢。
一次去修车,是车蹬坏了。师傅看了半天,把全体动力系统全拆下来,又在店内找了一套比原车还锈的部件换上,且说:“你这个质量不好,我这个好”。你说好就好吧。还别说,换上这看起来更破的部件,用了几年没再坏过。
一次去充气。师傅看了看,说,换个内胎。好嘛,换就换吧。
充一次气一元钱。没现金,师傅常日都是淡定地抬抬手,指指二维码,只说一字:“刷”!
车摊是一间租来的路边房,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工具、零部件、生活用品。修车只能在店外路边。店外放着一把竹躺椅,一把破的皮质办公椅。师傅除了修车,便是时常躺在躺椅上享受生活。
看这架势,不像是他在赢利做生意,却很像小老百姓去求官僚们办事情,递上笑脸,说着软话,奉上钞票。
附近周遭三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只此一家,你不找他还弗成。
过来人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前,国营商店的业务员们基本都是这德行。也不冤修自行车的师傅如此行事。
一家独大,没有竞争,爱买不买,爱修不修,爱干不干,以是师傅很NB。
这是市场规则,谁也没脾气。
(202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