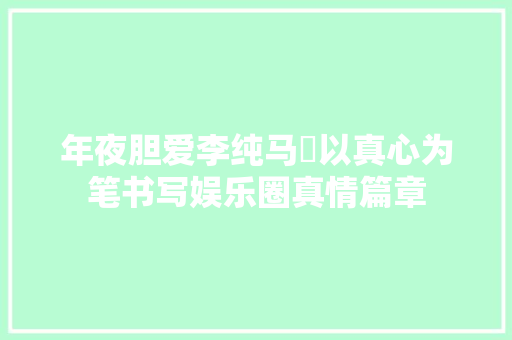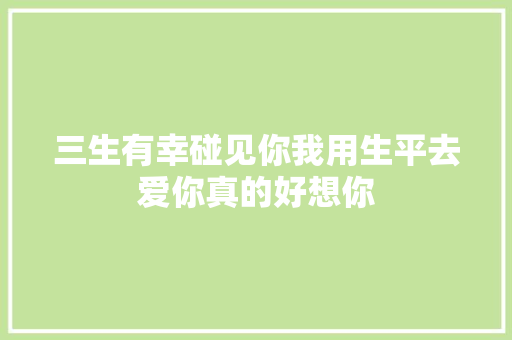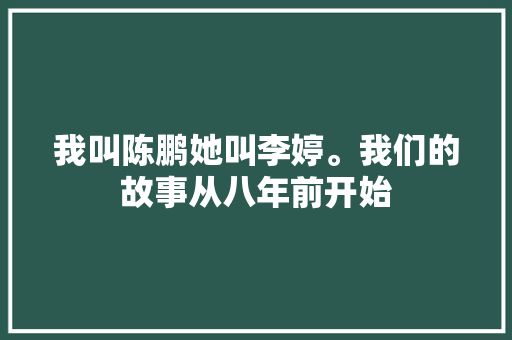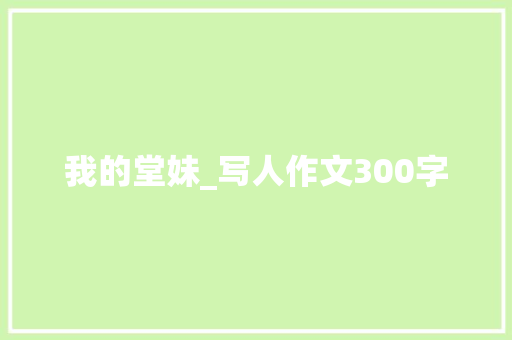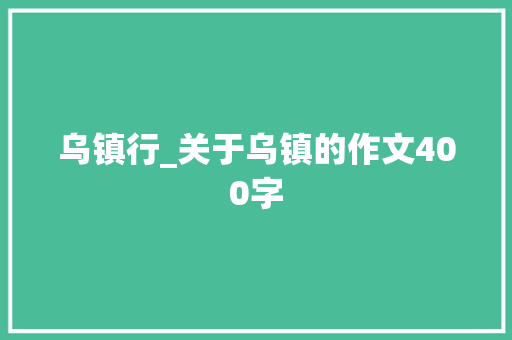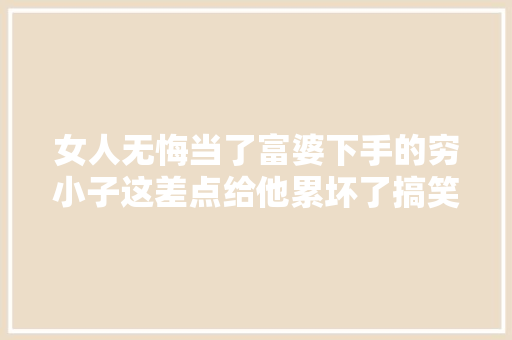对是否“便是ta”的觉得,不知从哪天起逐渐失落去了判断力;不敢表白,犹豫未定;牵手相恋后,韶光一长,却越来越以为“ta不懂我”,相互的沟通陷入窘境,使彼此经受煎熬。
爱情是人间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为什么还是会这么困难?当我们曾经接管并神往的那些爱情模式在遭遇现实撞击后,除了向父母辈的履历和言说妥协,或许也得承认“我们永久不可能像天使一样互换,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实,但又是幸运的事实”。只是,亲密关系的互换何以常常失落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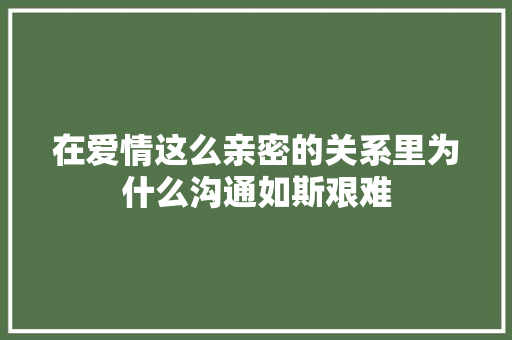
亲密关系的互换为何常常失落败?
亲密关系对我们来说陌生又熟习。有人渴望,有人害怕,它是每个人的铠甲,也是软肋。在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系过程中,我们深挚交流的主要性,却依然由于缺少互换反复陷入亲密关系中的困境。
《饮食男女》(1994)剧照。
电影《饮食男女》 是李安“家庭三部曲”的末了一部。台湾中国菜大师老朱退休后,每周日精选鸡鸭鱼肉煎炸烹炒,换着花样地摆出一桌桌色喷鼻香味俱全的丰硕菜肴,却创造三个女儿只是迫于压力来到桌前,心思早已不在这个家里。已经终年夜成人的她们,心里藏了许多比陪老爸用饭更主要的事。
类似的场景大概在很多家庭中都上演过,父辈期待子女团圆,子女却常常在寒暄过后,不知道该和父母聊些什么,只好耐着性子演示智好手机的用法,删繁就简说说生活的现状,像是在例行完成公务。对父母,彷佛永久心怀愧疚,却又无法心甘情愿。
互换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从生理上说,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无法与另一个对接,其末梢神经的终端是自己的大脑。从生理上说,人类的感知和感情细微而独特,具有唯一性。人与人之间的思想的隔绝,是人类最根本的特色之一。“这样的思想之间的隔裂,是自然界中最绝对的隔裂。” 人类的历史上互换失落败的悲笑剧和荒诞剧比比皆是。
1837 年,丹麦宗教哲学生理学家、墨客克尔凯郭尔认识了雷吉娜,这位15 岁的少女爱上了他。在订婚往后,克尔凯郭尔以为自己该当把内心的感想熏染见告这位未来的太太,好使得往后可以相互分担忧患、痛楚,可是当他把自己内心的所有忧郁,尤其自己有两个原罪,将来会下地狱的感想熏染见告雷吉娜的时候,雷吉娜当时只有17 岁,不能接管如此古怪的、颓丧的思想,把他所说的只有一笑置之。克尔凯郭尔在一封未发出的、给关系破灭的未婚妻的信中写道:“感激你从来就没有理解过我的意思。”
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年—1855年),丹麦宗教哲学生理学家、墨客,被认为是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当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
随着年事的增长,我们不得不承认,亲密关系不亲密
当代都邑的亲密关系中,不稳定性彷佛才是永恒。我们喜好听木心说,“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生平只够爱一个人。”但是,那是从前,或者只是我们对“从前”的抱负。当你真的走进“从前”的人的生活中,可能会创造,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童话故事只见告你,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至于生活在一起之后,事情如何发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白雪公主”是关于王子与公主幸福生活在一起的故事之一。图为《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1937)剧照。
何况现在年轻人会想,生平只爱过一个人,怎么知道ta是最得当的,怎么知道那便是爱?数学家给出一个方案:打仗并谢绝掉前面 k 个人,不管这些人有多好;然后从第 k+1 个人开始,一旦看到比之前所有人都要精良的人,就绝不犹豫地选择ta。欧拉推导出了一个数学公式,末了解出K的最优值是 37%。比如,你估量求爱者有10 个人,那该当先谢绝前4 个,从第5个开始,一旦创造比前4个都好的,就果断发offer。或者,假设你从18岁开始找工具,35岁之前结婚,那么根据37%法则,分割点便是24岁。那你的择偶策略便是,24岁之前是不雅观察期,只交往不结婚,但要记住交往的人中最优质的那个;24岁之后是决策期,在此之后一旦碰着比之前那个好的人,就准备进入婚姻殿堂。
数学决策看似科学有效,却也会在现实中遭遇滑铁卢。和越多的人交往,对爱情的期待和投入反而减少,或是不敢深爱或是累觉不爱。如果你有幸或不幸拥有多个前男友/前女友,就会创造,他们千姿百态,每每说不清谁是那个可以用来比对的“最优质的人”。乃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爱情持悲观态度,戏言爱欲不过是一瞬间的化学反应,凡夫俗子大同小异,这辈子和谁过都是过。
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嫁入豪门,最少门当户对。《非诚勿扰》成为征象级综艺,不仅是由于大家都有一颗八卦的心,还由于节目中很多“偏见”和看似荒诞的哀求,实在是很多人不敢说出口的希望。当精神层面的哀求不断降落,物质方面的需求自然节节攀升。
但是,为了知足本能的对归属感的需求,我们的内心仍无法抗拒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即便以符号为媒介进行互换的任何考试测验,都是一场赌钱,我们依然无法放弃建立联系的努力。即便如飞蛾扑火,我们依然希望找到一个人,建立真实的联结,用“最真实的自我”抵达另一个“最真实的自我”。
然而,随着年事的增长,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尴尬的现实,亲密关系不亲密。人类早就用具有“相互互换的能力”来给自己下定义,但互换不但是言说,而是盘根错节的思想和文化问题,隐含着自身和时期的冲突。
《花样年华》(2000)剧照。
在王家卫导演的电影《花样年华》中,上世纪60年代的喷鼻香港,苏丽珍和周慕云两家人住隔壁。有一天,他们创造各自的爱人竟彼此出轨。敏感、孤独、不解,作为情绪中的受害方,他们彼此同情,又尴尬相对。他们想知道“背叛”是如何开始的,却也在打仗中欠妥心爱上了对方。但房东太太一句带有世俗压力的“提醒”,就让苏丽珍谢绝了周慕云的船票。终极,他怀着绝望离开,将统统苦处说给吴哥窟的树洞,再用泥巴封存。她也只是浅笑,轻声一语“忘却了”。你可以说,他不足年夜胆,她只顾自持,再凄婉动人不过暧昧一场。你也可以说,那是时期的悲剧,但人最难面对的永久是自己的内心。
亲密关系的核心是认识自我
在古老而当代的中国,亲密关系这一基于“自我崛起”背景的当代观点与千年传统不雅观念之间形成的张力和冲突,每每让我们困惑犹疑。亲密关系的核心是认识自我,但在我们绝大多数人自幼接管的责任教诲里,关于“自我”的哲学思考极少被提及,强调自我反而会被贴上“自私”的标签。
这不是一代人的问题。把这样的命题抛给我们的父辈祖辈,就会创造,他们要么浅尝辄止,要么顾旁边而言他,“便是做自己呗,愉快就好”、“活出自我,那得有多少钱?多大本事?”、“自我都要服从组织安排”、“别总想那些,老人言,亏损是福”……我们没有资格苛求他们去细思慢想,逻辑严密。由于到头来,我们会创造这些生活的履历和教训在现实处境中每每更实用,乃至成为规训年轻一代的圭表标准。
进入象牙塔,接管人文熏陶,大概是很多人第一次开始负责思虑,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代价、如何认识自我这些哲学问题。在一场场学术谈论后,我们彷佛逐渐寻觅到了人文之光。我们去触碰去世亡的话题,我们许可自己沉浸在“无用”的书本中,我们守卫思想自由,我们努力兼容并包。我们见告自己要不要迷信威信,时候关注内心的感想熏染。
但是,好景不长,走出象牙塔进入社会和职场,会创造我们不得不拾起那些曾经被我们嫌弃的父辈的规训,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小心翼翼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却不敢再思考作为一个个体生活的意义。
《欢快颂》(2016)剧照人物关雎尔。
在电视剧《欢快颂》中,让很多人有照镜子觉得的是关雎尔。二十多年来一贯按部就班,过着父母早就替她方案好的生活。文静内向,气质温顺。事情努力,踏实,勤奋,常常加班到深夜,为了能在年底通过考察留在公司。她是范例的乖乖女,却也被生活的条条框框束缚不已。如果作为男性,你可能以为关雎尔是个好伴侣,温顺贤惠,俨然未来的贤妻良母;可是作为女性,我会担心,回望自己的生活,她会遗憾。可是,改变是有风险的,不愿定性会让我们徘徊、纠结、患得患失落。
可是,这便是生活。物质的压力跬步不离,生活的可能性被不断压缩。空想与现实的落差,让我们渴望在同辈人中寻觅知音,却也意识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围城里。城外的人冲不进去,城里的人逃不出来,到底是由于缺少勇气。我们开始封闭敏感的内心天下,乃至恐怖发展。就像歌词唱的那样: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终年夜,终年夜后天下就没童话;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终年夜,我甘心永久都笨又傻;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终年夜,终年夜后我就会失落去他;
我深爱的他深爱我的他,怎么会爱上别个她;
让我们回去从前好不好 ,天真屈曲快乐美好。”
——S.H.E《不想终年夜》
可是,我们究竟要终年夜的。一同发展的伙伴们可以相互安慰,抱团取暖和,但是没有人可以帮你做决定,自己的内心还是要自己照料。偶尔的风花雪月谈天说地过后,还是要再次回归到日常的生活中,保持微笑。内心的孤独感并没有减少,真正的联结也无从谈起。交情如此,爱情亦然。
《斐多篇》中的苏格拉底将爱欲与对话相等同,两者的共同点就在于:强烈渴望打仗无法打仗的他者 。柏拉图式的爱情,典雅而浪漫。但这一遗产,作为空想,光荣而苛刻。
我们永久不可能像天使一样互换,这是一个悲惨的、幸运的事实
《对空言说——传播的不雅观念史》,作者: [美]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译者: 邓建国,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1月
美国传播学家彼得斯1999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对空言说——传播的不雅观念史》。该书在传播学界被广泛引用,截止到2015年12月,该书在谷歌学术中被引次数高达1205次。他认为在心灵的互换中,自我或天下的真实再现不仅不可能,而且永久不可能充分。我们真正须要的是甘心的自我克制。“互换的寻衅不是虔诚于我们的地盘,而是对别人报有体谅的态度,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看自己那样来看我们。”
既然不可能做到空想中的互换,我们的问题就不应该是:“我们能互换吗?”而是:“我们能够相互爱护,能够公道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尽可能弥合那些横亘在自我与他人、私人与公共、内心思想与外在词语之间的鸿沟。
彼得斯认为,人与人之间互换的问题,每每是由参与度不同和缺少耐心带来的。情侣住在一起,不仅是由于那是经济层面谨慎的做法。事实上,他们意识到或本能地认为,持续的亲近是抵达灵魂的最佳路子。想要见证另一个生命中最残酷和最灰暗的瞬间,最保险的办法便是“在场”。
还记得那些寝室卧谈吗?还记得那些深夜哭诉吗?在某个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互换的希望,倾诉的需求。同处一室时,可能一个不经意的话题,人们会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些未曾表露的感情和想法,以及生活中的点滴细节,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亲密。比较盛行的说法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饮食男女》中的老朱,在经历了失落落、不解、无奈后,也逐步想通了。虽然随着年纪的增大,他逐渐失落去了味觉感知,但依旧在周日做上一桌美味佳肴。在饭桌上他借着酒劲说:“实在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还是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个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
看电影时,深深被这句话打动。没有人天生就知道该如何处理亲密关系,那些后知后觉都因此一次次失落望、痛楚、冲突作为代价的。可也正由于如此,我们终其生平,都可以探索自我和他人的内心天下,更紧密或变释然,进退都是生活。毕竟“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毕其生平,每个人只不过有韶光给少数几个人以关爱。我们凡人能做到的,恐怕只能够是爱比较亲近的人;不过没有博爱之心又是不公道的。爱之悖论是,详细的局限性和哀求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着抵牾。由于我们只能够和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度过共同的光阴,只能够打仗一些人,因此,亲临现场恐怕是最靠近超过人与人鸿沟的担保。在这一点上,我们直接面对的是,我们有限的生命既神圣又悲哀。”
——彼得斯《对空言说》
“我们永久不可能像天使一样互换,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实,但又是幸运的事实。”统统试图实现亲密互换的努力都藏着某种怪诞。但如果乐不雅观地看待这种怪诞,奇妙地把握着分寸感,我们不仅可以免于因不合而引起的羞愧,反而可以从中得到清闲和乐趣。
作者:紫二
编辑:徐悦东 校正: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