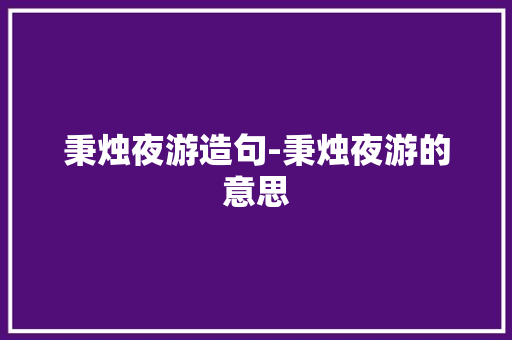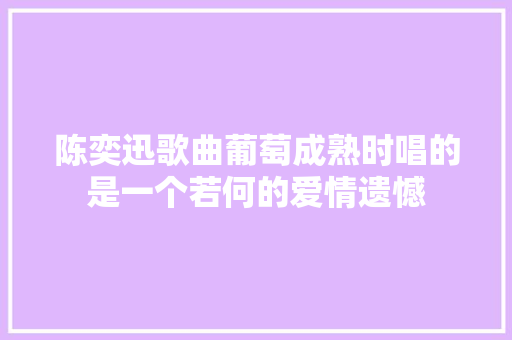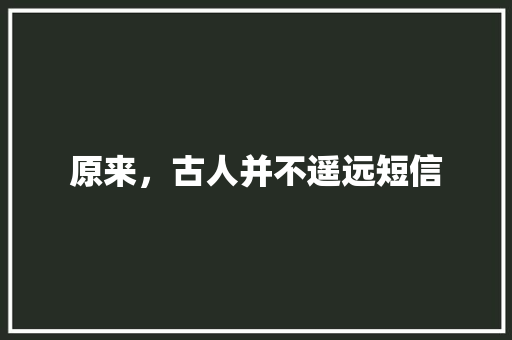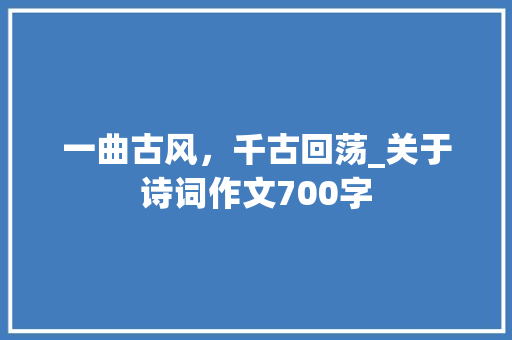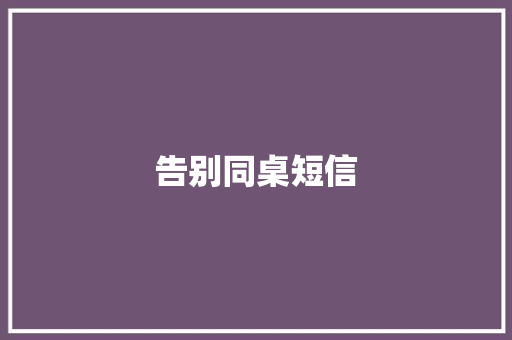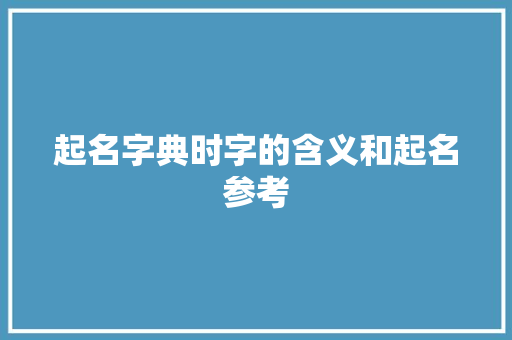蜜里调油的“蜜”
提及舌尖上的一丝甜,很难不让人想起蜂蜜的滋味。自周代始,就已有古人采集蜂蜜以食用的笔墨记录,而古人实际食用蜜糖的韶光肯定比史料文献记载更早。至魏晋南北朝期间,机警的古人已不再知足于从大自然中采集野蜂蜜,而是开始进行人工养蜂。这种采集蜂蜜的办法,不仅能够选择得当的地点,还能掌握蜂群的规模,以方便蜂农采集,同时蜂蜜也成了一个方便稳定的糖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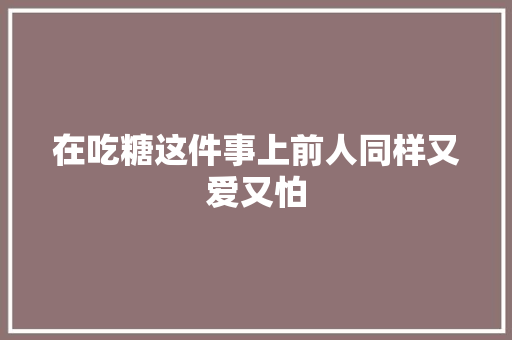
蜜源担保了,但想让蜜糖的甜味萦绕在舌尖还得先炼蜜。古人将不用火煮的蜜称为白沙蜜,用火煮的则被称为紫蜜。据《农桑衣食撮要》载:“不见火者为白沙蜜,见火者为紫蜜。入篓盛顿。却将纽下蜜柤入锅内,慢火煎熬,候融化拗出柤再熬。预先安排锡旋或盆瓦,各盛冷水,次倾蜡汁在内,凝定自成黄蜡,以柤内蜡尽为度。”明代的炼蜜技能更博识,据李时珍载:“凡炼沙蜜,每斤入水四两,银石器内以桑柴火炬炼,拣去浮沫,至朔成珠不散乃用,谓之火炼。又法,以器盛置重扬巾,煮一日候,滴水不敢,取用亦佳,且不伤火也。”
炼好的蜂蜜“白如凝酥,质量甘美,耐久储不坏”,如此美味自是要逐步享用。古人吃蜜除了最常见的用蜜兑水喝以外,蜂蜜作为甜味剂那可是在古代的餐桌上出尽了风头。秦汉期间的糕点,如粔籹(膏环)、髓饼、细环饼、截饼、茧糖等,都是在糯米粉或面粉中加入蜂蜜制作而成。南朝至隋唐时期,古人居然吃起了“蜜制的动物乌贼、螃蟹和鱼以及蜜制的姜”。到了宋代,除了各式蜜制糕点,如蜜糕、蜂糖糕、蜜麻酥、蜜辣馅饼等,蜜饯这个行业也随着蜂蜜的遍及而发达起来。此外,宋人还用蜂蜜来酿酒,苏东坡就曾在《蜜酒》诗中提到:“巧将蜜蜂炼玉液,胜似金丹万倍强。”可见这蜜酒是多么甘甜。
甘之如饴的“饴”
与蜂蜜一样古老的天然甜味剂还有饴糖。早在《诗经》中,周代人就用“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来歌颂古公亶父,意思是他带来了如饴糖般肥沃的周原地皮。可见,生活在周代的古人就已经尝到了饴糖的甜味。又《周礼·天官·疾医》贾公彦疏云:“五味,酰酒饴蜜姜盐之属者,酰则酸也,酒则苦也,饴蜜即甘也,姜即辛也,盐即咸也。此其五味酸、苦、辛、咸、甘也。”个中明确提出饴蜜是五味中甜味的代表。
饴糖之以是广受欢迎,是由于它对制作质料的哀求并不高,它由农作物萌芽后的种子制作而成。其种子里的淀粉在一定条件下,经由糖化成为糖类,古人就将其称之为饴糖。我们常见的水稻、大麦、小麦、糯米等,都可以制作成饴糖。
虽然质料好取,但要将其制成饴糖,还得经由制蘖与熬糖两个步骤。据北魏期间《齐民要术》载:“八月中作蘖,盆中浸小麦,即倾去水,日曝之。一日一度着水,即去之。脚生,布麦于席上,厚二寸许。一日一度以水浇之,芽生便止。”所谓“蘖”,是指谷物用水泡出来的芽。
在制蘖完成后,剩下的便是最关键的熬糖。古人在熬糖之前,先得根据不同的质料,对蘖与米进行不同的配比,包括发酵的韶光以及后续熬糖的火力都要有所调度。熬糖是个费心费力的活儿,得一贯守在锅边,稍有不慎,一锅糖汁就可能熬焦变黑。不同的谷物,制作出来的饴糖也有所不同。故意思的是,早在北魏期间,我们现在所吃的牛皮糖就已被熬制出来。
饴糖在古代也很有市场,魏文帝曹丕曾说:“蜀腊肫、鸡、鹜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食饴蜜。”可见早在三国期间,饴糖就很受蜀人的喜好。至宋代,尤其是南宋,杭州夜市上的饴糖制品非常多,如《梦粱录》中所记载的乳糖、十般糖、十色花花糖等。而在《武林往事》中,还曾涌现了几款“网红饴糖”,如“乳糖狮儿”“饧角儿”“猜糖”等。
渐入佳境的“甘蔗”
想必当代人在任意食品的包装袋上都见过“蔗糖”。古人将甘蔗榨出汁后,一种是随吃随榨,还有一种是将甘蔗榨汁后,将蔗浆放在太阳下暴晒,这样可以使蔗浆保存较永劫光且不变味道。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很早就生产了榨蔗工具。据宋应星在《开工天物》中记载,明代就涌现了一种既省力又能增大甘蔗出汁率的“糖车”,这对古代的制糖业是个重大的促进。
只是谁能想到,我们现在随便可以买到的各式蔗糖在历史上也经历了无数次升级。早在东汉期间,广州地区在澄清甘蔗汁的时候利用了石灰,于是产生出来了干固体的红糖。由于这种糖中有细沙一样的小颗粒口感,以是当时被古人称之为“沙糖”。陶弘景曾载道:“(甘蔗)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取汁以为沙糖,甚益人。”砂糖的雏形由此涌现。
至唐代,古人又开始制作冰糖,《糖霜谱》载:“取尽糖水,投釜煎……约糖水七分熟,权入瓮。事竟,歇三日。再取所寄收糖水煎,又候熟,稠如饧。……始正入瓮。”当糖浆熬制到九分熟时,就可以将其倒出来制作冰糖。宋代时,“糖霜”已很普遍,也即当代人的绵白糖,不少文人都为此写过诗文。如苏东坡《送金山乡僧归蜀开堂》:“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到了明代,宋应星又记载了一种“黄泥水淋法”,白糖的制造工艺进一步提升。
古人的“蜜糖”与“砒霜”
古人对付吃糖这件事,跟当代人一样,也是又爱又怕。糖是五味中的一味,既能入菜,又可补充能量,同时还能治疗疾病。《本草大纲》认为吃蜂蜜可以“和营胃,润脏腑,通三焦,调脾胃”。明初朱橚的《普济方》中的药方多次涌现了饴糖,如“麻子汤”中可用来清凉解毒,“人参汤”中可以滋补养身,“贝母散”里用饴糖和白糖治疗“热咳”。至于甘蔗,由于其性味甘、凉、无毒,具有清热、生津、下气、润燥等功效,更是被古人称为“天生复脉汤”。
甜蜜的诱惑很难抗拒,于是历史上嗜糖如命的人特殊多。陆游曾在《老学庵条记》中记载苏轼对糖的执着:“……所食皆蜜也。豆腐、面筋、牛乳之类,皆渍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东坡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饱。”苏东坡就连吃豆腐、面筋的时候都要放糖。而他的好友黄庭坚也是甜食爱好者:“远寄蔗霜知有味,胜于崔子水晶盐。正宗扫地从谁说,我舌犹能及鼻尖。”吃起糖来一点也不自持,居然想用舌尖舔鼻尖。
在享受这种甜蜜的同时,古人也创造过量地食用糖会带来身体疾病。当代人所熟习的糖尿病在古代被称为“消渴症”,司马相如、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陆龟蒙、卢纶都得过。个中司马相如更是糖尿病的代言人,因其字长卿,于是糖尿病在古代又叫“长卿病”。杜甫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病况:“我有长卿病……肺枯渴太甚。”糖尿病的症状之一便是口渴,对此杜甫如此形容:“闭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渴。”
对此,古代的中医已有相对全面的认知,他们留下了不少治疗药方,个中有一句“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想要治疗糖尿病,还得从源头抓起,合理摄入糖分,这样吃起糖来才能“细水长流”。
文并供图/金陵小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