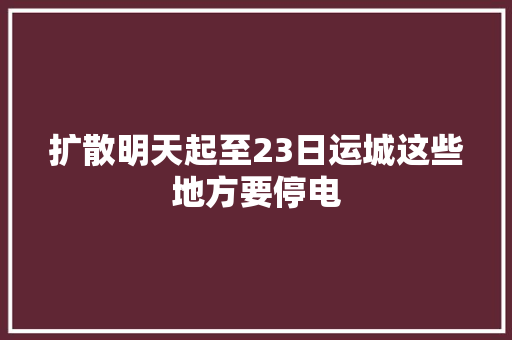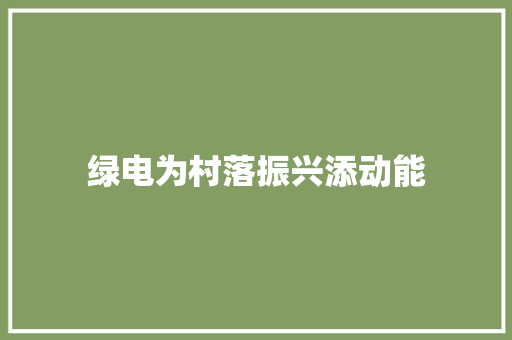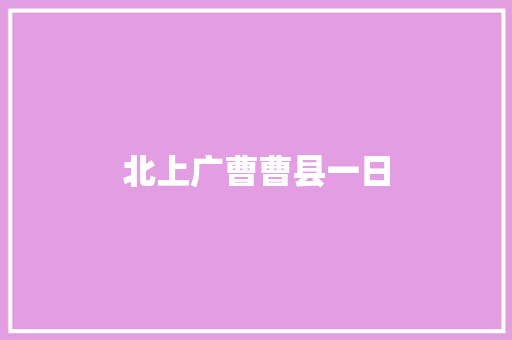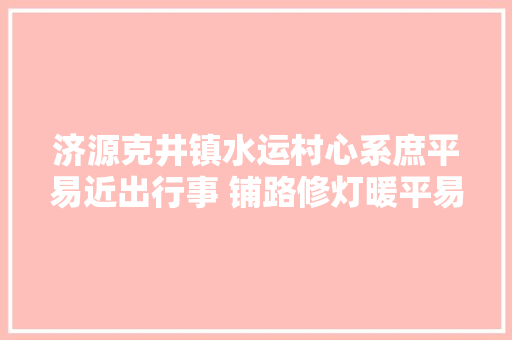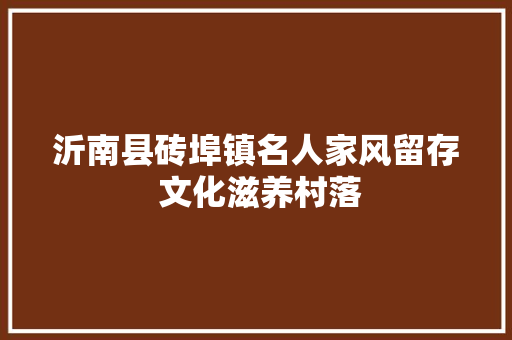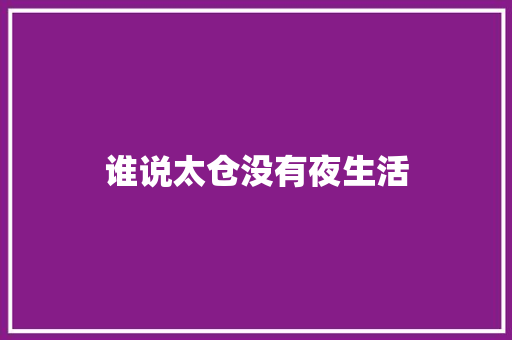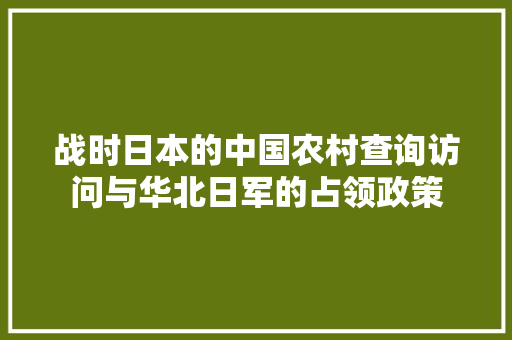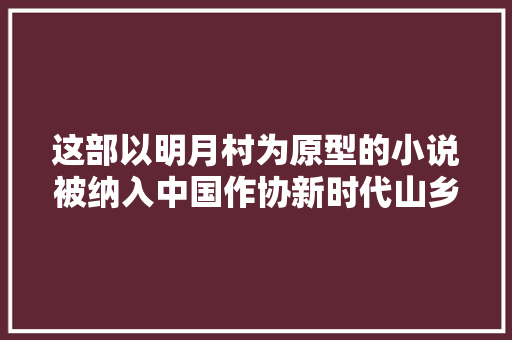50年前的1965年夏天,一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在这里打响,当时的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坐镇红村落第一线指挥,大庆、玉门等地的精英也调来增援,荒漠的山村落迅速建起了上千栋房屋,上万人在此事情生活,这里每天都是彩旗飘飘,红歌洪亮。
50年后的2015年夏天,来到红村落,宛如隔世。绝大多数房屋已被毁坏,处处是残垣断壁。从破败的角度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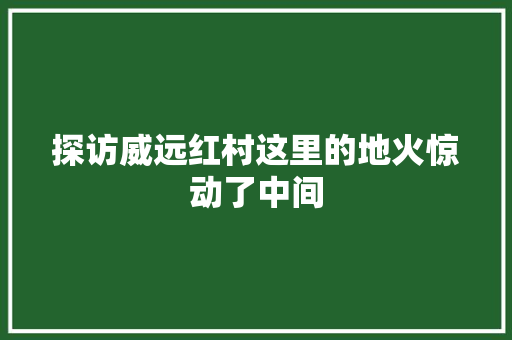
红村落“去世了”,但仍有一人守着这座废城,他是当年万人会战军队中惟一留下来一贯住到现在的人——廖宣州。红村落50年的繁华、悲惨,他都是眼见者。
寻路 废墟上的文物保护单位
红村落位于威远新场。威远当地人对这里没太大兴趣,这里道路破败,景致平常,离这里不远的石板河才是夏季大家爱去的地方。石板河有一段河床是由整块石板岩石构成,平坦干净,河水清浅而平缓,在酷暑中溯溪而上,就能在酷热中享受清凉。如今周末韶光,河里的人密密麻麻,快要遇上春熙路了。
而红村落是生僻的,上山的路是只有两三米宽的碎石路,野草丛生,时时时能看到一截石板台阶,或垮了一半的墙壁,偶尔也能看到几栋比较完全的房屋。这里的房屋和四川传统民居有明显不同,它的墙体紧张是石头和黏土,但其石头并不规则,这是用干打垒(一种大略单纯的筑墙方法,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入黏土)的办法修建而成。颜色也不是四川常见的青、灰、白色,而是比较鲜亮的土黄色,这是一种在西北常见的颜色。
我们的车只能开到半山腰一处平地,从地面依稀可辨的白色瓷砖线可以看出,这里以前是一个篮球场。再上面是蓄池塘和一片片玉米地,如果走近会创造,这些玉米地的位置以前该当是房屋的屋基,其边缘还有水泥和石头硬化的痕迹。
夏日午后,知了鸣叫,而四周听不到人声,如果不是有一块2012年直立的四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红村落石油会战旧址”这块牌子,恐怕不会有人以为这里有探访的代价吧。
拜访 一位老人五十年的坚守
这里毕竟不是无人区,红村落的半山腰也有一户人家,78岁的廖宣州和他的老伴在退休后“意外”住在了这里。由于退休的时候要交一笔担保金才能搬到县城,而廖宣州拿不出这笔钱,以是老两口留在了红村落,住在标着814栋的平房。这样的屋子,这面山上曾有上千栋,这样的场景现在自然看不到了。
乃至想通过照片理解红村落都弗成,廖宣州曾有一张红村落的夜景照片,“屋子依山而建,晚上看起来特殊俊秀,我们都说像小重庆。”这张照片被水打湿之后,红村落所有的场景,只留在廖宣州的脑海里。
但曾在这里住过的人,对这里的情形如数家珍,“卫生所、招待所、面包房、四合院、三合院、电影院、舞厅……”屋子不在了,但在什么位置,有什么故事,都记得一目了然。
而对更多的人来说,住在这里的廖宣州正在代言红村落。他见证过红村落的兴起,也目睹了红村落的冷落。他在这里足足居住了50年,他清楚这里的一砖一木。即便是老红村落的,跟廖宣州谈天,也是安慰,“红村落没有消亡,还有红村落的人守在这里。”
在平日,廖宣州喂鸡、钓鱼、遛狗、逗鸟,他习气并喜好这种生活,现在哪怕出钱让他去县城住,他也不会答应,这里清净,空气也好,他已经适应了。
溯源 这里的地火惊动了中心
红村落是在1965年才涌现的地名。在此之前,其所在的新场曹家坝区域就有“非常征象”而被史料记录。一百年前,当地人创造,这一带动田间地头,常冒出一股难闻的气体,着火即燃,蹿出蓝幽幽的火苗,人们就用它烧水、煮食、取暖和,并称之为“地火”。
威远的“地火”引起了地质专家的极大兴趣。1930年代,地质专家谭锡畴、黄汲清等人先后到威远稽核,推断这里埋藏有石油和天然气。但在当时的技能条件下,要找出地层构造繁芜的威远“地火”实非易事。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派队到曹家坝钻探,钻至1200多米时,只在二叠系阳新统(中国地层系统的专名,现已停用)地层中创造微量天然气和卤水,遂停钻。新中国成立后,地质事情职员重启了钻探事情,在经历多次失落败后,于1964年创造气藏,测试日产量高达7.8万立方米。
在当时,西南三线培植正拉开序幕,在威远的创造立即引起了中心的重视,于1965年初哀求石油部在四川搞一次“石油大会战”。这次会战的级别非常高,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担当会战指挥部指挥长,大庆、玉门等其他油田的精兵强将被抽调入川。
在成都指挥肯定不如在现场指挥,于是指挥部和干系的机关决定放在新场的一处荒山坡上。卖力通讯保障的廖宣州就这样随着来到了指挥部。
培植 传奇人物现场鼓劲打气
廖宣州还记得第一次到曹家坝这座山上的环境,那时这里完备是一片荒山,一条路都没有。本来,山脚下是一片狭长的平坝,在这里修屋子的话,大家不用爬坡上坎,比较轻松,但为了少占良田,指挥部还是决定将领导机关设在山坡上。
参加会战的培植者先修屋子,就地取材是他们的传统,威远这边石头多,于是就炸开岩石,用碎石垒起,这样修屋子的速率非常快,廖宣州从工地经由,每天看到的景象都不一样,房屋的培植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一栋平房快一点的话,只须要两天就可以修睦。以是,如果有几天不来指挥部的话,就可能会认不得路。
最先来到的领导人是邓小平,他与薄一波、粟裕等人在1965年11月到石油会战现场,廖宣州当时还看到了邓小平本人,而在其走后,这里也被命名为红村落了。次月,彭德怀到红村落察看,并参不雅观了建筑的住房和办公用房。1966年,彭真和贺龙也先后来到红村落,一个培植项目短韶光引起这么多领导人到现场打气鼓劲,这在当时也不多见。
小小的山村落,一下子涌进了几千人的修建军队,大家拿起钢钎、二锤、锄头,破石头、平园地、搭工棚,威远当地人也帮着烧石灰、修建大略单纯公路、建房挖沟。最先修睦的是山脚的几十栋屋子,所有的屋子修睦后立即住人,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至少可以住16个人,中间再摆一张桌子当办公桌,一石二鸟。
往事 激情燃烧根本停不下来
万人誓师大会是当年“石油大会战”的一个高潮,参加万人大会的,是从大庆、玉门、青海、华北等全国各油田调集来钻井、测井、试油、机修、供应、医疗的军队。当时提出年产天然气70亿立方米,为的是学大庆苦干实干的精神,鼓舞干劲,大造声势。
各矿区、各工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各油田的队长们争相抢发话器表决心。廖宣州专门守在那里,卖力管理音响和发话器。台上本来只有4支发话器,按照规则,该当是一个一个依次来,可是为了争到发言机会,没轮到几个人发言,就乱套了。队长们持续赓续上台争着发言,到后来,干脆是谁抢到发话器谁就发言,由于人太多,发话器被抢坏了好几个。
红村落很快就建好了,山坡上是密密麻麻的屋子,锦旗和标语满山都是,到了晚上,全体山村落灯火辉煌。在红村落,生活基本以事情为主,廖宣州从1965年到红村落,直到1969年才有假可以休,“我是卖力通讯保障,一天事情韶光常常是17、18个小时,从早上8点开始,就要检修线路,那时电话常出故障,一下子山脚、一下子山坡。晚上指挥部要开电话会议,我更是不能离开,一贯待到深夜,而这个会议室做事员是不能进的,以是我还要客串做事员,端茶送水,电话会结束后还要打扫卫生。”
听说,当时在红村落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高强度、快节奏,用现在盛行的话来说,“根本停不下来。”而会战的成果是显赫的。1966年年底,威远布局探明储量达400亿立方米,这次会战找到了四川第一个陆上整装大气田——威远气田。
光阴 他或许还在等军队回来
在几千上万人的红村落,用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每个小单位都有自己的食堂,有自己的饭菜票,这些饭菜票不能在其他食堂流利,以是到饭点的时候,必须赶回自己单位的食堂。有一年除夕,廖宣州错过了饭点,他于是上阁下的小镇去觅食,去了才知道,除夕这天,这里的店铺只做上午的买卖,下午和晚上都关门过年了。
但当年的红村落在周围老百姓心中,是个神圣的地方。这里的工人地位高,这里常常放露天电影,在全国盛行穿解放军服装的大景象下,这里却盛行穿红衣服——石油工人的事情服,常常有当地人费钱买红村落人的事情服,然后穿着在街上得意地走来走去。
到上世纪80年代,气田产量开始下滑,威远气田逐步淡出人们视线,为油气而建造的红村落,也逐步走向衰败,离开的人越来越多,曾经一度上万人的红村落,逐步变成人烟稀少的野村落。2003年,红村落遭到毁坏,《中国石油报》这样写道:那年夏天……一排排见证红村落艰巨创业的干打垒屋子被夷为平地,一周之后彻底消逝。
作为一个退休老头,廖宣州没法阻挡事情的发生,但他却又以为,这么一个地方,不可能就这样完了吧,早晚还得要有人守护。于是,当年那上万人的军队中,他成为个中惟一留下来的人。
他在这里,看到会战旧址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看到红村落当年的工友和在这里终年夜的红村落二代回来故地重游,很多人都堕泪了,当年生活、恋爱、结婚、生子的地方,从卫生所、大礼堂,到电影院、舞厅,都不在了。只有坐在廖宣州门口的破椅子上,聊聊当年,体会“人是物非”。
但廖宣州还在期待,前几年这里搞页岩油探测,他创造红村落又时时有穿赤色衣服的石油人来来往往,他向每一位到红村落的石油人问同一个问题,“红村落是不是又要会战了?红村落是不是又有希望了?军队是不是要回来了?”
我们向廖宣州告别的时候,他溘然跟我说,“我不离开这里了,去世了也埋在这里,就守在这里啦!不离开了!”他末了摇了摇头。
廖宣州正在代言红村落。他见证过红村落的兴起,也目睹了红村落的冷落。他在这里足足居住了50年,他清楚这里的一砖一木。即便是老红村落的,跟廖宣州谈天,也是安慰,“红村落没有消亡,还有红村落的人守在这里。”
四川省档案馆 成都商报社 联合出品 本期协办单位 内江市档案馆
成都商报客户端 蒋庆 演习生 曾月娥 四川省档案馆 庞家陵 宋弋 威远县档案馆 刘莉 杨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