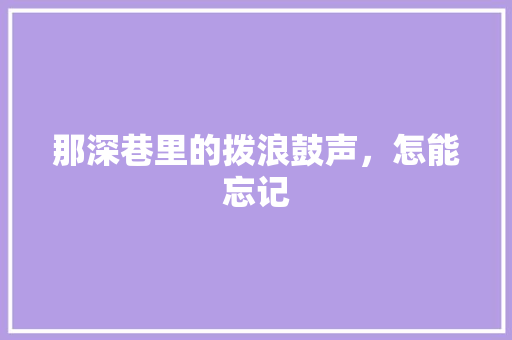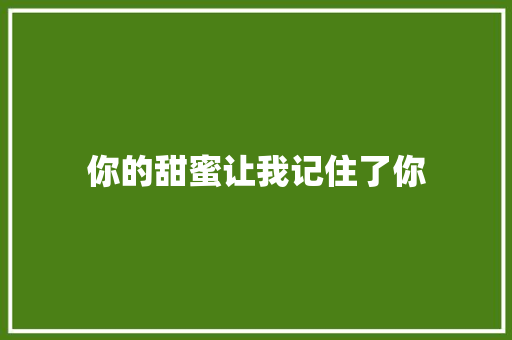村落庄的土屋扑拙可亲,屋顶铺的是茅草。木窗棂古朴而又沧桑。
晚上,母亲们常坐在蒲团上,右手摇着纺车,左手捏着棉条,嗡嗡嗡地纺棉线。织布机是老式木制的,人坐在上面,双脚一左一右地踩踏板,双手麻利地抛接着梭子,交织出古朴的土花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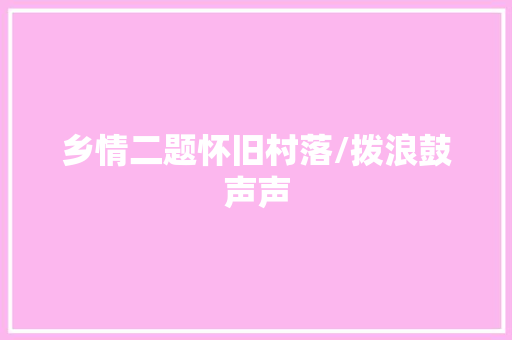
院墙是用泥搭就,掺了麦秸,用铁泥叉一叉叉往上搭,十分结实。孩子们常在墙缝里捉到蝎虎什么的。
庭院多栽种桐槐桑楝梨枣诸树。槐花白馨馨地清香袭人,采摘后拌了面,锅里蒸好后,洒上喷鼻香油葱蒜汁,诱人口水。桑葚红时,孩子们爬上树直吃得满嘴血红。打枣时更热闹,或站于树上扭捏,或以长棍击打,或投以砖头瓦块,枣落如雨,砸得头疼,众皆纷抢。
俗话说三好听“百灵子(鸟)叫、打(碎)茶盅、小孩叫(喊)娘头一声”。乡下小孩常以小花袄、花棉裤装裹。脚穿小花棉鞋,鞋底用棉线纳成,鞋面首多为小布老虎、花公鸡、小花猪等图像,如工艺品玲珑可爱。
老者烟袋锅或铜或竹,烟嘴多为玉制,碧绿晶莹,光洁可人。年代久了,玉石烟嘴里便长出一些似龙云雾岚般的图案,保佑人化险为夷。烟袋多为布制,内装烟丝,扎一松紧小口,用之松开,不用则束之腰间。
土灶多配一风箱,一拉呼哒响,不是有句歇后语“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么。
村落里去世了人要土葬,响器声如泣如诉,去世者家属白衣白帽披麻戴孝,手执招魂幡哭丧棒,众哭嚎啕,直到去世者入土为安。
玩杂技的刀枪不入,耍猴儿的给猴儿戴上面具牵着小猴翻筋斗嘴里喊着“小猴子上场来不要匆忙------”;锔盆匠将裂痕的瓦盆用手钻打孔,锔钉固定;爆米花者将一个黑不溜秋的长圆筒锅烧热了用脚一踩,“砰”地一声爆出喷鼻香喷鼻香的玉米花来。
逢庙会便有戏台,锣鼓喧天,唱戏的呀呀唱将起来,轻舒水袖,字正腔圆。听戏的伸长了脖子,听得津津有味。有道是“唱戏的是疯子,听戏的是傻子”嘛------
说大鼓书的老艺人在晚上右手敲着大鼓,左手简板伴奏,说尽了《岳飞传》《杨家将》《明英烈》《说唐》等评书里的忠良奸佞。
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剃头师傅烧热了水,用推子剪子剃刀润色得人满面东风,第二天挨家收粮以作理发用度----
上述的旧日村落庄这些景象,有的已不复存在,却依然留在我们的心扉里,一如老屋堂前悬挂的毛主席画像,永久都是那么令人感怀,那是一种感情,在悄悄流传-----
----2001年3月29日于宁波
拨浪鼓声声我五岁时,已经认识拨浪鼓了。
那天,摇拨浪鼓的是个老货郎。他的拨浪鼓鼓面是牛皮做的,鼓腰红通通的,鼓柄有尺把长,两根短绳头际系着坠儿,用手一摇就“卟愣咚----卟愣咚----”地响,以招徕顾客。
老货郎推着个架子车,车上放着一个木箱子,里面全是针头线脑顶针喷鼻香脂木梳发夹甩炮之类的东西,箱子旁放着一大袋豇米糕。
围了很多小孩,好奇地看着老货郎手里拿着一个泥巴狗(瓦叫吹),吹出动听的哨音。我惊奇于那从泥巴里传出的呜哇声,对那玄色的被点上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泥泥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购买欲。
我一溜风跑回家里,东找西寻,终于看到了那个被用来打压水井的铁钻头,忙提上跑出了家门。
老货郎换给我几个泥泥狗。我愉快不已,以一个孩子的天真反复把玩着。我在酝酿感情,想着若何爬上黄土高坡,对着那清清的河水,吹出心底红彤彤的渴望。
我激动不已,很想把这巨大的幸福与小伙伴们分享,又怕他们会把泥泥狗抢走。
我决定先吹一个试试。我线取出来一个,小心翼翼地用袖口擦干净,努力沉着了一下,拿到嘴边憋足气猛吹了一口,那“瞿---瞿--”的哨音使我微微地陶醉了。
就这样边走边吹,悠然趾高气扬。
二奶奶劈面走来,瞥见了我的小把戏。二奶奶问,吹哩啥。我说,是瓦叫吹。二奶奶又问用啥换哩,我只好照实说了。二奶奶急了,扯了我的手就走,说那是打井用哩你也敢换。
好在老货郎还在村落里转悠,二奶奶又让我换回了那个打井用的铁家伙。
我感到失落望沮丧极了,白云小鸟也不好看了。我无奈地看着老货郎摇着拨浪鼓走远了,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
我看到货郎老头快出村落了。
我依依不舍地随着。
老头的拨浪鼓彷佛比以前还响亮,音质厚重,每一声鼓点都强烈震荡着我的心田。
老头走到村落东一间废弃的生产队里的打面机房里小解去了,车子停在大路中心。
我的心忽然咚咚地狂跳,脑筋里一片空缺。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箭步到了架车前,先开箱子,拿了一个塑料口哨就跑了。
这是一个小巧而扁长的塑料口哨,一半黄一半红,哨嘴扁长,半圆的哨体内,装着一粒黄豆般大的鄙吝械,一吹就骨噜噜地滚动,好玩极了。
我尽情地吹着,又蹦又跳地在家里大床上看着墙上几张毛主席的画像,在心里对毛主席身边的一位穿吊袋裤的工人说,终年夜了我也要穿吊袋裤。
娘从生产队里收工回来了。
娘创造了我的哨子,问哪里来的。
我只好说是偷着拿的。
娘生气了,照着我的脸上、身上打了一阵。我感到火辣辣地痛。娘问,还拿人家的东西不拿。我小声说,不拿了。娘说,再拿比这打哩还狠。
傍晚了,所幸老头还没走多远,娘从我手里拿出那个哨子,还给老头。老头忙摆手说,不要了,给孩子吧,看把他打哩。娘说,不中,不能惯他。娘给了老头钱。老头只好收下了。
晚上,石油灯闪闪烁烁,一如我的心情。我被娘罚面壁思过。大(父亲)说,让他睡吧,看他困哩。娘说,从小偷针,终年夜偷金,不管他他上天哩。
灯灭了,阴郁里老鼠窜去又窜回,地上蛐蛐乱爬。我嫌恶地用手挥之不去,哭够了也乏得再动。
娘忍不住点亮了灯,大(父亲)伸开被窝一角,我忙钻了进去,温暖得很。
“拨浪鼓,咚咚咚,妹妹笑得脸通红-------”而今,小燕子赵薇的歌在唱着拨浪鼓,撩拨着我儿时的那份红彤彤的渴望。如今,摇着拨浪鼓游乡的老货郎也不多见了,但那拨浪鼓的声音为什么还是那样动听------
----2001年4月5日清明于宁波
(李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