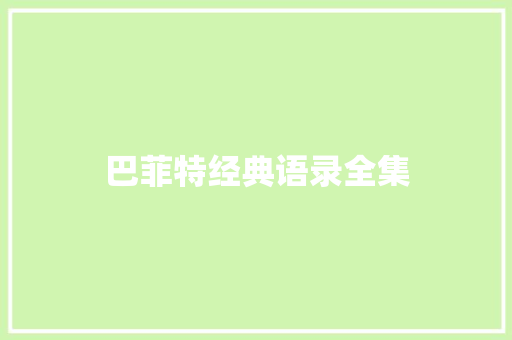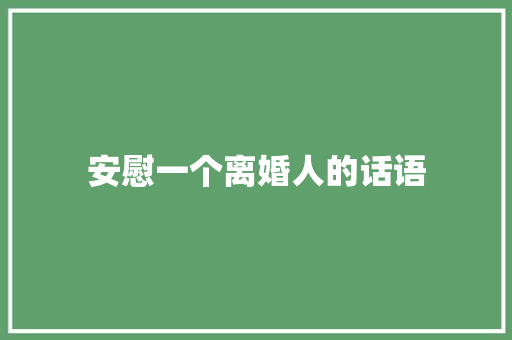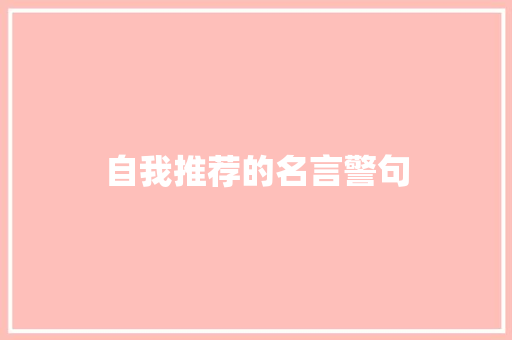马頔说,20多岁时他在音乐创作上表达欲很强,猖獗输出,30多岁则更追求表达的准确度和言之有物,创作题材的选择也更广泛了。至于“标签”,都是别人看他,他并不在意,他对自己的评价是“独立音乐人”——完备独立于市场之外,只从自己本心出发去思考和写歌的音乐人。但他很介意有人“极度歪曲”解读他的作品、给他编故事。“就彷佛是他写的歌一样。这种行为除了想要彰显自己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综艺、演出和挣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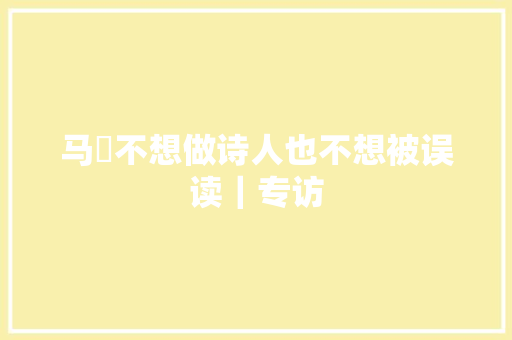
《南山南》火了六七年之后,马頔参加综艺节目的次数才逐渐多了起来。今年以来,他已在《拜托了冰箱》轰趴季、《嫡创作操持》等几档综艺里亮相。聊起个中原因,马頔很坦诚地回答:“由于疫情的关系,今年定了10场演出,黄了8个。没有演出,韶光许可、项目得当我就参加呗,得挣钱活着。”
从市场反馈来看,作为独立音乐人的马頔,其天然生动的性情特质和在音乐上的输出表达能力颇受综艺节目喜好。当然,如果演出和上综艺的机会同时摆在面前,他肯定优先考虑演出,这和钱没有关系。“演出舒畅啊,那是我能驾驭的环境,也不用说那么多话。”
而作为《嫡创作操持》的“风云西席团”成员,他不可避免地须要说很多话来点评学员、表达不雅观点。“你还得核阅自己说的话是不是能让孩子(学员)接管,不会给他带来侵害,也不会让他飘了。说话就挺难的。”只管有一些顾虑,但他在节目里欣赏李天姿就直接赞她“北京之光”,对同学们的作品失落望也开门见山,乃至自己都红了眼眶。
马頔是《嫡创作操持》的“风云西席团”成员。腾讯视频供图
在马頔看来,参加综艺无需刻意展现,自己生活里什么样,节目里就什么样。对付年轻音乐人作品,他有想说的话还是会直接说出来。“生活中谁能掌握得这么完美?我不是措辞艺术家,不太会拿捏这个。由于之前听过那对双人组合的音乐小样,后来现场确实不尽如人意,以为想象和呈现差太远了。这时候还说好话就该飘了,该说点不中听的了。”
《嫡创作操持》最吸引马頔的是年轻人和音乐创作,“我对现在年轻人在做什么音乐挺感兴趣、挺好奇的,就想去看看。”他坦言平时很少有机会去打仗年轻的音乐创作人和他们的作品,“我这岁数平常也不太有机会跟2000年出生的孩子在社会里成为亲密朋友。”
上网听歌他又习气听“日推”,由于大略不费事儿,较少主动征采想听的歌,顶多会去搜一些老歌,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摇滚乐、老民谣,90年代的中国摇滚和中国民谣等等。这样一来,互联网算法推举之下,他就很难听到年轻人写的歌了。
墨客、孤独和误读
对付身上的“标签”马頔并不在意。他认为那些“标签”是别人对他的评价,本身就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读。比如他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给别人留下“孤独”的印象——虽然他认为每个人都得有孤独。他也剖析了一下:“可能最早是由于我上节目的一个段子。当时喝多了,我给人发信息说:‘哥,你孤独吗?’后来大家老拿这个段子起哄。”
至于“墨客”,他印象里那是特殊早的时候,不知道谁写的文案里的词。“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墨客,也不想做墨客。”至于写歌词会不会追求诗意化的表达,他自认写歌也都是正常写的,便是矫情点。“谁如果能用正常措辞说出来,还非要写一首歌啊?这事儿本身就挺矫情的。做一矫情的事,难道还不让别人说你矫情?”
他对自己的评价是独立音乐人,即不是从工业角度去写歌,而是完备独立于市场之外,只从自己本心出发去做思考、做阐述、去写歌,“你的精神内核是独立的。如果写的时候考量这首歌是不是会受人欢迎,就不叫独立音乐,而是工业化音乐。”如果做工业化音乐,他自己在写的过程中就得不到任何的乐趣,他以为自己写不了,也不想写。
《孤岛》专辑中的《南山南》成为马頔的代表作之一。
《南山南》广为传唱、备受欢迎,但他当初纯粹是从独立音乐人的角度去写这首歌的。发布之后,他本以为只有部分喜好独立音乐圈的人会喜好这首歌,没想到很快传播到了大众层面。“《南山南》的走红在我的猜想之外,但我是很愉快的,人都会虚荣啊。”但歌曲的走红也带来了曲解和误读,有人编了很多和这首歌有关的故事,“就彷佛是他们写的歌一样”。
他当时非常生气,不过现在回看只以为可笑。“传播广的歌,势必都会这样,我是没有经历过,以是没有生理准备。”经历过《南山南》被误读之后,有生理准备了吗?“后来也没这种歌了呀。”
不介意“标签”的马頔很介意别人对他的作品进行缺点的解读。一首歌发布后,他常日会去看评论,假如创造有极度歪曲解读的评论,并且还得到了很多人的簇拥和点赞,他会忍不住回怼。但他也没想过在评论里阐释自己这首歌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我吃饱了撑的跟他们干同样的事?”
他认为这样曲解音乐作品的行为是不好的,实际上妨碍了别人听歌。“每个人听歌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和理解,不然听歌的意义在哪儿呢?听歌又不是做阅读理解,有一个标准答案。这种行为除了想要彰显自己,得到大量虚荣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电影、漫画和篮球
间隔首张正式专辑《孤岛》的发布已经由去了将近十年。马頔从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迈入了三十而立的行列。回看当年写的《南山南》这些歌,他以为是有遗憾的,“但没办法,20岁能做的也便是那些”。
聊起写《孤岛》时的创作状态,他形容自己当时抵触社会生活、郁郁不得志、愤世嫉俗、企图爱情。“那会儿的表达希望好比今要兴旺。对爱情的渴望也好比今要更多。”现在的马頔,依然会有愤世嫉俗的感情、依然会有对爱情的渴望,却不会像20多岁时那么“猖獗输出”了。
和当年比较,马頔现在写歌的灵感来源实在没有发生太大的变革——自己的生活、别人的生活,看到的影视作品、书本和漫画。他一贯喜好漫画,小时候爱看《幽游白书》《七龙珠》,现在乐意欣赏更多的漫画类型。他从小学就开始打篮球,因此喜好《灌篮高手》,“井上雄彦永久的神啊”。他也对电影保有持久的兴趣,欣赏偏作者向的文艺片譬如《大佛普拉斯》《瑞士军刀男》,近期则比较期待娄烨的《兰心大剧院》。
他也一贯习气自己创作,很少主动找人互助。“基本上都是别人写好了找我互助,我说可以。我自己写歌找别人互助,没干过这种事。”比如那首《大雁》,马頔跟文雀乐队很熟,由于他自己乐队(OKK乐队)的黄继扬和刘佳,也是文雀乐队的成员。当时文雀乐队要做专场演出,找他去做高朋。“他们是‘后摇乐队’,我去曲稿身的歌也不得当。他们说要不你找一首歌填词写个和声吧,我说行啊。”
马頔说,随着年纪的变革、阅历的增长,他在音乐创作上变得更加谨慎了——题材的选择更广了,但写出的东西更少了,由于他现在更追求表达的准确和言之有物。“谨慎不是由于外界的批评,我对这些不在意,纯粹是自己对创作的哀求。20多岁和30多岁做同一件事,你会对30多岁的自己更加吹毛求疵。”
新京报 杨莲洁
编辑 田偲妮 校正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