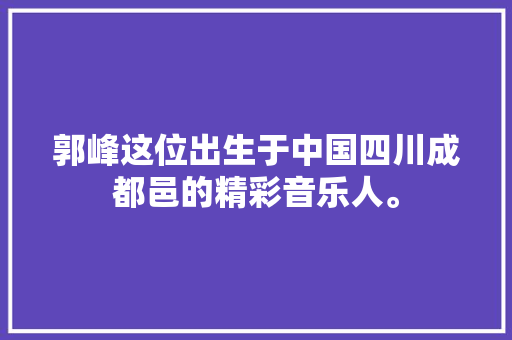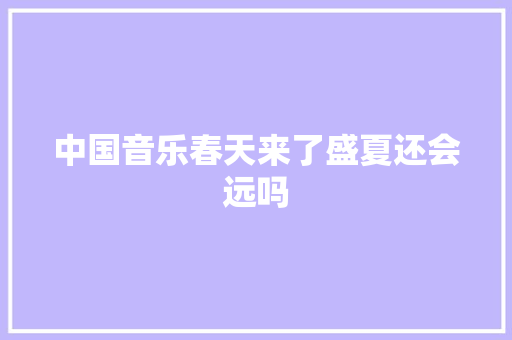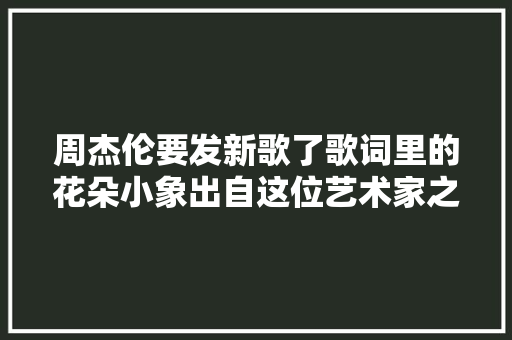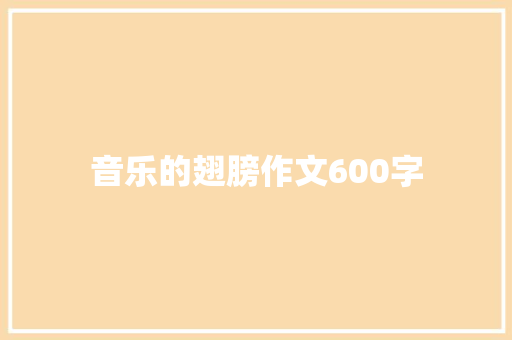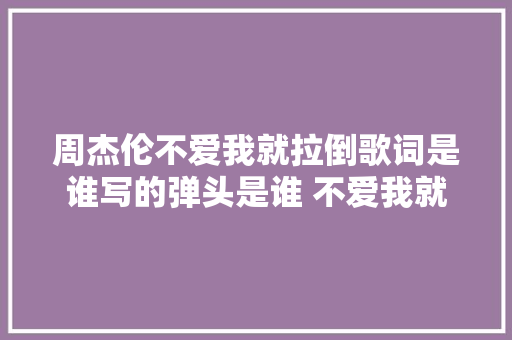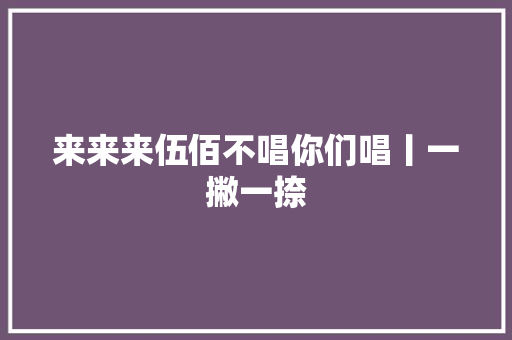最近,一则论坛中的帖子引发了人们的把稳。帖子名叫“推举一个冷门的新加坡华语歌手孙燕姿”。发帖者表示,自己是无意入耳到孙燕姿的歌,觉得她声音很有特色,推举大家去听。
很快,“冷门歌手孙燕姿”的话题便引发网友热议,孙燕姿本人也愉快地接下了这个梗,并在社交媒体中以冷门歌手自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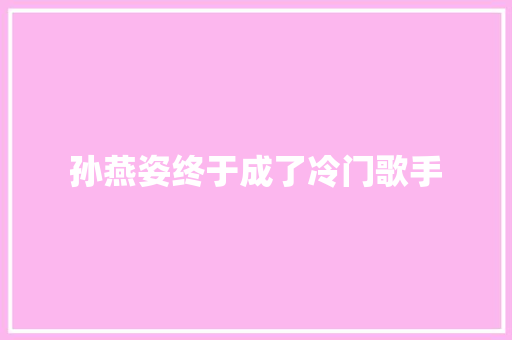
是天后不足出色,还是审美发生了变革?老歌迷年夜方冲动大方,新粉丝一脸迷惑,相互说着自己的回顾和标准。
仿佛在互换,又仿佛在自说自话。
被逐渐拉大的代沟
冷门歌手孙燕姿不是第一个被网友考古发掘出来的“上古大神”,之前的一段韶光还有“周杰伦当年真的爆红过吗?”“那英有什么实绩吗”“SHE是什么水平的女团,和创造101比谁更厉害?”,年轻的网友们把不懂就问发挥到了极致。
2019年便涌现过的“周杰伦保卫战”,那也是一个问题引发的哗然。“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为什么演唱会的票如此难买?”
一石激起千层浪,那些已经步入中年的周杰伦粉丝,放下了手头在写的PPT,利用孩子上补习班的缝隙韶光,拿起了手机,注册了账号,重新拿出了当年的劲头,自学打榜,刷数据,学起了年轻人们的网络黑话,带着七彩标语,仅仅几日,便把当时排在超话榜第一的蔡徐坤“打”了下来。
微博截图
现在,我国的艺人迭代速率是很快的,一个艺人溘然就蹿红了,乃至没有给出充分让大家理解他/她的机会,更谈不上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对付音乐这种产品为王的艺术形式,上一代受众显然无法理解作品本身不足出色的歌手是如何成为顶流的。
但在年轻人眼中,流量,彷佛是判断一个明星红不红的唯一标准。
两个时期不同受众群体的审美标准、评判体系、欣赏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群体间的不理解有时会被社交媒体放大,在发言评价没有任何本钱的情形下,小规模的“擦枪走火”很随意马虎衍变成大规模的“集团式作战”。
火热的嘴仗显然没有冰冷的数据有说服力,《2020腾讯娱乐白皮书》中显示,周杰伦的《Mojito》在2020年华语新专辑销量TOP10霸占了第二名,在专辑发卖额TOP10中位列第四,在新曲热度榜中则排名第一。而在苹果音乐公布的2020年度音乐排行榜前100首音乐中,周杰伦以47首险些撑起了半壁江山。孙燕姿、林俊杰、陈奕迅等名字也位列个中。
数据至少证明了,这些所谓的“上古神话”的音乐作品,在多少年后的本日依然拥有弘大的受众群体。
评价体系的改变,很难评价曾经的歌手和现在的粉丝究竟是哪拨人没遇上好时期。
信息茧房带来的蝴蝶效应
人们习气性地认为,每个时期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有着自己的审美情趣,这是造成两代人口味不同的缘故原由。
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口味千差万别,但是选择的权利和机会曾经是均等的,这种均等受制于市场环境和技能手段等多方面的成分。
在21世纪初期,唱片公司经由了多年的发展步入了辉煌期,推广体系、运用渠道都相对完善成熟。在华纳、滚石等国际唱片公司与音乐制作工厂的支持下,全体音乐市场的制作流程也更为专业,市场、歌手与唱片公司之间逐步形成了一种良性助力关系。
孙燕姿 图/中国新闻图片网
因此我们才能在一个期间内同时见到周杰伦、孙燕姿、梁静茹、蔡依林、陈奕迅等带来的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状态,市场足够宽广,生态足够支撑如此数量的歌手被发掘和打造。
音乐载体的变革也让人们的选择变得多样和随意马虎,从磁带到CD,正版唱片的价格并不低廉,人们会将自己的钱花在刀刃上,去选择自己最喜好的歌手,但当数字音乐格式兴起,人们的选择陡然增加,本钱也迅速降落。受众可以从海量音乐产品中选择符合自己口味的产品。
由于市场足够大,选择足够多,成本没必要对生态进行过多的干预。
如今则大不相同,在大数据和算法涌现后,为了赢得市场,险些所有的平台都开始利用大数据对用户进行算法推举。从音乐的角度上,数据和算法乃至可以精确地通过每个人的数据有针对性地为人们推举你可能喜好的内容,从歌手到曲风,从歌词到音色。
当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气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勾引,就会涌现信息茧房的情形,个人的审美和意识被不断尊重放大,不断为人们提示着“你喜好的便是最好的”这样的观点,这会让单一个体对艺术的网络和剖析进入一个相对狭窄的区域中。
在这样的算法下,每一次歌迷和歌手的“错过”可能都意味着“永别”。有多少年轻人错过了孙燕姿、周杰伦,就有多少中老年人错过了蔡徐坤、华晨宇。
信息茧房不仅影响着受众,也影响着成本,成本通过流量直不雅观判断艺人的代价,并为其供应更多的机会和曝光度,这就从另一个层面减少了人们可以选择的机会。
这也直接造成了在一代人眼中“我都没听过唱歌的小孩子,怎么一夜之间哪都是他/她?”的情形。
在辩论中,很少有人去真正思考其背后的缘故原由是什么,技能变革和成本参与带来的变革实在并没有完备将人们的选择束缚住,终极选择权实在仍在每个人的手中,点点手指大概就能打破。
但当被裹挟个中后,原来可以理性互换的喜好变成争吵,几代人建立理解的可能性也随之降落。
实在,没听过孙燕姿,不识周杰伦并不是天算夜的罪过或者是笑话,反而是一件十分正常和自然的事情。
最好的时期
今年3月,TME旗下的由你音乐研究院发布了《2020华语数字音乐年度白皮书》。个中显示,2020年华语新歌数量,同比2019年增长216%,达到74.8万首,超过2017-2019三年总和。2020年发行新作的华语歌手人数同比2019年增长82%。
纯挚从数据上来判断,彷佛华语音乐正在经历触底反弹后的涅槃重生进入最好的时期。
但关于音乐水平低落的不雅观点却几次再三被提出,实在无论哪个年代,一名音乐人想要终极得到受众的认可,也都要经由不断的试错,只是曾经的年代留给试错的空间较大,如今的时期,当音乐人基数变大,歌迷反馈速率变快,总会给人一种,这个时期的歌者都在“犯错”的错觉。
孙燕姿 图/中国新闻图片网
“老歌者和新歌手谁唱得更好听?”这个话题可以永久纠缠下去,却不会有结论,好听的标准无法量化,这里既包含着音乐专业性上的评判,也包含着受众投射到歌曲和歌手身上的情绪成分。
一代人对付音乐的回顾,并非都来自于音乐本身,许多艺术作品和独立个体发生的情绪联结都与个体在彼时彼刻的生理状态、认知构造、代价体系紧密干系,一首歌曲带来的回顾可能是一座城市、一段光阴、一份感情,当一首老歌响起时,会自动为其曾经的受众带来一份安全感。
但曾让一代人得到共鸣的声音能否会让20年后的另一代人感同身受,这很难讲。毕竟周遭的环境和蔼氛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同理,年轻一代音乐人同样有属于当下语境下的表达,从办法到风格也不会和曾经完备相同,这也是一定的。
韶光带来的鸿沟就完备难以超出,完备方枘圆凿么?也不见得,但须要足足数目标精良作品和足够空间的选择余地,让音乐回到原来地评判维度中,或许还有心平气和互换的可能性。
一个属于音乐的好时期究竟是若何的?是有数量弘大的好作品?有大量优质的好歌者?有良好的市场氛围?大概都是,但不局限于此。
在海量的音乐作品中,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爱好,不断考试测验和选择,从而探求到自己喜好的内容,并且能接管他人有其他喜好并享受个中,这大概才是最好的时期。
至于谁是冷门,谁是顶流,留给成本去思考和博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