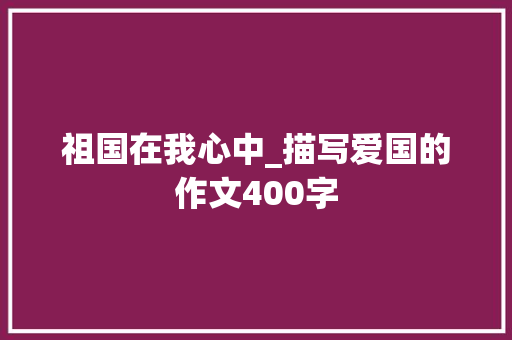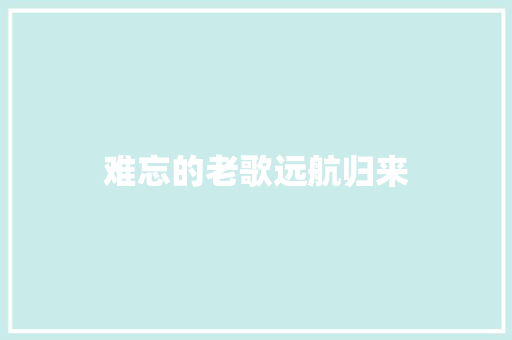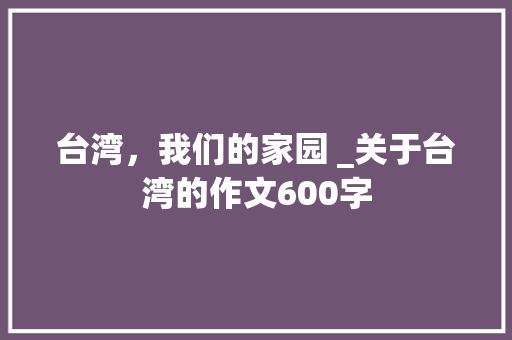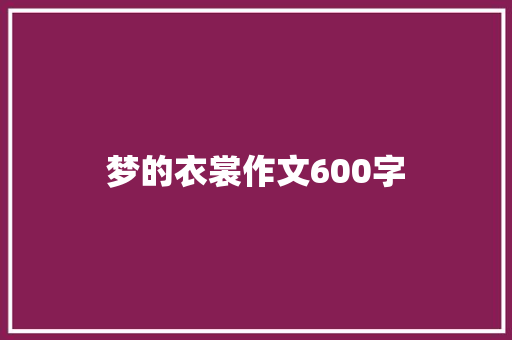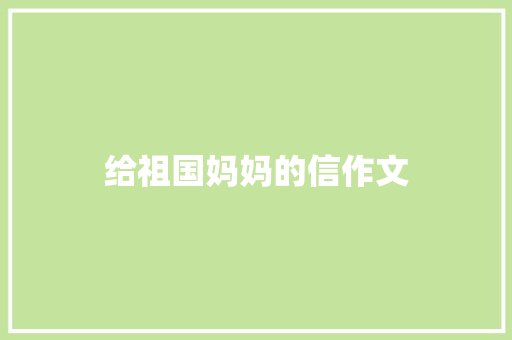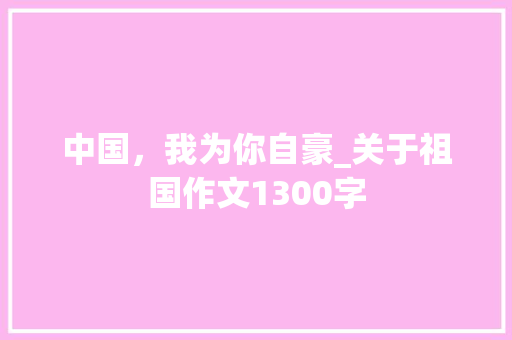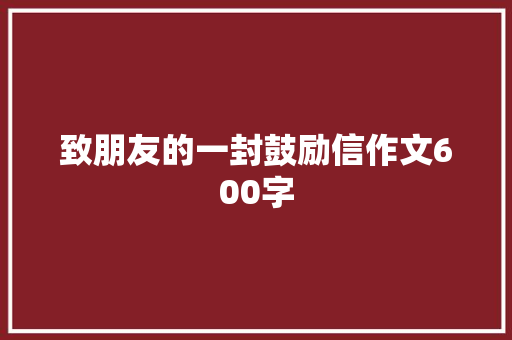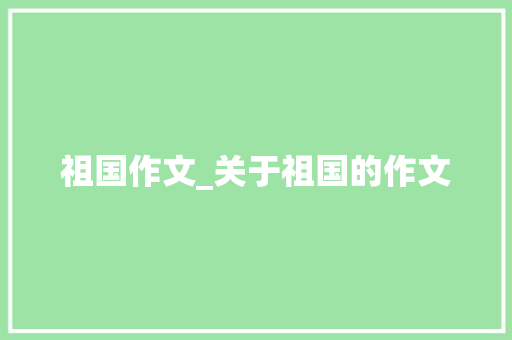同乡兼同窗,不同的艺术人生
《我和我的祖国》词作者张藜、曲作者秦咏诚是辽宁大连同乡,他们都毕业于继续了延安鲁艺光辉革命传统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秦咏诚15岁就在《旅大日报》揭橥了处女作《抓害虫》,1948年考入大连地下党领导的关东社会教诲团,成为一名文艺事情者。1952年他考入东北鲁艺音乐部(今沈阳音乐学院),在作曲家李劫夫和苏联专家古洛夫的悉心栽培下,秦咏诚很早就显露出卓绝的创作才华。1964年,刚过而立之年的他以一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名誉鹊起,那随处颂扬的旋律迄今仍响彻祖国大地。随后,他更是一鼓作气地创作出《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满怀深情望北京》等赤色经典歌曲,成为继李劫夫之后,东北大地冉冉升起的一颗作曲新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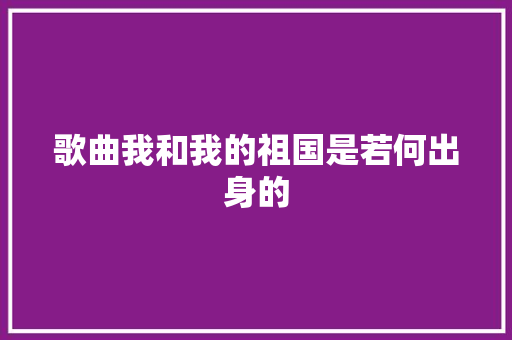
与秦咏诚顺风顺水的创作进程正相反,张藜的艺术之路走得坎坷而艰辛。1946年,张藜考入东北鲁艺四团,1947年进入东北鲁艺文学研究室学习。1950年,他在《东北新歌选》揭橥了第一首歌词作品《建筑工人之歌》,遂以此为终生职志。然而,李劫夫看完张藜创作的歌词后,却很诚恳地告诫他:“张藜,你写东西够呛。”(张藜:《谈佳构歌曲的生产》)1979年,张藜调入中心民族乐团任创作员,随后秦咏诚也从辽宁乐团调回沈阳音乐学院,任作曲系主任、副教授。当这两位生活、创作阅历完备不同的老校友再度聚首,究竟会碰撞出若何的灵感火花?
二十分钟写就的旋律
1984年,秦咏诚在中心教诲行政学院学习培训,每周六他都要坐几小时的公交车到张藜家中小坐,共同畅谈歌曲创作心得。张藜的女儿张路常常演奏秦咏诚于1962年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海滨音诗》。张藜耳濡目染,也逐渐迷上了《海滨音诗》那动人的旋律,于是他请秦咏诚把《海滨音诗》的主旋律用简谱记写下来,按照歌曲的哀求重新发展一下。秦咏诚写好后,张藜很快就给填上了歌词,还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太阳与大海》。试唱了几次,张藜以为歌曲在同名大小调上转调两次,随意马虎跑调,怕群众唱不了,流传不开。
一天下午,张藜约请秦咏诚来家用饭叙谈,借机对秦咏诚提出:“能否再写一首旋律和《太阳与大海》的音乐主题反着来的歌曲?前者是旋律从低往高走,而这首歌则哀求音乐从高向下行,但感情和意境不要变,音域不要太宽。”秦咏诚稍加思虑,便顺着张藜的意思,想出一个新的动机,不觉笔下生风,思如泉涌,仅仅20分钟,一曲新的旋律便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秦咏诚给张藜唱了一遍,打趣说:“我的任务完成了,现在看你的了。”
“第二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瞥见面前晨雾中的巍巍高山,溘然有了觉得,歌词就出来了”
谱子得手,一晃半年过去,用张藜的话说,“我揣在怀里走到哪都琢磨这个曲调,一贯转到鼓浪屿,又转到张家界。”这年秋日,张藜去湖南张家界参加一次笔会,在颠簸的卧铺车厢里,他夜不能寐,把头靠在枕头上,习气性地点起一支烟,目光牢牢追逐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灯光与茫茫夜色。燃着的烟头欠妥心落在枕头上,把枕头烧出一个大洞,他却毫无察觉,险些重演墨客郭小川的悲剧。
抵达大墉县确当晚,张藜又把曲谱拿出来看了几遍,可依然灵感全无,伴着难以名状的失落望,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当清晨的霞光穿透窗棂,张藜推开窗户,纵目远眺,一轮朝阳东升,天门山身披万道霞光,巍然耸立潇湘大地。虽说张藜饱经生活磨难,也走过许多名山大川,却没有一次像这次一样感慨万千。他回忆起走过的人生道路,只管跌宕起伏,却始终与祖国母亲的脉动和衷共济。祖国与个人,就犹如大海和浪花,浪是海的小儿百姓,海是浪的依托。正如张藜所言,“一首歌词的开句是起承转合的起语,开句与起句的裁定是最最主要的,它有如一幢房屋的门楣和门槛,走进去才洞开一穴而天地顿开,承语、转句、合成,都能顺开句而延伸。”(张藜:《那些词儿》)张藜这样对秦咏诚描述灵感奔涌的切身感想熏染:“第二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瞥见面前晨雾中的巍巍高山,溘然有了觉得,歌词就出来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歌曲主旨一旦确立,久滞的心潮再度澎湃,瞬息爆发的闪电,划破黎明前的阴郁;不期而至的神思,引发出动人的诗篇。“如果说我为填这首词整整憋了半年,憋的便是这两句,这两句选好后的那天清晨真是如释重负。”同样只用了20分钟,张藜就完玉成体歌词的创作。
在当晚举办的中秋联谊晚会上,张藜饱含深情地朗诵了这首新作,“眼圈儿红了,万般心情都涌上心头,我用它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亲人的潜藏于心的思念。”多年往后,张藜回顾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我和我的祖国》抒发的纯粹是我的真感情,我以为铸就了我爱国情绪的紧张摇篮,是我曾经就读的大连商业学校。在学校里,我曾被日本人扇耳光,差点被打去世,而且每天看到的都是唾弃的眼力,深切觉得到亡国奴的悲哀和痛楚,再加上我曾生活在大连的海边,以是我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像海和浪花一朵’。”(王雁来:《花开满竹篱——访作家、词作家张藜》)
《我和我的祖国》歌词朴实大方、亲切动听,第一段以高山、河流、炊烟、村落、车辙等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意象,表达对祖国锦绣河山的赞颂;第二段以“大海”和“浪花”为指代,连用六个排比式博喻,生动形象地揭示出祖国和公民不可分割的血脉深情。秦咏诚惊叹道:“张藜填写的歌词与音乐形象是那么的吻合,它给旋律注入了令人回味无穷的乐思,特殊是歌词措辞的四声,与音乐的旋律十分贴切,毫无一点倒字之处,实在难能名贵。”
这首歌穿越岁月沧桑,依然荡气回肠
《我和我的祖国》创作完成后,秦咏诚从与张藜互助的50多首歌曲中选出16首,请歌唱家李谷一演唱,做成专辑盒带《我和我的祖国》,交由中国录音录像公司出版。在录制过程中,李谷一如预言家般地发布:“《我和我的祖国》能流传出去!
”她在接管央视专访时说:“这是改革开放后最主要的一首主旋律歌曲,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成果……这首歌的歌名是一个很大的打破,祖国好了我就好了,我好了,我努力了,祖国就好了;我依赖祖国,祖国也靠我们,便是不可分割的这样一个关系。”
2004年,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了秦咏诚音乐自选集,书名沿用《我和我的祖国》。在秦咏诚之子秦际凯看来,这首歌今年再度唱红大江南北,也折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中华儿女内心深层次的变革与感想熏染,“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人在国外也受到尊重,中国人的凝聚力多强!
由于有了这个做根本,唱歌的底气都不一样了,是存心在唱,而不是用嘴唱,我唱的时候在传染你,你在听的时候也能吸收到,这便是心与心的互换”。
坚持以公民为中央的创作导向,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这是植根于张藜、秦咏恳切中永恒的信念,历经磨难,初心始终不改;崇奉之火,点亮追梦征程。鲁迅师长西席有言,“创作总根于爱”。张藜、秦咏诚正是把对祖国和公民最深奥深厚的爱,融入《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中,在新中国音乐史上谱写下不朽华章。“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是我们心中永久的歌。虽然两位作者已先后作古,《我和我的祖国》那婉转悠扬的旋律,穿越了35年纪月沧桑,依然荡气回肠。
(作者:黄敏学,系绍兴文理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