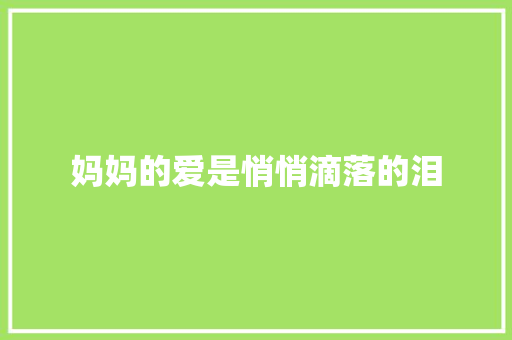题图 | 《梅艳芳》剧照
喷鼻香港词人黄伟文曾为出道不久的Twins写了首《下一站天后》,在2003年4月发行,90后女生大概都会哼几句。这首歌讲了年轻女孩实现明星梦后错失落爱情的遗憾,歌词仍是黄伟文浅白却凌厉的风格——“纵然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旧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若何唱。多少很多多少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顺地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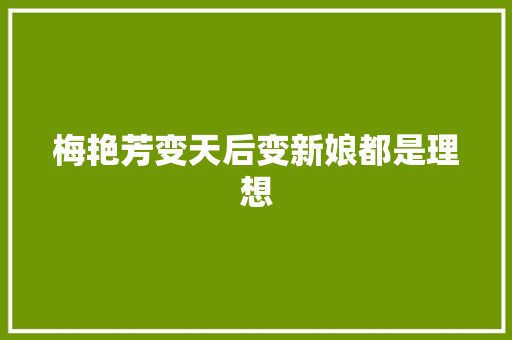
彼时,Twins作为新秀,对歌中奇迹与爱情之间的抵牾仍懵懵懂懂。但是喷鼻香港娱乐圈的前辈,在那一年以身诠释了这首歌的内涵。梅艳芳于11月15日——间隔她离世45天——在红馆举办了末了的个人演唱会,她一袭白纱,演唱《夕阳之歌》前倾吐了肺腑之言:“我穿婚纱好看吗?可惜错过了韶光。我也曾经有几次穿婚纱的机会,但是自己错过了……每一个女性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婚纱,有一个自己的婚礼,我相信自己已没有机会……扑来扑去也落空。”
诚如黄伟文所写,“末了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空想。”
几段恋情,有缘无份。纵使星途开阔,歌迷无数,一代天后终是抱憾。如果女权主义者难以容忍一个女子的梦想是嫁人,那大概也是狭隘的女权主义。最开阔的态度仍该是,嫁人或不嫁人,都可以是一个女性的选择,也都是年夜家的境遇罢了。谁也不必揶揄谁。
天后、新娘
梅艳芳有足够的好运成为天后。《芳华绝代》正应了她与张国荣的星途——“颠倒众生,吹灰不费,收你做我的迷。” 这首歌,后来换做别人唱,总没有他俩对味。
论唱歌,19岁的梅艳芳在1982年举办的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中以一曲《风的时令》夺冠。全体80年代,她风光无限。1985-198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仪式中,梅艳芳连续五届夺得“最受欢迎女歌星”,并于1989年得到“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及“金曲金奖”。论演戏,光凭一出《胭脂扣》,就横扫台湾金马奖、喷鼻香港金像奖及亚太影展的“最佳女主角”。这样的星运,没有谁倾慕得来。
如果天后是梅艳芳实现了的空想,那么成为某人的新娘,便是她未遂的欲望。
站在人生的尽头,她对演唱会的不雅观众坦白:“人生便是这样,有时候你想拥有的东西偏偏没有,我以为自己在28岁或30岁前便结婚,希望在32岁前拥有自己的家庭,但也没有。终于过了40岁,我拥有什么?我拥有你们。但我想提醒你们,如果你们在拍拖,不要考虑太久,不然你身边那一位,想得太久便会作罢……女孩和男孩的梦想不同,女孩的梦想便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庭,拥有爱自己的丈夫,有一个陪伴自己终老的伴侣。”
梅艳芳曾努力捕捉过爱情,在八卦周刊里有迹可循的是邹世龙、近藤真彦、林国斌、赵文卓。最近热映的《梅艳芳》改编了她的两段恋情,大概是电影做了美化的缘故,她与日本男星的感情令人唏嘘。
影片中,走红不久的梅艳芳与日本歌手一见钟情,她随即像所有陷入热恋的女子一样,无心顾及刚刚兴起的奇迹,时时时就飞去东京。在异域,做好三菜一汤等男友回家。大概在最初的日子里,也不是烦懑活,晚饭后,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弹吉他,两人一起唱歌。
但华星唱片的老板苏孝良为她不值,他忍不住提点梅艳芳:“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红了?这些年我见过不少音乐天才,十个有九个都输在不专心。”
然而,哀求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专心,本就太苛求了。如果她真的在20至30岁齐心专心一意专注于自己的奇迹或学业,大概这个社会稍后又会反过来责问她,为什么不在过去十年好好恋爱成家?女性的天下,总是充斥着被议论的声音,永无宁日。
设计师刘培基最通透,用皮尺量着梅艳芳的肩膊,对她说:“女明星贩卖的便是性感。性感从哪里来?七情六欲!
如果至心,不妨年夜胆去爱。”
也唯有爱过、经历过,梅艳芳才能在慢歌中唱出唏嘘,在快歌里唱出背叛。
这段感情以两人分离告终。梅艳芳本着“善始善终有交待”的原则,给男友打去电话,刚巧他正要走出家门,铃声响了,他没有接。多年往后,梅艳芳在病笃之际又去见了前度,两人悄悄走了一段路,他说:“那个电话是你打来的吧?对不起,我当时没有勇气接。错过的爱情,已经成为了人生的一部分。” 梅艳芳声线淡淡:“我以为自己想要平淡的生活,但平淡与否都不主要,主要的是谁陪在你身边。”
世事如此,“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我心想,或许有运做天后,都会倾慕彭羚“加冕光圈变天使”那份甜蜜。天后与新娘,是两种不同的风光。
变天后,在四面台开唱,台下山呼海啸般的礼赞,得到很多很多的爱。这可以引申为一种奇迹上的成功。我想起政治哲学课上谈论女性主义,教授点明现实:如果女性要得到成功,有些人利用自己的女性特质上位,有些人则必须抛弃自己的女性特质,这可能意味着不结婚不组建家庭,这时她才可以专心同男性竞争。
这仍是苏孝良所谓的“专心”问题。西蒙波娃是对的,男性从小到大都被鼓励专心去争取世俗的成功,而女性却一起被险些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哀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
婚姻便是这样一种诱惑。由于很多人难以取得奇迹上的造诣,她们同时被告诫着自己有限期,这时结婚便是退路。不是那么多人都可以变天后的,但变新娘倒不是难事。既然在奇迹上取得造诣那么难,不如走一条大略的路——嫁人,至少在婚礼那一天是风光的。
但是像梅艳芳,缘分段段擦身,台前的热闹与人后的寂寞相映成辉。一个人在诺大的屋子里,总让我想起李商隐那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上苍夜夜心”,那些清冷的时候。她要得不多,至心而已,却偏偏没有。
喷鼻香港女儿
抛却奇迹与爱情的抵牾,梅艳芳的侠气不得不提。天后、新娘各有各风光,但如果做一个侠女,还真了不起。
大家都称她为“梅姐”,梅艳芳确实当得起一个姐字。她讲义气,常说前辈要提携子弟。她提醒身边的子弟:“如果今后碰到肯学的,你们一定要肯教。”梅艳芳对歌迷也讲义气,《坏女孩》由于歌词大胆被电台禁播,公司希望也不要在演唱会上演出。但梅艳芳表示,她是由于这首歌红的,歌迷喜好,她一定要在秀上唱《坏女孩》回馈歌迷。
金庸有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梅艳芳有家国大义,知道如何做一个中国人。一个人的品质,和学历、背景关系不大,她只读到中二,却有一种纯金的品质。1997年,喷鼻香港回归,她没有移民,永久和喷鼻香港站在一起。2003年,非典肆虐,她作为演艺界协会会长,策划1:99抗非典演唱会。喷鼻香港政府不批室内场馆,她和团队就在大球场搭园地,携同众明星筹集抗击非典的善款。港府官员说,之前大球场开唱收到过很多噪音投诉。梅姐回:“如果你们当天收到任何投诉,我亲自挨家挨户上门道歉。”
敢作敢为,与同时期共呼吸,因此梅艳芳才能被称作“喷鼻香港的女儿”。
有一次我看喷鼻香港的清谈节目,谈论为什么现在的明星不像当年的明星那样有星味。高朋认为,造星工业一贯在间隔感和代入感之间探求平衡。英国学者Nick Couldry说过,在大众文化中,出色的明星一定要有间隔感,但在有间隔感之余,偶尔让你以为他是真的。“真”是什么意思呢?比如周润发也会搭地铁。很多时候,明星司帐算什么时候让你看到哪个形象。高朋补充道,随着近十年媒介的转变,曾经主打的影视歌三栖巨星,如今被更多的“邻家女孩、男孩”所取代。明星在社交账户上与粉丝的互动,彷佛把大众与明星的间隔拉近了。
可是在我看来,这种拉近的间隔可能是现在的明星更司帐算如何多多展示“平凡的一壁”。比如他们在真人秀中立人设,镜头面前滴水不漏,他们不但没有星味,一个个都是假人。这样比较起来,当年的梅艳芳名贵的,是那份真,她是真人。
传记电影不易拍。有些会聚焦某一时候或事宜来刻画人物,比如《我与梦露的一周》、《至暗时候》。《梅艳芳》在叙事上聚焦了她的几个人生节点,试图讲述人物的生平,难免有流水账之嫌,于是有人说很多没有拍又有很多不必拍。但如果电影可以传达主人公的精神内核,实在已经足够了。至少,我看到了一个硬颈(倔强)的女性,未在奇迹上胆怯,敢于坦承情感上的遗憾,又有回馈社会的公益心,她活出了自己。
电影有很多值得落泪之处,我是从《Que sera sera》开始泪眼模糊的。在清迈,梅艳芳看到一个小女孩卖唱,自己四岁登台揾食的情景历历在目,两番景象交织在一起: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当我还是小女孩时)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我问妈妈,终年夜后我会变成什么样)
Will I be pretty (我将变得俊秀?)
Will I be rich (我将变得富有?)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她这么对我说)
Que sera, sera (世事不可强求)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统统顺其自然)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我们无法预见未来)
Que sera, sera (世事不可强求)
What will be, will be (顺其自然吧)
女孩的人生总是这样展开的,带着好奇、憧憬,她们将度过普通的或欠亨俗的生平,只是都不会太随意马虎。
正在改变与想要改变天下的人,都在 虎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