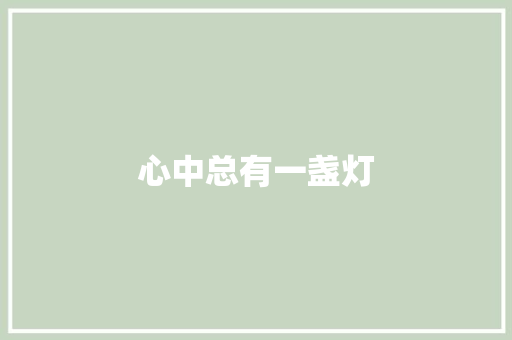雪林间乌鸦盘旋,啼声回荡在听觉深处
天高云淡,碧草如茵铺展,两三头牛嚼着寂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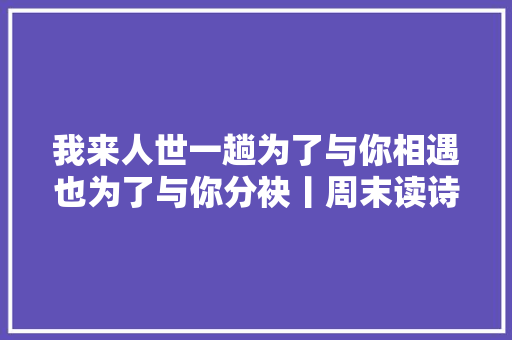
一条白净的小路转身去了山后
铁路桥下,大河悠然流淌,亘古如此
几户人家,寂寂瓦屋,檐前晾着衣服
村落庄土路上,老农扛着锄头逐步地走
一亩方塘,绕堤绿草萋萋,大片水光映照天光
远处浮现朦胧灰影,蜃景之城
闸口外等火车通过的人群,一张张似曾相识的脸
列车追风逐电,铁轨边剧烈摇荡的野草花
横过天边的公路上,甲虫般跑动着一辆白色轿车
落日遍野,山林那边先黑下来
朝火车后方大步逃跑的群山
地平线上,零落几点灯火,为隐没的天下守灵
古老的夜,一轮明月,绕车窗载歌载舞
夜色无边,我梦见一列火车在阴郁中狂奔
《火车外一闪而过的风景》 三书
撰文 | 三书
去住心情知不共
/ /
《上行杯》
(五代)孙光宪
离棹逡巡欲动,
临极浦,故人相送。
去住心情知不共,金船满捧。
绮罗愁,丝管咽。
回别,帆影灭,江浪如雪。
/ /
已附近离去的末了时候,行棹逡巡,徘徊不忍遽去。
“离棹逡巡欲动”,一个细节,急速就能唤起觉得。孙光宪填词,起句多奇警,直击民气,譬如我们读过的《思帝乡》:“如何?遣情情更多。”以及《谒金门》:“留不得!
留得也应无益。”
《花间集》十八位词人,美感互异,毋庸排名,读者各取所好,我偏爱孙光宪。与其他词人比较,孙少监词气骨遒劲,虽闲婉不及温、韦,但能摆落故态,别有一种洒脱之致。
孙光宪出身田舍,自幼好学,生平屡经朝代变迁,历仕前蜀、荆南、北宋,丰富的阅历开阔了他的视野。且据史籍记载,孙光宪性嗜经籍,聚书凡数千卷,订正缮写,老而不辍,多有著述,然而除了古本辑录的八十四首词,传世之作仅余条记小说《北梦琐言》。大手笔而作小歌词,盖如酌蠡水于大海也。
此词所叙别情,并非男女爱情,而是故人之间的交情。“临极浦,故人相送。”朋友送别,唐诗中很常见,在《花间词》中却属奇异。因是送别朋友,故词句有大丈夫气,无甚儿女沾巾之态。“临极浦”三字,细味之无尽黯然,只能送到这里不得不别离了,望着江水滚滚流逝,倍增伤感。
“去住心情知不共,金船满捧。”金船便是大羽觞,可以想见二人相对举杯痛饮而尽。离人与送者,一别之后,海角天涯,心情知不共矣。
就连别宴上奏乐的侍女和歌女,也都愁咽惨沮,把这番意思写成诗,便是“绮罗愁,丝管咽”,以绮罗丝管指代其人,更富深味。
末三句极凝炼,“回别,帆影灭,江浪如雪。”情到深处,无语,孤独。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涯流”,与此词结语异曲同工,节奏与回味却大不同,太白诗境阔大,少监词意抑扬,各具情致,不妨并美。
南宋 阎次于 (传)《风雨维舟图》
燕宋秦吴千万里
/ /
《上行杯》
(五代)孙光宪
草草离亭鞍马,
从远道,此地分襟。
燕宋秦吴千万里,无辞一醉。
野棠开,江草湿。
伫立,沾泣,征骑駸駸。
/ /
孙光宪的两首《上行杯》,俱写送别,一在水边,一在离亭,同样是送别朋友,同样的词调节奏,水行与陆行景致不同,离去的氛围与况味亦不同。
“草草离亭鞍马”,离去总是匆匆,纵然长亭复短亭,送了一程又一程,到了分离的时候,仍不堪草草。鞍已备好,马儿嘶鸣,眼底人虽在,早是万里身。《诗经·小雅·巷伯》曰:“骄人好好,劳人草草。”人在世上,转烛秋蓬,漂沦干瘪,总是行色匆匆,聚散无常。
第二句铭刻下分离的位置,“此地分襟”,这个位置既是空间上的,也是韶光上的,一个凝固的瞬间,永在那里。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饯行于锦江古桥之上,费祎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矣!
”此桥后遂更名为“万里桥”。万里桥是一个关于送别的公共影象,即便是无名无姓的私人影象,也同样无缺地保存在“此时此地”,当你回到离去的位置,就会创造那个瞬间仍旧活在那里,你乃至听得到它的呼吸。哪怕仅仅作为不雅观想,不必实地返回,多少也可感同身受。
“燕宋秦吴千万里,无辞一醉。”燕宋秦吴,皆春秋国名,代指南北东西极远之地,江淹《别赋》曰:“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古代山河阻隔,难通,迢遥的空间间隔,也就意味着漫长的岁月空缺。杜甫与少年时的好朋友卫宾一别二十载,他不禁感慨“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不期而相逢,他觉得像在做梦,特殊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而今夕匆匆一聚,嫡又将隔山峰,世事终归两茫茫。
这首词至此,寥寥数语,写的真是气度豪迈,接下来,朋侪跨马拜别,词笔乃转入细腻。“野棠开,江草湿。”不是为了描写环境,也不是为了比兴,凡是“为了”什么,都嫌太造作太有为,诗乃无为,至文无文。当送行的人被留下,他看到野棠开,看到江草湿,此固是景物,但被他看在眼里,便成了他的心情。野棠仲春开白花,春草方生,小雨绵绵,润湿多少流年。
他伫立,沾泣,眼泪这时才落了下来。朋友的拜别,也是自己人生的部分拜别。大概野棠江草,这些孤独的事物,它们的存在使我们不致过于动荡,就彷佛神秘的星辰,使我们不致过于孤独。
“征骑駸駸”,朋侪策马疾去,头也不回,扬起一串快马的蹄音。读到这里,我们随墨客一起,谛听那征骑駸駸,渐远渐杳,久久弥散。
元 曹知白 (传)《虛亭竹趣图》
离合悲欢,一别两宽
我来人间一趟,为了与你相遇,也为了与你别离。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列火车,沿途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与你坐得近些,有人远些,但我们终归都是过客,各有各的目的地,各看各的风景。即便中途相恋,偕手相拥,到站也不得不下车,转眼之间彼此就不见了。
犹记儿时去外婆家,要走八九里路,早饭后出发,日午前才到,晌饭后不多时,日又西斜,母亲恋恋告归。外婆每次送我们,一双裹过的小脚,拄着手杖,蹒跚走下城崖边那道长长的土坡。到了城下,她坚持要再送我们一程,送到集上,送到村落外,母亲挽留叫她回去,她嘴上答应脚步却不肯停,就这样一贯送到砖厂那边的十字路口,眼看天色将暮,这才怅怅止步。母亲带我和弟弟走了一下子,转头,外婆仍在那里,黑袄黑裤,举着系在大襟上的天蓝手帕,朝我们挥手。我们又走了一下子,转头再看,外婆还在那里,隔着渐浓的暮色,成了一团更小的人影。
一次次的聚散,竟不觉无常,隔些日子总会再去,外婆总在那里。当我们一如既往数着日子,期待再去外婆家时,溘然晴天霹雳有人登门报丧。看外婆一身寿衣躺在木板床上,我仍不相信她已离世,她脸庞沉着得就像睡着了。我不理解去世亡这件事,只以为心里空空,众亲戚都在灵前哀悼,母亲更是哭得形销骨立,我却没有一滴眼泪。待到去了后院,瞥见外婆平常打扫清洁的地方,冷寂寂堆着落叶,土墙角蒿莱野草有半人高,我这才哭了出来。
外婆去世后,母亲常常夜里坐在炕上哭,有一次外婆托梦给她,说自己在那边什么都很好,叫母亲别再难过了,要不她也没法安心。母亲说外婆在梦里笑盈盈,刚刚辞别,随即她就听见鸡鸣,她相信外婆是专到梦中来会她一壁的。
人生漫长,时或度日如年;人生短暂,忽如白驹过隙。就这样,你过完你的生平,我过完我的生平,说短不短,说长不长。
已经第五天了,对面的老妇还没回来,那天我有时起夜,见她的公寓亮着灯,两个人在她寝室里走动,当时就觉得不对,心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翌晨,果真没有瞥见她,我猜或许她提前去子女家过圣诞节了,但是不大可能,几年来从未见她离开过公寓,况且有人拿掉了她餐桌上的赤色桌布,寝室里衣柜的门大开着,衣服一件件挂在那里。接连几天,每到傍晚,别家窗户都亮起灯,她家的几面仍是黑的。不知她会不会回来,厨房窗台上一束郁金喷鼻香,橙红白黄正在开放。那天她买花回来,在窗前瞥见我便朝我招手,她招手的动作有点夸年夜,完了还把双手叠在胸口。明知她已年过古稀,我却一贯以为她在那里,犹如那棵槐树长在街角,犹如秋月东风等闲度,统统都理所应该地久天长。
作者/三书
编辑/张进 何安安
校正/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