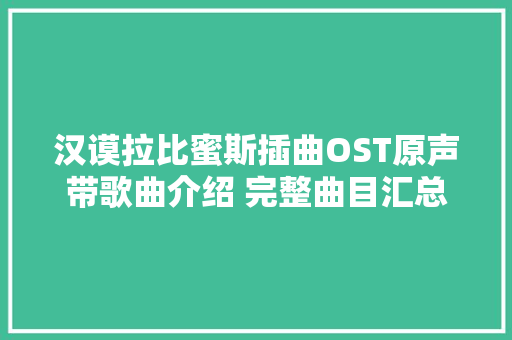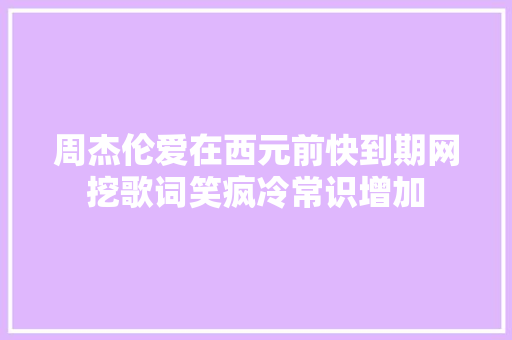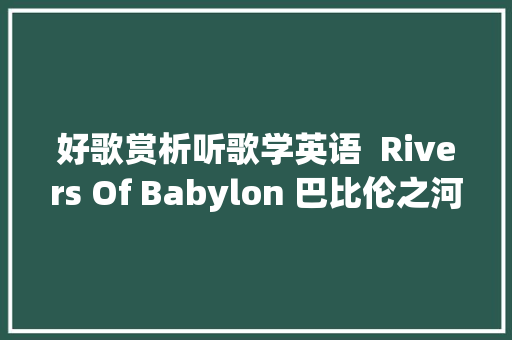“你在橱窗前,瞩目碑文的字眼,我却在旁悄悄欣赏你那张我深爱的脸。祭司神殿征战,弓箭是谁的从前。喜好在人潮中你只属于我的那画面。”
2001年的秋日,引爆华语乐坛的不仅仅有刚柔并济的《双截棍》,还有这首充满他乡风情的《爱在西元前》。西元即公元,是公历纪年在台湾的称呼,这首歌的故事原型是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和她妻子安美依迪丝的爱情故事,韶光跨度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六世纪,“爱在西元前”五个字算是对这段故事最大略干练的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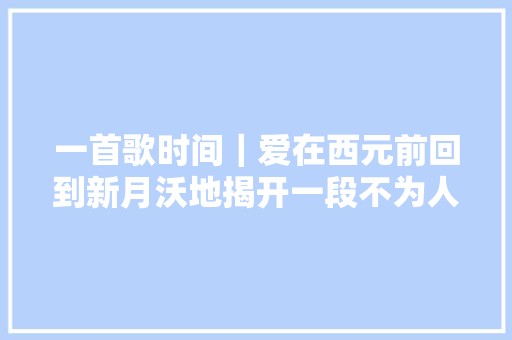
周杰伦的曲配上方文山的词,《爱在西元前》里的故事幽美得犹如中东沙漠绿洲里随风扬起的诗篇。巴比伦文明跻身于天下四大古文明,尼布甲尼撒二世所处的时期更是新巴比伦王国最为壮大的时期——将这样的王国比作人类文明中的诗篇也丝毫不为过。不过在历史的年夜水中,“祭司神殿征战”背后埋葬的更多是战火与兵戈,而至于歌词中“像底格里斯河般的蔓延”的恐怕不是思念,而是红色浓浓的离合悲欢。
红色黎明:我给你的爱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红色的起因,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个丰饶肥沃的月牙沃地。在地球上,大概没有哪个地区如两河流域这般呈现过如此多盛极一时的帝国;也没有哪个地区的帝国如在两河流域这般消弥得迅速。一支支军队如潮涌来,一个个王朝如潮退去,在时期更迭中,这一块刺目耀眼的地皮却不是文明的纹理,而是满目疮痍。
悲剧的紧张缘故原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一块不折不扣的四战之地;而更为悲剧的是,这一块四战之地又从来不缺少强邻。历史上统治过这一片地皮的强大帝国险些数不胜数: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萨珊波斯、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随意挑出一个名字都是当时天下的霸主,随意挑出一个国家都列得出年夜军百万,于是随意看一眼这个名单,也但能感想熏染到其背后有多少杀伐之声了。
从苏美尔人发明楔形笔墨开始算起,当古巴比伦入主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时,两河流域的韶光轴已经翻过了一千五百余年。古巴比伦与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并称为天下四大古文明,但两河流域最早涌现实际上是苏美尔人,而其带来的贡献之一便是《爱在西元前》中“刻下了永久”的楔形笔墨。
比较于埃及草纸上的象形笔墨或是中国纸张上的语素笔墨,楔形笔墨的确显得坚韧得多。楔形笔墨多利用削尖的芦苇杆或木棒在软泥板上刻写,而软泥板经由晒或烤后变得坚硬不易变形,在古代这种技艺很好地办理了文献长期保存的难题。比软泥板更为坚韧的是笔墨本身的张力,苏美尔城邦灭于阿卡德王国之手,后者又亡于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一百年后,古巴比伦王国终于吞并了乌尔第三王朝,这时已经到了公元前1894年——这个姗姗来迟的王国所用的,依然是楔形笔墨。
须要明确的是,巴比伦分为古巴比伦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前者由阿摩利人建立,存续于公元前19世纪至16世纪;后者由迦勒底人建立,为公元前626至539年——而汉谟拉比,正是古巴比伦的第六代国王。
“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刻在玄色的玄武岩,距今已经三千七百多年……”
歌词中的“古”字并非虚词。《爱在西元前》的缘起是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爱情故事,而他是新巴比伦的国王,距周杰伦创作歌曲的韶光相距只有二千六百多年。在“三千七百多年前”到“二千六百多年前”之间的千年跨度里,巴比伦文明遭遇了什么呢?
还是回到汉谟拉比的时期。那时的两河流域的东北信风大约没那么干燥。王座之上,汉谟拉比炯炯有神的双眼带着些许笑意。在持续串战役中,这个国王已经将王国的统治区域扩展至全体美索不达米亚,他或许不会想到一个半世纪之后,古巴比伦便再度被赫梯灭亡。
公元前十世纪,亚述帝国异军突起横扫中东北非——这是一个名副实在的军事帝国,在其统治的三百余年险些无年不战,而其军队又极其残暴,所到之处城镇都被点火毁坏,巴比伦古都也在这一过程中“亚人一炬,可怜焦土”。在经由漫长抗争之后,迦勒底人终于在巴比伦故地重修王国,史称新巴比伦王国。阿摩利人早在公元前1595年便被喀西特人所灭,而迦勒底人则把自己看作是古巴比伦王国传统的合法继续者。
这一年是公元前626年,距耶稣出身还有六个多世纪的跨度,而美索不达米亚上的战役史诗已经交往返回写过了十数个王朝。
同态复仇:用楔形笔墨刻下了永久“用楔形笔墨刻下了永久,那已风化千年的誓言,统统又重演。”
在巴比伦文明里,的确有一个人用楔形笔墨刻下了永久,但这个人不是新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而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他写的誓言当然也不是“思念像底格里斯河般地蔓延”的动人情话,而是充满了血腥与复仇的法律史诗:汉谟拉比法典。
在楔形笔墨的帝国里有部个辉煌的作品,一部是最古老的叙事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另一部便是天下上最早并且完全保存下来的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段玄色玄武岩石柱,故得名“石柱法”。
这个玄色石柱富有极强的仪式感:上端刻有汉谟拉比从太阳和正义之神夏马修面前接管象征王权的权标的浮雕,以象征君权神授;下端是用阿卡德楔形笔墨刻写的法典铭文,共3500行、282条。
之所注明是阿卡德楔形笔墨,是由于楔形笔墨不是某一种措辞的书写办法而是一个书写系统,其对应的措辞有很多种。苏美尔人、亚述人、赫梯人、波斯人等都用或用过楔形笔墨,但这些措辞之间的差异巨大乃至属于不同的语系。比如赫梯语属于印欧语系,苏美尔语属于伶仃措辞,而汉谟拉比法典所用的阿卡德语则属于闪含语系。
汉谟拉比法典的宝贵当然也包括了它供应了一份完全的阿卡德语楔形笔墨文献,但改名贵之处在于它向后人描述了一幅清晰完全的法律图景,通过这幅图景,后世的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得以回味古巴比伦法律的森严与残酷。
汉谟拉比法典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权利责任,一言以蔽之便是人生而不平等。法典将人被分为有公民权、无公民权的自由人的奴隶,不同等级之间的权利责任完备不对等。比如奴隶主将奴隶侵害致去世为无罪,而奴隶不承认主人是自己的主人则当割除双耳。法典尤其把稳保护奴隶主对奴隶“神圣不可陵犯”的权利,以至于收留一不堪主人虐待而亡命的奴隶要判去世刑,理发匠剃去奴隶的发式标记要判砍掉双手。比较于这样句句带血的条文,法典的序言却赫然写着“要让正义之光照耀大地,消灭统统罪与恶,使强者不能压迫弱者。”虽然在奴隶制时期这之间的逻辑顺理成章,但个中隐蔽的屠戮与侵害却不会因此而减少。
另一类是法律原则,依然可以一言蔽之,便是同态复仇。同态复仇是人类原始社会最主要的复仇习俗之一。氏族、部落成员或集体在遭到外来侵害时,受害方给对方以同等的报复,以命偿命,以伤抵伤,加害者氏族或部落则交出惹祸人,以求得全体氏族或者部落的集体安全。同态复仇思想是人类道德的朴素反响,中国汉朝开国天子刘邦曾做出的“约法三章”只有一句话:“杀人者去世,伤人及盗抵罪。”这也是同态复仇的形式。然而,汉谟拉比法典中的同态复仇却详细得有些“萌”属性:
第196条:挖去别人眼睛的人也要被挖出眼睛。
第197条:打断别人骨头的人也要被打断骨头。
第200条:打掉别人牙齿的人将会被敲掉牙齿。
以牙还牙,以骨还骨,以牙还牙的办法在后人看来也没有大问题,不过还有一些条文就显得不那么“明德慎刑”比如“如果在给人做手术的过程中致其去世亡……年夜夫将被剁手”的规定。当然,令人惊异的是古巴比伦对挖眼睛这件事的谜之热衷,除了第196条“以牙还牙”的规定之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条:
第193条:如果情妇或者妓女所生子希望回到生父的家庭并抛弃了养父母,将被挖出眼睛。
第199条:挖出奴隶眼睛或是打断奴隶骨头的人要赔偿奴隶价格的一半。
第220条:如果用手术刀医治肿瘤的年夜夫将奴隶的眼睛挖出,必须赔偿奴隶价格的一半。
更让人惊异的还有第247条:租借公牛却挖出其眼睛者将赔付牛价的一半。
在汉谟拉比法典的统治下,古巴比伦的似血流年,岁月静好。
巴比伦之囚:我感到很疲倦离家乡还是很远
《爱在西元前》的歌词以汉谟拉比法典开始,但更灵感来源却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和她妻子安美依迪丝的爱情故事。在帝国的视野下,王后、妃子如果不做出极其重大的贡献是很难被历史记住的,但安美依迪丝这个名字却被很多人铭记在心,这源于她身后的一栋建筑——空中花园。
空中花园又称悬园,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为缓解其王妃安美依迪丝的思乡之情而建筑的。空中花园听说采取立体造园手腕,二十余米的高台以巨型石柱支撑,之上再建有具备独立灌溉系统的花园,园中奇花异草品类繁盛犹如悬在半空,空中花园之名由此而来。古巴比伦城早已在亚述帝国的铁蹄下被毁,但在尼布甲尼撒二世手中这座历史名城及首都又抖擞了生命力。那时迦勒底人已经制作出了色彩明快的釉砖,新巴比伦城在匠人的经营下披上了多彩的外衣,巴比伦城墙即为其代表。城墙底色为亮蓝,上面装饰着亮白亮黄的狮子、公牛及怪兽图案——城墙的色彩尚且如此华美,就更不用说空中花园了。
空中花园跻身于古代天下七大奇迹,而在这个奇迹背后则是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军事奇迹。在全体巴比伦王国史中,最著名的国王除了汉谟拉比便是尼布甲尼撒二世,而后者的赫赫武功丝毫不逊色于前者。尼布甲尼撒二世一方面与米底王国联姻,一方面积极向西开疆拓土,数胜亚述、埃及等强国,大马士革、西顿等地均称臣纳贡。后由于犹太王国转投埃及,尼布甲尼撒二世一举清剿犹太王国并将耶路撒冷夷为平地。攻陷巴基斯坦之后,新巴比伦基本统一了两河流域,其版图比古巴比伦王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空中花园的建立便隐蔽在这持续串的业绩中,安美依迪丝正是米底王国的公主,她与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婚姻更多是政治联姻而不是爱情的结果,而空中花园是不是与两千年后的泰姬陵一样有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情结,已不得而知。这持续串的业绩中隐蔽的还有其余一个更著名也是更血腥的历史事宜,那便是“巴比伦之囚”。
“我感到很疲倦离家乡还是很远,害怕再也不能回到你身边……”
“巴比伦之囚”事宜之后,巴比伦城的确会响起“害怕再也不能回到你身边”的悲鸣,不过这个“你”指的不是爱人,而是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二世两度征服犹太王国,在这期间尼布甲尼撒二世三次抢夺犹太王国的人口,大批民众、工匠、祭司乃至王室成员掳往巴比伦,这些人便是“巴比伦之囚”。直到公元前538年波斯国王居鲁士灭新巴比伦王国后,这些被囚掳的犹太人才获准返回家园,当然个中有不少人早已客去世他乡。
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不缺的便是鲜血的颜色。在新巴比伦王国灭亡前的第十二年,那个与尼布甲尼撒二世联姻的米底王国也亡于内忧外祸——其征服者也正是居鲁士。这个征服者终极建立起了天下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以两河流域为中央的东、西、北三面的广袤地域都成了波斯王室的领土,而巴比伦文明也终于在些划了上句号。
结语
热闹了几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终于步入了波斯时期,直到此时,离耶稣出身依然还有几个世纪的跨度。作为当时天下上的环球性帝国,波斯将其触手伸向了更西的地方。当时小亚细亚的霸主是吕底亚王国,其国王名克洛伊索斯。面对波斯大军,克洛伊索斯在神职职员手中得到了一条 “你这次出征将摧毁一个帝国”的神谕,然而这一次战役却成了吕底亚自己的墓碑。这时,神职职员才对克洛伊索斯说,那个帝国指的便是吕底亚王国。
相似的战役,发生在几十年后的希波战役中,只是失落败者却变成了波斯帝国。正如《爱在西元前》所唱的那样……
“那已风化千年的誓言,统统又重演……”
只是这“写在西元前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故事从来不是爱情,而月牙沃地上变幻了千年的红色史诗。
作者:江隐龙
编辑:李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