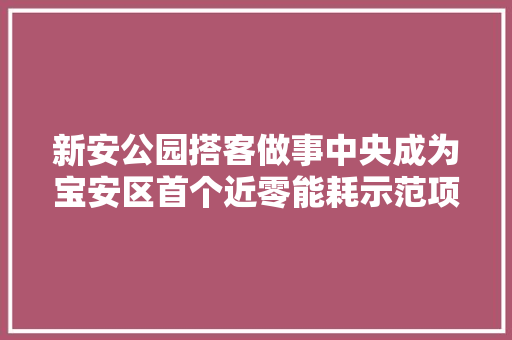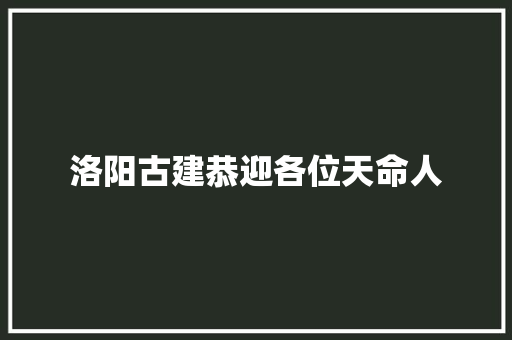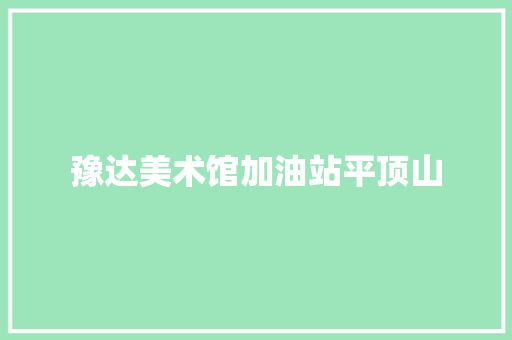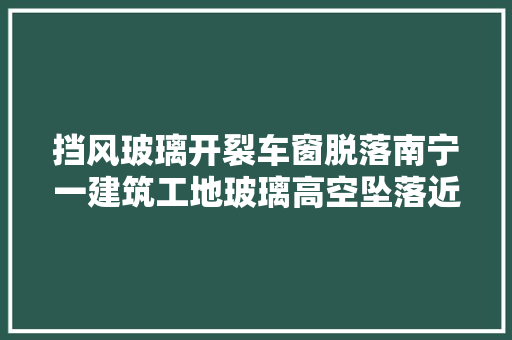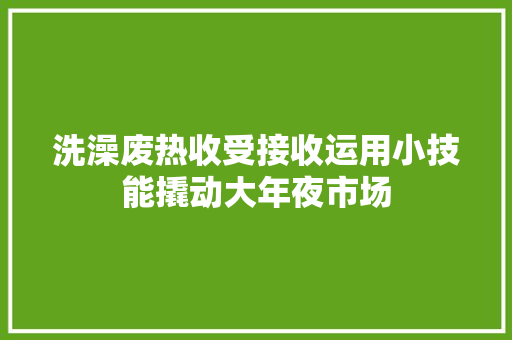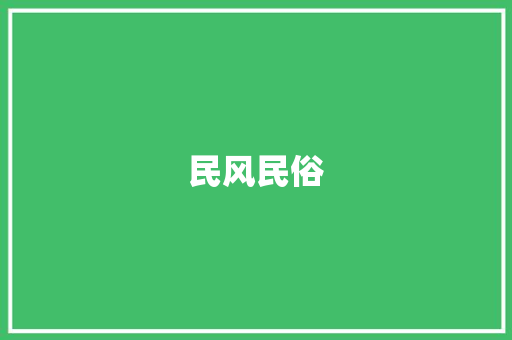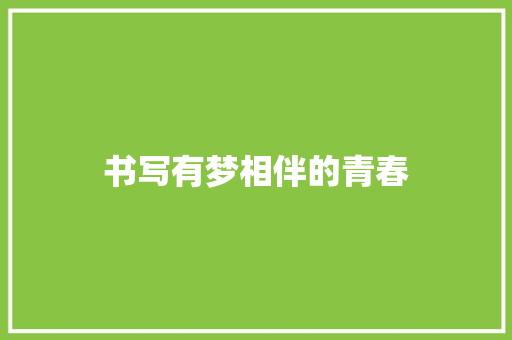张永和解释道,建筑设计师不会喜好听到他的作品像什么、代表了什么,这种思维办法特殊不“建筑”。那什么才是“建筑”的思维办法?
“我对你彻底失落望了”

本次活动的主谈高朋张永和有一张令人瞩目的履历——主持创办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央、曾出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曾任建筑界的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活动中张永和用词平实,听上去亲近,他语速徐缓,带着些许鼻音,是在四合院里终年夜的声音。
张永和,美国建筑师协会院士,非常建筑创始人、主持建筑师,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1984年得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硕士学位,1993年在美国与鲁力佳创立非常建筑,2000年主持创办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央,2005年出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成为首位执掌美国建筑研究重镇的华裔学者,2011年至2017年任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
天安门不雅观礼台的设计师伸开济是张永和的父亲,中国第二代建筑师代表人物名号分量不言而喻。这份重量没有压倒张永和的童年,在张永和的回顾文章中,他和哥哥是被放养终年夜的,没有被干涉干与过学习,没有被检讨过作业,算术没考好是一件不值得垂头丧气的事情。
而等到终年夜成人,事关专业,压力便显现了踪迹。年轻时的张永和在伸开济访问美国见到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时溘然冒出一句“往后我也要当哈佛建筑系主任”,伸开济即刻露出痛楚的表情。
“我自以为口出年夜言,赶忙为这没边儿的野心道歉。不想我父亲却说:当个系主任算什么,你的野心太小了!
要做就做个好建筑师!
”(见《作文本》内《我的家教》一章)
由于记住这一句训导,张永和在麻省理工当了一届建筑系主任就辞职了。后来他返国从事建筑实践,常常与父亲发生争执。在活动中他有一晚北京停电,百口没事做只能坐在一起“大眼瞪小眼”,伸开济对张永和说了一句话:“我对你彻底失落望了。”
“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吗?”
“心里瓦凉瓦凉的?”(活动主持人语)
“我一下子就放松了。”
《作文本》
张永和 | 著
世纪文景 | 上海公民出版社,2023年9月
古典主义与当代主义的结合
张永和与伸开济的冲突,来源于理念的差异。张永和在建筑设计中想解一道题:古典主义是如何一步步演化为当代主义的。古典主义与当代主义在某种过渡期的形态下不会有那么强的对立,可以相互结合,从而涌现一些自由的打破教条的想法。“我父亲可能是古典主义学得太好了,以是一脱手就更是古典主义的做法。”
古典主义,对付张永和而言不是大略的对称,它是克制的设计,意味着严谨、简洁、安静。安静不总是和谐的,尤其是张永和的安静,可能是令人不安的。
《图画本》中张永和少数几张画作之一,约创作于1985年至1988年间。画中宁静的风景和令人不安的地下空间存在强烈反差。
戴锦华如此形容她在现场看到张永和建筑作品时的震撼:极度方正、极度工致,强烈的不雅观念性表示在建筑的每一个细节;在方正和工致中含有很多大胆的元素,乃至搪突了设计的传统。我们或容许以举张永和一个设计案例来佐证。
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央主任。紧张研究方向为电影、大众传媒与性别研究。代表作包括《浮出历史地表》《雾中风景》《昨日之岛》《性别中国》等。
从前张永和留美没有什么实操的项目可做,进行了大量玄想式或为竞赛而做的设计,这些设计图纸已搜集在《图画本》中出版。1991年,他为《新建筑》国际住宅设计竞赛做了一份设计——垂直玻璃宅。
《图画本》
张永和 | 著
世纪文景 | 上海公民出版社,2023年8月
“少即是多”的提出者、当代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MiesVan der Rohe),因对钢构造框架与玻璃在建筑中的运用践行了一种古典式的简洁艺术而有名于世。他最为众人熟知的建筑作品之一是坐落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范斯沃斯住宅(Farnsworth House),住宅四周全部都是玻璃墙体,对四周景致一览无余,室内空间在视觉上融入了室外空间。
在张永和看来,这种水平层面上的玻璃住宅暗含了一个局限——缺少私密性。它只能存在于封闭的私人园林里,与高密度的都邑环境相抵牾。以是他设计了一个可以在城市中存在的透明空间模型、一个垂直玻璃宅,每一层的楼板以及屋顶是玻璃的,四周的墙体是不透明的。墙体割断了住在个中的人与周边城市的关系,透过玻璃看到的是上面的天空和下面的地皮,张永和曾写文章道“实墙的极度城市性反为回物化然做了准备”,将建筑的表达与精神的诉求相连。
“曾想到西晋的刘伶,他声言‘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于是总是裸居于家中。从刘伶的角度看垂直玻璃宅,天地便是这宅子的一部分。”
垂直玻璃宅有多份草图,分别由水彩、彩色铅笔、墨线绘制,张永和说他利用水彩去营造材料、光芒、韶光和气氛、黑白图更具剖析和抽象性,而其他媒介更有空气感,更适宜探索透明性。上图用铅笔和水彩绘制,多层透明楼板构成透镜。收录于《图画本》。
垂直玻璃宅草图之一,用铅笔和水彩绘制,图中含地窖、天窗平面、地窖剖面。
垂直玻璃宅每一层设计得极为方正,四分空间表示了东方空间的等值理念。张永和曾比拟过中西方住宅,西方住宅房间与功能一对一,不同房间的尺寸和位置与此干系,彼此仿佛存在等级关系。但是传统的中国住宅不同,不存在这样的等级关系,它们在建筑上是等值的。在文化上不一定等值,比如正房和厢房的差异。
如今垂直玻璃宅已经从想象变为了现实。2013年垂直玻璃宅已落成落成,加建的咖啡厅 “水平玻璃宅”将于2023年年底之前落成。
建筑的实质是“盖屋子”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什么才是“建筑”的思维办法?作为一名门外汉,在听活动对谈与阅读《作文本》《图画本》中,我有一些模糊的感想熏染。
建筑是理性的,它可以是艺术的,但首先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石上。张永和在设计玻璃住宅时首先会考虑它如何能融入它所在的环境里,便是一种理性。活动中张永和谈到,一项设计如果只是在图纸上好看,但在造屋子时涌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会让他极度困扰。
他认可“本体建筑学”,认为建造及材料与节点,空间及利用与感想熏染,建筑与基地、城市及地域的关系,构成了建筑学的核心知识。建筑是文化性的,但它的实质便是“盖屋子”。
建筑有一套属于自身的语汇,在这套语汇之下,建筑师关心的基本元素和普通人有相称大的差异。构建一个屋子的语汇体系,不是大略的象形逻辑,它不是像某些类型的绘画、像汉字的早期在模拟真实天下。而在符合理性基本哀求的条件下,建筑也将成为一种表达,一种搜集了设计者过往人生痕迹的表达,表达终极塑造了一种空间感想熏染,抵达身处个中的人。2003年,张永和曾写下一篇描述北京的文章《物体城市》,看他视角中的城市,或容许以一窥他看天下的办法——
“我也有一个城市的故事可以讲讲……”
“我是在一个水平城市中终年夜的。从空中看,这座城市像是一个向天涯展开的坡屋顶的海洋。冲破这灰色瓦浪的知识院落中飘出的葱茏的绿色以及城中城辉煌的金色……水平城市是看得到的,然而,一场革命将颠覆水平城市的清晰。个性以及垂直性将在城中崛起……”
“1959年,民族文化宫:长安街上一座对称且自我完善的白墙绿瓦建筑,建筑的对称轴上矗立一栋13层、67米高的纤细塔楼……”
“曾经一度连续、和谐的城市景不雅观现在被无关联的形体张扬的设计和不断增高的摩天楼的罗列取而代之……终极物体城市是无肌理城市。”
“公共交通系统不敷或失落效、交通堵塞、社区破碎或封闭、城市空间不明确、缺少公共空间与步辇儿街道、缺少真正为低收入居民的公共住宅操持……都是物体城市的范例症状……”
“物体城市可以转译为:希望城市、野心城市、贪婪城市、机会主义者的城市。”
“但物体城市不应是唯一的答案。随着经济急速增长和社会巨大变迁,至少还可以涌现:冒险城市、开放城市、机会城市(而不是机会主义者的城市)、不定性城市。”
《图画本》收录了一篇策展人王蕾(Shirley Surya)对张永和的采访,采访内容能让我们更清晰理解张永和设计理念来源与变革,理解绘画艺术、电影与文学给他带来的影响。摘录部分如下,内容有删减,人名采取原书标识办法,“S”指代王蕾(Shirley Surya),“C”指代张永和(Chang Yonghe)。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内向履历的探索
S:您曾经提到过绘画可以是一种“冥想”的行为。您如何通过绘画这种媒介来探索您所感兴趣的命题,无论是自己设定的还是基于项目的?
C:我不认为绘画是冥想的过程。对我来说,首先必须静下来,将把稳力完备集中在画画上。这样,绘画才能帮我进行对建筑、艺术等的思考。这险些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画的同时又从画中得到启示。于是,便推进了所思考的问题。终极,对付建筑来说,绘画是不足的。绘画曾经在一段期间内对我十分主要。但画了八年图之后,我对盖屋子的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S:为什么会有这种渴望?
C:由于仅靠绘画已经无法连续拓展我的一些建筑想法了。
S:我把稳到您的绘画中有一些反复涌现的主题,比如叙事、文化识别、居住或者家居生活,有时对某些建筑原型进行反思,以及您称之为“内向履历的探索”等。什么使您对这些主题格外关注?
C:这些主题中有一些和当时建筑圈内的关注点有关,包括后当代主义以及当时正在兴起的数字建筑等。但是我的兴趣在其他地方。比起功能性,我更把稳居住性,即人们是如何现实地而非抽象地体验或者感想熏染空间的。一种在某处的感想熏染每每和某种特定的活动干系联,有一点仪式的意味。活动的仪式性非常主要。或许,这便是我眼中人们和空间所建立的形式关系。更进一步来说,这或许便是我对建筑形式的认识—形式来自仪式,形式存在于空间中。以是,我从未对建筑物体有过太多兴趣。
“内向履历的探索”是类似这样一种感想熏染:在一个空间当中,光芒从上方以一种特定的办法进入,这个空间就有某种特定的形状,你一个人坐在正中心一把椅子上,独自抽着烟;我并不吸烟。在那个状态下,空间、光芒、家具以及吸烟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S: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内向履历的探索”?
C:由于这是在一个空间内部的感想熏染,而不是从外部去看一个建筑。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履历。
S:以是这完备不是一种思考某些问题的自察的过程?
C:对,这不是。冥想并不是我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只管画画的时候我常常是一个人,但是我并没有冥想。我享受的是创造画中空间和各种形象,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去创造。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我想那是一种类似“研究”的过程,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而是艺术意义上的。许多电影和小说都能帮助我更好地去“看”,尤其是卡夫卡的作品。我曾看过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导演改编自卡夫卡作品的电影《审判》(Le procès,1962)。这部电影太棒了!
它是“超现实”的,但是如果考虑到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艺术运动,“超现实”彷佛又不能准确地形容这部电影了。它是如此扎根于现实,表现了一种现实的状态,既真实又不真实。电影拍摄于1960年代,以是那里面有1960年代的现实,但是所表达的却远不止这些。看上去没有什么是不屈常的,但同时又没有什么是我们所理解的现实。
弱的形式,
并非无力的形式
S:您提到文学,比如卡夫卡的作品,电影以及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都对您的绘画办法和内容有所影响。您是否可以分享一下,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创作出这些绘画作品的?
C:我考试测验着阅读一些理论书本。对我来说,它们非常难懂。我努力并且也读懂了一些东西,但是也没以为有太大用途。然而,在阅读文学和不雅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我能感想熏染到很多。常日,我感想熏染到的东西每每会相称永劫光地留在我心里。这也是我现在所面临的抵牾之一,由于目前我在中国开展的事情每每哀求强烈的视觉效果,而非常建筑的作品在这方面却非常“弱”。
S:哪方面的“弱”?
C:视觉上弱。
S:对付人们的期待而言?
C:是的。当下你能看到非常多特殊强烈的形式。但是我们的作品不是的,现在依然不是。弱的形式并不是无力的形式。我认为无力的形式是那些不能带来持久体验的形式。在小说和电影中,我能感想熏染到一些令人不能忘怀的体验。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小说和戏剧就能给人这种感想熏染。
我对“极简主义”的理解便来自萨缪尔·贝克特,并不是由于他的措辞,我想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大略短句在措辞上比贝克特更“简”。贝克特的极简并不表示在措辞上,他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极简生活办法。他有一部小说名叫《马龙之去世》。小说的主人公马龙,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口袋里的三块石头之外,空空如也。这些石头没有纪念意义,也没有任何戏剧性,但它们是有功能的、实用的。主人公会把一块石头放进嘴里,由于石头的温度比嘴巴要低一些,以是放在嘴里可以让他感到少许风凉。以是那是用来含在嘴里的石头,仅此而已。这才是“极简”。
后来我在印度看到一些朝圣的人,他们也是如此生活,浑身高下只有一件托蒂,白天朝拜的时候穿着托蒂,晚年夜将它脱下来洗,赤身而睡。在印度的景象下,洗过的托蒂很随意马虎就干了,以是每一天他们都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色托蒂,显得精神奕奕。托蒂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但是他们却以非常有肃静而且神圣的办法拥有着这唯一一件家当。与此相反的是在美国,人们穿着牛仔裤,吃着烤肉,然后随手把油往裤子上一擦。那是一种完备相反的生活办法。
在规则建立之前
S:建筑中的后当代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对古典主义,包括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和古典主义建筑的兴趣?
C:你的问题包含两个观点,一个是古典主义,另一个是文艺复兴早期绘画。这两者都和我的背景有关。我在中国终年夜,不过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西方教诲的影响,比如数学、科学、艺术、绘画和古典音乐等。以是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那便是,我以为任何事情都有精确的做法。比如,画人像时必须力求画得越像越好,作曲必须遵照一定的法则,学习音乐必须节制精确的知识和技能,等等。当我二十几岁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所拥有的全体知识体系里有着非常多的限定——这些知识本身便是束缚。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到,我想超越自己以前所做的和所知道的。我想冲破所有这些限定。
中国画非常主要,但是中国画和西方的系统没有任何联系。以是我反而更随意马虎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由于我知道那些作品创作于规则建立以前。透视法很主要,它表现的是不考虑韶光维度的、准确的数学打算和空间建构。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创造,只管文艺复兴早期的画作中常常涌现一些“奇怪”的画法,比如不符合数学规律和透视法等,但它们实在有着非常清晰的逻辑。那是一种自由的逻辑,至今我对此仍十分感兴趣。在特定作品中,人们想要表达和塑造特定的内容及空间,以是就须要发明一个特定的逻辑出来。由于他们没有数学或者透视法这些终极真理的限定,以是也就没有任何禁忌,尽可以考试测验各种不同的东西。
S:指的是视觉表现方面的考试测验?
C:还包括画中的空间、叙事,等等。我是从我的老师罗德尼·普雷斯那里学到这些的,是他将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作品先容给了我。这些作品非常奇妙。乍一看什么都是错的,可一旦弄明白了,就会创造它们不仅不是错的,而且还颇具逻辑性,只不过那是一套不同的逻辑罢了。这些早期绘画远比后来的更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一贯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作品会这么有创造力?由于它们没有受到体系的限定。福柯指出“终极真理”并没有太大的意思,由于就算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超越界线,才能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S:以是您一贯在探索这些不一样的维度?
C:我真正关注的是早期文艺复兴绘画中的空间与叙事。至于古典主义,它曾经而且现在依然对我很主要。紧张表示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和我的历史不雅观有关,我认为历史和韶光是连续的,不能被切割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古典精神,那里面存在着一种特质。自密斯·凡·德·罗之后,有不少非常故意思的建筑师,包括让我对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产生兴趣的德国建筑师翁格尔斯(Oswald Mathias Ungers)等。现在英国的一些建筑师,比如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和托尼·弗莱顿(Tony Fretton),正在延续着辛克尔和翁格尔斯的古典传统。在形式上,我比拟例没有兴趣,完备没有兴趣。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我在南京工学院接管的是一种巴黎美术学院式的古典主义建筑教诲,但是却完备不提欧洲的古典主义,由于那在当时是不被许可的。
S:这种巴黎美术学院式的古典主义建筑教诲和欧洲的古典主义有什么不同?
C:非常不同。在实质上两者是一样的,有着同样的基本原则和主题。但是,在欧洲,人们会去考虑柱式或者某种装饰系统,由于这些都是古典主义建筑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我却没有学习这些,但是古典精神是一样的,那种特质是一样的,与特定的风格无关。
古典精神中有种很严谨的东西。古典主义的核心或许并不是和谐,而是一些非常大略的东西。古典设计是克制的,不会去添加任何无关主旨的东西。以是,对称是可以的,但是重点不是轴线,而是对称很简洁。
如果你去自然中不雅观察,会很随意马虎创造对称,由于它们大略,一半和另一半是一样的。在黑泽明的电影《蜘蛛巢城》中,对称的观点就非常主要。电影中,所有的空间都是一点透视的,以是也是对称的。如果有两个人,那很显然是对称的。在其他情形下,一点透视也是对称的。我说的便是这种特质!
我不在乎形式上的比例,也不在乎山墙或柱廊,这些东西在以前和现在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这便是我所谓的古典精神。
很可惜,现在我所做的东西还不太具有这样的精神,但是我打算在我的事情中更关注这个问题。再强调一下,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和谐。由于和谐和沉着有一定关联,而我感兴趣的是安静,但是我的安静也可以令人感到不安。我想在建筑中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但是在现在的一些项目中,这非常困难。我在为一个物质社会事情,它的实质是享乐的。大略的生活有一种安静的张力,我的作品还没有表现出这一点来。随着年纪的增长,这是我越来越急迫想要追求的。
最近和同事们谈到一些意象,个中一个对我来说比较主要(在纸上画起草图来):当我和同事们提到“亭子”的时候,他们常日想到的是这个(指了指刚画好的草图,一个传统的中式翘檐亭子),这没什么错。但是我想到的却是这个(接着画了一个有着直线条屋顶和柱子的亭子)。说到这儿,我们现在正在为四川安仁的博物馆建造一个最基本的亭子。它有屋檐,但是却没有这些(手指着草图中的翘檐),这些并不主要。建筑从屋檐处收进,以是它像所有的亭子一样有阴影。如果加上门的话,那便是一个立面。仅此而已,这就构成了一个亭子。它是非常古典的。
S:从哪方面表示出来?
C:对称、完全,等等。我现在和你讲的东西,在我脑海里是非常清楚的,不过我并不期待你能完备地理解它。这是非常个人的东西,是我个人对建筑的理解。不过,等安仁的博物馆落成之后,大家就都能理解我的想法了。
“我便是想很‘土’”
S:接下来的话题和您刚刚谈到的内容有关。您1980年代早期的许多绘画和关于这些绘画的笔墨作品中,常常会涌现比如“营造”“亭子”“风水”等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您提到这些是您故意要去探索的命题,由于过去在中国对这些没有太多打仗。您乃至曾经将东方和西方明确地区分开来,比如在作品《四间房》中所表现的那样。现在二十年过去了,东西方的这些差异还那么明确吗?还是已经界线模糊了?“中式”的定义中,有没有加入新的元素?
C:这个问题不大略。在实践中,“中国性”是很难用措辞去描述的。就像这样(指着先前画的两张草稿)。这个是中式的(指有翘檐的亭子)。但是我认为这种联系是不对的,这样很随意马虎掉入东方主义或者中式媚俗的陷阱。19世纪进入20世纪往后,尤其是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那个时期,它就演化成这个样子了(指直线屋檐的亭子)。
S:为什么演化会发生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这段特定的韶光?
C:这是我的简化版的社会现实主义(指直线屋檐的亭子)。这些仍旧是“亭”,界线并不模糊。从紫禁城的太和殿到陵墓,我能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
S:这个问题不太随意马虎回答。
C:不随意马虎。
S:不如我们跳过这一题。
C:不,不用。这个问题很主要,和人们对非常建筑的作品的意见特殊干系。一种意见是,我们的东西“时时尚”——这可以算作是一种表扬。而另一种意见就不能被当作是表扬了(开始在纸上写中笔墨),人们说非常建筑做的东西“太土”。
S:时时兴?
C:我来阐明一下。如果能搞明白这一点,那么你就能弄懂很多东西。(在纸上写中笔墨)这是“太土”和“太洋”的比拟。“洋”始终是一种褒奖,它意味着都邑感、国际化、外国的,而这些词在中文里都是褒义的。“太土”不只是说这东西是本土的、城市以外的,而且还有粗鄙、乡气的意思。如果你是屯子来的,那么你很可能就很土。以是你看,这里面的差别在于——一个漂洋过海来自外国,一个土生土长,以是很乡气。
S:轻微打断一下,以您来说,我以为您会一贯一只脚在国外一只脚在这里。您无法回避“洋”的一壁。
C:“土”是人们对我作品的非正式的批评。由于你认识我,而且我们现在正在用英语发言,以是我或许比这里大部分的人要“洋”, 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去那些有这个的地方(圈出纸上的“太土”两个字),我便是想很“土”。
S:是不是由于您想扎根于您从事事情的地方?
C:不,不是那样。是由于从某种方面来说,那样更加……像我自己,而且我以为那样会更有趣。我不是一个随大流的人,以是那些时髦的、主流的东西对我没有太大吸引力。参数化设计或者某些主流的形式措辞等,这些都不是我。我以为我们正在评论辩论一个非常主要,但是很可惜,又有些难度的话题。
S:对付其他和您绘画风格相似的作品,您有什么想法?您曾经提到过,只管别人也用类似的方法来画画,但是从对建筑设计作品的影响来看,对他们的影响要远小于对您的影响。
C:这是其余一件事,要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古典绘画或者效果图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有很多人比我更在行。但是我用这种办法诠释的是完备不同的一种建筑。再者,我相信,抽象(这或许不是最确切的词语)和当代的觉得也同样主要,而我的画中也有这些元素。我懂得如何去欣赏杜尚和毕卡比亚这一类的艺术家。我一贯在考试测验将古典主义和当代主义结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希望这样能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安仁的亭子可能便是这样的作品,是我的“中庸之道”。
收看活动回放
运营团队
本文整理 吕婉婷
本文编辑 吕婉婷
海报设计 世纪文景
本文校正 卢茜
本文图片 世纪文景供应
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
从属于新京报的文化领域垂直媒体,自2003年创刊以来,新京报书评周刊深耕于文化出版动态,向读者供应有关文学、社科、思想、历史、艺术、电影、教诲、新知等多个领域的出版动态与学界动态,供应诸如专题宣布、阐明性宣布、创作者深度访谈等深度文化内容。
2019年,新京报书评周刊基于现有内容资源,推出了“文化客厅”系列活动。文化客厅线下活动,旨在通过与读者的真实互换,建构立体的内容传播办法,与真实的个体共同理解并见证时期的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