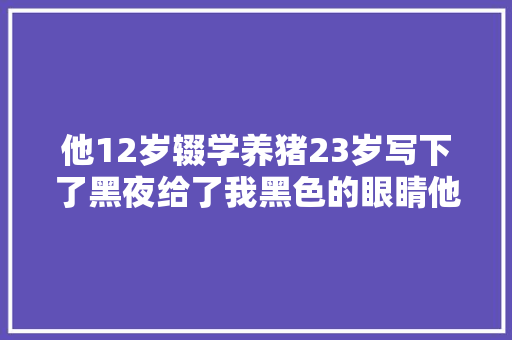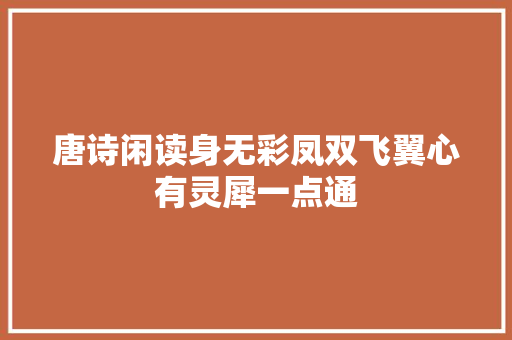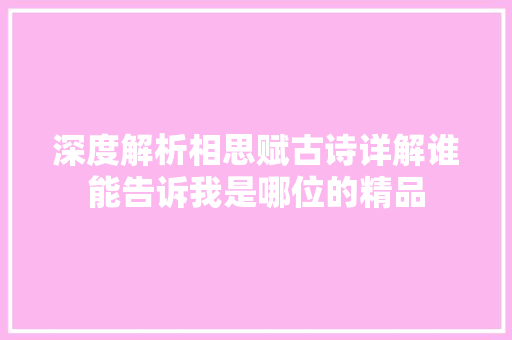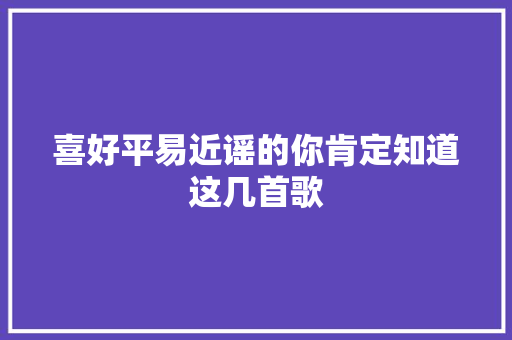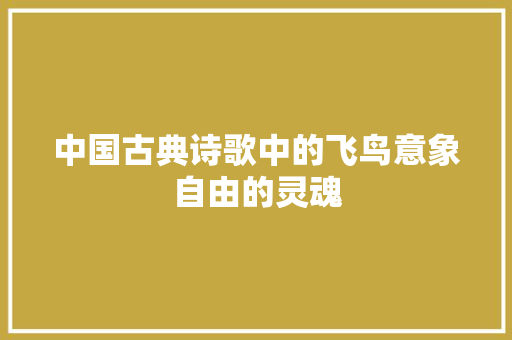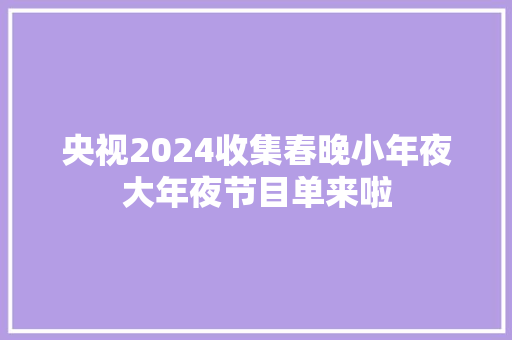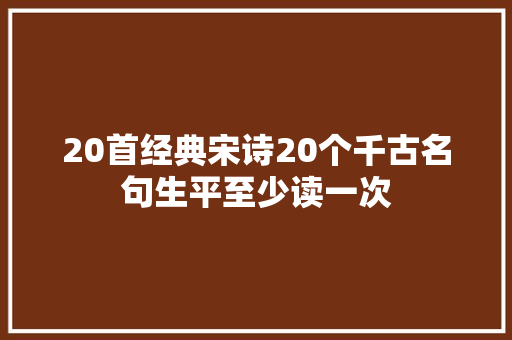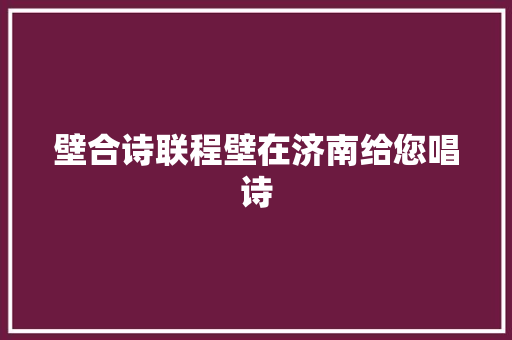撰文|季体 视觉|玉琪
统统都要从昨天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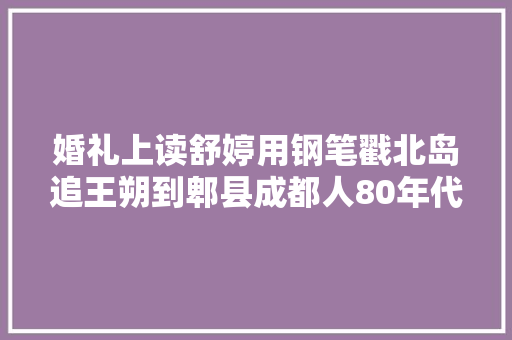
这个昨天,是个精确的日期——适逢天下读书日,在成都邑图书馆展品中,我们瞥见了舒婷和汪国真的手稿。
这几页纸菲薄,沉着,但背后代表了更远的昨天的激情与日常。
我有点不愿定,我们是否还记得墨客和成都人曾经的真实生活。
1980年代,在一些文艺青年的婚礼上,朗诵舒婷的《致橡树》成为婚礼上的必备节目。北岛的“路啊路,飘满红罂粟”则成了一句港台味儿的盛行歌词,被城乡青年不明就里地哼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回去问一下妈老汉是不是这样的……
舒婷是1952年生人,汪国真小一些,1956年出生。汪一度是一个铣床工人,1978年凭借阅读功底,考上了暨南大学中文系。
汪国真走红的韶光是1990年代,第一部诗集为《年轻的潮》,曾经在1990年代掀起“汪国真热”。
在电脑和互联网没有大行其道的时期,汪国真的诗又被达州人庞中华“加持”,红上加红。
当年《庞中华钢笔字帖》有多火?问一下你身边的70后、80后就知道了。网上有句神评论:那些被父母逼着练庞中华字帖的孩子你伤不起!
少年庞中华的空想是当一名墨客,李白是他的偶像。17岁那年,《重庆日报》上揭橥了庞中华的组诗,他一下子成了同学中的名人。
但很快,有人兜头给他泼了一盆凉水,“我学的是地质,老师就说庞中华你想当墨客,这是不务正业;大伯也说,你写诗歌写得不好,随意马虎犯缺点。”
▲当年在地质事情中仍旧在“划拉”的庞中华。他后来成为了天下皆知的硬笔书法家。庞中华本人供应。
薄薄32页的《庞中华钢笔字帖》,当年定价只有一角钱,巨大的市场爆发力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滚滚利润。而且,也让庞中华阔别了他大伯当时的担心,“犯缺点”。
提出出版这份字帖的是一名下海不久的编辑:尹明善。现在,他仍旧是一个弘大商业集团的主人——力帆。
那时候大家都想成为墨客。
北大毕业后进入中心办公厅事情,从事政治系统编制改革研究的吴稼祥,当时曾和同乡叶匡政一起在诗歌报上揭橥诗作,他曾在博客上贴出自己从前写的当代诗(1991年所作),“纵然爱的风标没有转向,地上的双脚想已被拖入另一种生活。”
90后和00后很难明得的是,墨客,曾经在1980年代有过摇滚歌星的报酬。
精确点,是摇滚巨星。
BTW,在墨客小明的影象中,那时坐公共汽车缺钱,喊一声“我是墨客”竟可免票。
一贯到90年代,追球员的热潮中,魏大侠魏群还收到过一名女球迷的来信——里面誊得清清楚楚的一首戴望舒的《雨巷》。
一
被粉丝逼进厕所的北岛
诗歌究竟曾经有多红?
先看一张照片:
▲上个世纪80年代,诗歌氛围浓厚,辽宁义县七里河公社石卜子大队21岁的女社员才素莲,在田间向社员朗诵自己的诗作。
这是辽宁,屯子。
一度以诗歌著称的成都,又当如何?
1986年底,成都星星诗歌节:开幕那天,只管有纠察队坚持秩序,没票的听众还是破窗而入。他们冲上舞台索要署名,“钢笔戳在墨客身上,生疼”。
北岛后来在《朗诵记》回顾了这些。
“那时的诗歌写作讲究铿锵有力,像我的《回答》,朗朗上口。那与其说是朗诵,不如说演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在听众的蜂拥冲击下,北岛等人不得不躲进厕所,对征采者谎称“我们不是北岛、顾城”,随后翻窗逃跑。
同时在场的还有很多墨客,舒婷、顾城等人也在。在被“包围”的过程中,据拍照家肖全回顾,顾城特殊生气:一定要出去,他们又能把我如何?!
肖全还拍下了谢烨在一旁哄顾城的照片。
搞一个笔墨互换会,末了“割须弃袍”,不独是墨客们的遭遇——纵然是学者刘再复和李泽厚的美学演讲,也曾由于听众太多三易讲坛,台下尘土飞扬,索求署名的听众差点掀翻了桌子,李泽厚还由于“讲得太少”遭遇强烈责怪,二人在保护中撤走。
2013年9月7日,墨客北岛在成都白夜酒吧。这一天虽然热闹,但不复有“仓皇北顾”之尴。拍照|肖全
一贯到今年疫情之前,北岛时时时都会来成都。
拍照时仍旧是一副严明的样子,朋侪调侃说,“像省长”。
毋庸置疑的是,墨客——哪怕是莫言,也再难见到当时那种粉丝踩掉鞋子般的战斗场面了。当阅读日渐小众,一个小青春偶像给成都年轻人带来的影响,大概比墨客要强N倍。
四年前,张艺兴在东郊影象,D叔亲眼目睹:一些小娃儿激动得跑掉了鞋子。
二
大凌晨被墨客喊醒的火锅店主们
诗无达诂。
这是对付诗而言的。但对付墨客,乃至仰慕墨客、诗的人来说,还代表了随便说,随便想,所谓自由。
在一次清华大学的诗歌朗诵会上,政法大学学生王俊秀第一次见到海子。
在评委席上,牛仔裤络腮胡子的海子和谢冕邻座。当一个女学生上台朗诵时,身为评委果海子听到某一句诗竟拍起了桌子,让王俊秀以为他“特殊暴躁”。
海子的暴躁受到了女学生的回嘴。当她连续念到一句“我的爱人,你的脸像食堂的烧饼”,海子又开始拍桌子,众评委则掩面大笑。
实在,爱人的脸确实是可以像食堂的烧饼的。
我饿的时候,看谁都像烧饼。
墨客万夏回顾的成都墨客生活,现在看来特洒脱:
墨客们会吃,会生活。
以李亚伟为例,1982年开始当代诗创作,1984年与万夏、胡冬、马松、二毛、胡钰、蔡利华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1993年下海做生意,常年来回于北京和成都间。
作为80年代最有名的墨客之一,李亚伟的诗歌最早多以在酒桌上朗诵的办法揭橥,后以一首《中文系》被传抄遍全国各大学的中文系。李亚伟在诗歌写作中表现出的卓越的措辞才能和反文化意义,使他被认为是“第三代”诗歌运动最有影响的墨客之一和中国后当代诗歌的主要代表墨客。
不管李亚伟或二毛,都是厨神、贩子和墨客一体的生活者。在宽局促路,他的喷鼻香积厨迎来送往,连续着李劼人之后的成都传说。
我是从这个角度理解个中的魔幻的——犹如1938年出生的尹明善有次接管CCTV采访时,他本意是要给犯了错的年轻球员机会,说了一句:
年轻的时候我们也很荒诞噻。
如果岁月可转头,开火锅店的老板们还会对这些年轻墨客再说一句:
一大早跑来吃鸭儿的火锅啊?
不是每个墨客都理解一些朋友们的做法。
美学的争端之外,将海子卷入的还有气功潮。这曾经是和改革新星李向南、海灯以至qian xuesen的掌握论一同盛行的时尚,最著名的文学界卷入者包括柯云路,海子是不声不响的身体力行者。亲历者回顾,发功者第一次来到昌平,当场震倒政法大学的几个学生,带给海子和其他不雅观者震荡。这个反对异化的时期,相信人可以提升自己的身体,将肉身变为超越的“气”,开天眼,乃至散发芳香。海子自傲他已经打通了“小周天”,冬天可以穿一件单衣走在昌平校园里,双脚泡着冷水写作。
在交情后面,圈子也正在形成。朦胧诗一代的“幸存者俱乐部”,对付海子、西川这样的“第三代”既吸纳又拒斥,后来者加入须要超越苛刻的身份验证;在四川的“非非主义”和北大的“学院派”之间,也存在奇妙的话语权不合。
在1986年的诗歌大展中,上海的“撒娇派”坦承:“光愤怒弗成,想超脱又舍不得天下。我们就撒娇。”
那时候的成都文青,对很多诗都非常熟习。比如“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地处青海湖以西的德令哈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1988年的海子在这里的夜晚“不关心人类”,只惦记远在拉萨的“姐姐”,一个通信多时的诗友。姐姐终极谢绝了求爱的海子。但德令哈抒怀的温顺却保留了下来,代替了它在历史中的荒凉面孔。
1980年代的爱情,是诗歌的孪生物,其间却又含有禁忌。野夫在《1980年代的爱情》中的描述得到了小明的称许。男女主人公在久别相逢后,一夜面对炉火说不出话,“那时候爱情便是这样的”。
本日诸多1980年代怀旧者的现状,他们已经在一场自我补偿后两手空空,无从赎回自己的青春友爱。
三
追王朔到郫县
《诗意的年代》是80年代作家第一次,也是末了一次在银幕里集体出场。
拍摄场景居然在郫县,成都文青们其实追了一把。
这部电影很神奇。
听说2000年在紫禁城影业放映厅内,导演吕乐手指着银幕,划来划去,一直给几个台长说:
这是阿城,这是王朔,这是方方,这是余华……
吕乐把新拍的电影,送到紫禁城影业审核。看片会上,他担心几个电视台台长,不认识画面里的作家。谁出场,他就指着谁报名字。
电影放完后,几个台长坐那儿,净吸烟,不说话。吕乐刚想问他们的见地,边上一个电影发行策划人,溘然绷不住,冲他大声训道:
这什么玩意!
就这个能往电影院放吗?
吕乐一下子懵了,怎么作家演的电影就不能放了?
这部电影,叫《诗意的年代》,里面一贯在谈“诗意”。但参演的没一个墨客。除了两个演员,其他全是作家。
开拍前,吕乐和制片人从一家空调公司,找来150万预算。然后把80年代红极一时的作家,挨个请了遍。终极出镜的南北作家,多达12位。
北方作家有,阿城、王朔、赵玫、丁天、马原。
南方作家有,余华、林白、陈村落、徐星、须兰、棉棉、方方。
这个阵容,相称于搬来了全体当代作家的半壁江山。至今,这都是出场作家最多的一部电影。
实在和墨客比较,这个电影已经很严明了。当年墨客们南北大战,是饮酒。
电影的拍摄地点,在郫县。王朔来时先坐飞机,抵达成都。那时候他人红是非多,刚下飞机就被围追堵截,从成都一起追到郫县。
拍摄前,王朔要喝点酒。等满脸涨红,坐在摄像机前,边抠牙,边大谈什么是诗意。会场时时有个俊秀姑娘入画,替他们续开水,倒烟灰。等电影都快拍完了,他才知道那才是女主角。
电影出来后,王朔创造自己声音被掐了不少。每到“他妈的”地方,就被删了。
只管如此,这部电影仍旧没有过审,连张盗版碟都没有。直到2007年,吕乐拿着它去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才得以重新面世。
参演的作家们得知后,激动得说:我得买一张放放,怎么也算我做了回演员。
现在我们转头看,《诗意的年代》是80年代作家第一次,也是末了一次在银幕里集体出场。而银幕之外,这也是他们末了一次,在时期里集体登场。
电影《诗意的年代》出演的作家
成都的墨客仍旧在打仗电影。
比如贾樟柯的24城,编剧就有翟永明——她的白夜酒吧,燕徙两次还是成都墨客的盘桓之所。
就像万夏一样,翟永明当然也不可能不把稳到城市的更新。
这种更新还不仅仅是一颗树、一条街、一个立交桥的变革。
即便在诗里,沧桑感也是剧烈的。
好了
本日是天下不读书日
致敬
我们所来的方向
1980
资料来源:
1.牛皮明明,当你们评论辩论方方的时候,我看的却是80年代作家去哪了
2.万夏,成都墨客
3.肖全,【我们这一代】我的朋友北岛
4.袁凌,海子:去世于一场春天的雷暴 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