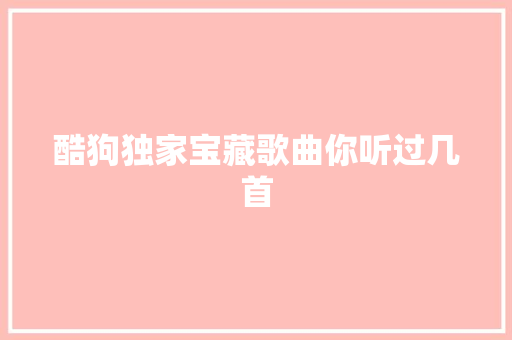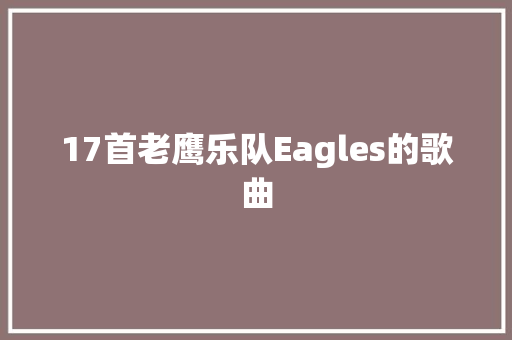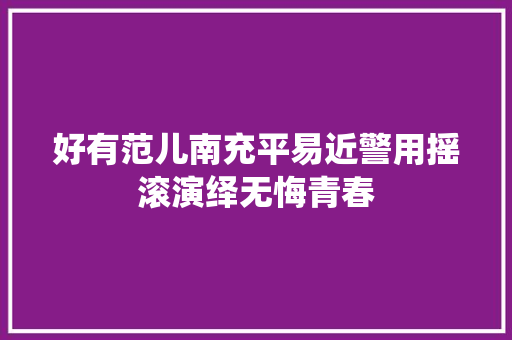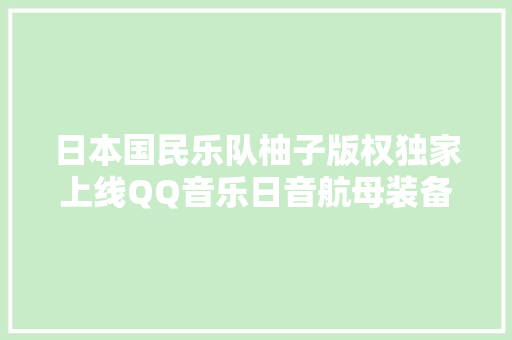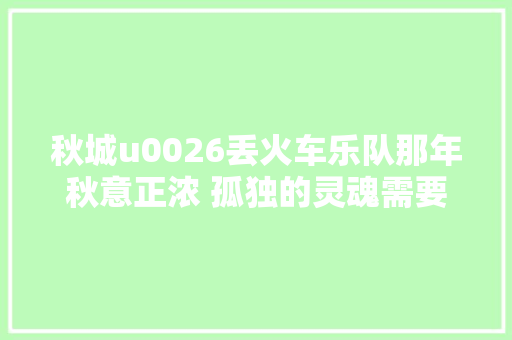法国墨客洛特雷阿蒙曾写过一句诗:“一把雨伞和缝纫机在手术台上相遇也是美,由于那是我的一个梦。”而当马东把摇滚乐和综艺捣鼓到一起时,它们的相遇是否是美的,则一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作为综艺节目,这一结合本身的噱头所引起的流量,对投资方而言,一定是“美”的;但与此同时,当它打着“复兴摇滚”、要“带来中国摇滚乐的另一个夏天”这类标语时,人们一定也就会对它的所作所为以及其所能达到的程度保持集中关注,质疑和批评之声也随之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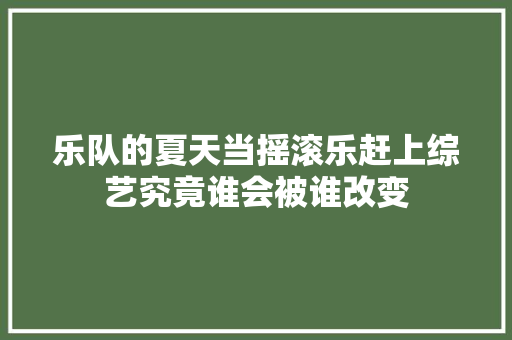
《乐队的夏天》节目截图
而在这许多质疑声中,有一些迷惑或许是最根本的,即摇滚乐和当下中国风起云涌的综艺节目会搭吗?所谓“复兴”或是表现摇滚乐的精神及其个性,综艺这样的节目形式是否能够较为完美地承担这一任务?在这一系列疑问的背后,实在有一个十分根本且旧调重弹的问题,即摇滚乐这一音乐中的“异类”,在当下中国它要往哪走?
作为“异类”的摇滚乐
摇滚乐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出身时,就已经注定了它在音乐天下中的异类形象。
首先它兼容并包,在其三大来源——节奏布鲁斯、叮坪巷音乐(Tin Pan Alley)和pop(叮坪巷音乐的改编和延续)——中,对付当时主流白人和边缘黑人的音乐都有接管,并且通过改造而逐渐形成了以灵巧大胆、富有激情与节奏著称的音乐形式,直白且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愤懑、迷惘、痛楚、快乐、激动与背叛。再者,在摇滚乐迅速发展及爆发的六七十年代,对付欧美诸国而言,正是社会、政治与经济、文化都处于激烈转变中的阶段,而推动这一转变的正是广大躁动、富有空想且充满了反抗精神的年轻人。摇滚乐与这一广阔的变革同声相应,从而成为年轻人最喜好与最常利用的表达载体和手段。
摇滚乐自身所具有的个性是有限的,但当它与六七十年代西方青年运动中的意识形态相领悟,其独具特色的精神便逐渐被塑造而成,并在其后的八九十年代得到更进一步地巩固与发扬光大。我们本日提到摇滚乐,人们脑海中大概都会有一些十分相似的印象——每每是激情澎湃的、个性的、躁动的且具有强烈颠覆性的,这一颠覆既可能表现在音乐形式上(英国摇滚乐队皇后(Queen)的一首《波西米亚狂想曲》领悟了诸多传统与当代的音乐形式),也可能表现在他们通过音乐、动作和形象来表达对付某些社会政治文化、日常生活以及诸种意识形态的意见,而个中又常常会以批驳的形式涌现。虽然并非所有摇滚乐和摇滚乐队都如此,但它却是所有摇滚乐最基本的底色,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当摇滚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发展起来,它的个性与精神也一并被继续着。一样平常认为,1986年崔健以一首《空空如也》喊出了中国摇滚第一声,三年后,崔健发行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与此同时,在80年代后期,中国的摇滚乐队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纭成立,唐朝、黑豹、零点、眼镜蛇以及这次参加《乐队的夏天》的面孔乐队。
作为中国第一代摇滚乐队,他们一方面继续了西方七八十年代摇滚乐的个性与精神,另一方面诸多十分相似的时期与社会背景,也让这些中国年轻人借助摇滚乐表达着他们的情绪、心境以及对付现实生活的迷惘、不满与抗争。终极在90年代匆匆成了高晓松在《乐队的夏天》中反复提及的,摇滚乐的“黄金时期”。
对付公共议题的关注,是摇滚乐一个十分主要的面向。或者我们可以说,由于摇滚乐自身自由、无拘无束、独立和出格的特性,导致它时常要去对抗那些企图剥夺或是限定这些特质的力量,摇滚与主流和日常生活循规蹈矩的冲突也频繁发生。因此,许多摇滚乐队积极参与对强权的批驳和抵抗;另一方面,它们也必须时时当心主流意识形态对其异类身份形象的污名与打压。而由于音乐这一艺术形式本身就具有传达见地的能力,我们能看到许多摇滚歌曲都带有强烈的意向性,即对付某些特定事宜或某种不雅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批驳,乃至直指强权。
六七十年代为了抗议美国政府发动越南战役,披头士乐队的约翰·列侬曾以当时著名的口号“要做爱,不要战役”(Makelove,not war)为号召,创作了歌曲Mind Games,雷鬼教父鲍勃·马利也以此写了一首叫No more Trouble讽刺美国政府的霸道;成立于七十年代的英国著名朋克乐队性手枪(The Sex Pistols),对付英国政府和君主制的批评也十分强势;创立于2011年的俄罗斯女子朋克摇滚乐队Pussy Riot,则锋芒直指普京集团,并由于她们的激进性而遭到政府起诉……
反抗——无论摇滚告成长到哪一阶段,或传播到哪个国家——都依旧是其最主要的个性和精神之一。
从公共转向私人,
摇滚的变革不止在综艺中
当然,背叛也并非是丰富繁芜的摇滚乐的所有面向。在《乐队的夏天》中,我们便能看到摇滚乐的其余诸多个性与形象,如成立于1998年的台湾乐队旺福,他们便发挥了摇滚乐队的另一壁向,通过轻松愉悦的歌曲来传达许多看似稀松平常却实则深刻的人生感悟。个中两支老牌乐队,如面孔(成立于1989年)和痛仰(成立于1999年),则带着强烈的独属乐队的个性。痛仰的标志截取自经典动画片《哪吒闹海》中哪吒自刎“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的形象,而这一形象本身也就展现了他们所具有的叛逆性。
痛仰乐队的logo
在《乐队的夏天》中的31支乐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摇滚乐史的一个小缩影,从80年代的第一代到成立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几支90后组成的乐队,个中的继续与变革都十分明显,紧张表现在对付公共问题关注的减少与缺失落。创作方向逐渐开始转向对付个体情绪、内心与履历的诉说,而对公共生活和边缘群体等社会议题避而不谈。越来越后期的乐队,他们对付公共性所表露出的兴趣也常常越来越低。
面孔乐队在《乐队的夏天》
面孔乐队的《梦》中,歌的内容看似只是一个白日梦,但却十分生动地反响出了90年代中国社会或是个中许多人的某些状态——在积极变革之下的惶恐、不安、迷惘和某种渴望。而痛仰的《再见杰克》所致敬的则是那一代年轻人共同的偶像,美国垮掉派作家杰克·凯鲁亚克。与痛仰成立于同期的新裤子,所演出的歌关于disco文化,同样反响出了那个期间潮流的动向……比较之下,后来的诸多乐队——个中又以一些年轻的乐队而言,他们作品中越来越少看到此类东西,而转向了个体、过去和私人情绪等等。
涌现这一转变,一方面与摇滚乐自身的变革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全体社会政治环境的转变使得它也随之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这里并不存在乐队道德上的高低之分,它与其他诸如文学或艺术的转变是相似的,伴随着19世纪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衰落,对个体内部——心灵、情绪和履历——地关注便逐渐开始成为主流。在文学中,雨果、福楼拜和巴尔扎克式的社会与历史全景式的描写和关注逊位,取而代之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普鲁斯特所开启的对付个体内心的挖掘;而在艺术中,叙事性绘画被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所取代,当代人的内心的激情亲切和扭曲在梵高和蒙克的画中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与这一转变相似,年轻乐队开始关注他们当下的生活,关注自我和内部的情绪,对付外部和公共领域中的议题呈现出普遍的——这一普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社会与文化中的方方面面——冷淡。也正是在这里,摇滚乐的边缘和异类状况再次被凸显,对付那些依旧一如既往的老牌乐队,他们在《乐队的夏天》中被批评扞格难入且不大适应个中的比赛氛围;但对付那些唱着吃吃喝喝、小情小调的年轻乐队,则又遭到是否还具有摇滚精神的质疑。对付文学和艺术而言,这一转变并无好坏之别;但对摇滚乐而言,它的这一转变却极有可能会侵害它所具有的核心精神与个性。
就如高晓松所说的,摇滚的黄金时期已经由去,无论对付东、西方而言,伴随着电视媒体与互联网的兴盛,以及消费主义的来势汹汹,20世纪后半段曾让摇滚“燥起来”的环境已经彻底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盛行乐,是关注娱乐的综艺。
是摇滚改变娱乐,
还是娱乐收编摇滚?
马东是一个综艺神经敏感且颇有想法之人。在《奇葩说》中,他通过各种包装与创意把辩论变成了一个娱乐节目,与此同时还能通过其所辩论的话题来谈论一些当下人们关心和关注的议题,个中不乏对付公共领域与边缘话题的谈论。一些不雅观众乃至认为他是某种当下知识分子的“新形象”,另一方面,他又被批评者称为“文化贩子”。但无论如何,不管《奇葩说》还是《乐队的夏天》,在某种程度上都大概做到了它所希望能完成的那个目标。一方面带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无论是对某个问题的谈论或是希望推介摇滚乐;另一方面则也照顾到了成本和利润,也便是尼尔·波兹曼在其《娱乐至去世》中所指出的,统统公共话语如今都以娱乐的办法涌现。在很大程度上,这便是当代社会最光鲜的一个特点,即统统都被笼罩在成本和消费大潮中,因此当你借助这一形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一个主要的问题便是:它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前者的汹汹气势。
在《乐队的夏天》中的31支乐队,许多老牌乐队早已名声在外,一些年轻乐队也在摇滚乐圈子里有了一定的有名度。但无论如何,对付更广大的音乐不雅观众而言,他们都属于小众。就像张亚东在节目中所指出的,由于音乐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导致原来就异类的摇滚乐在中国的音乐市场中变得更加边缘。新生代乐队的演出园地大都是酒吧或一些小型乐迷会,著名的摇滚乐队也大都只在各种音乐会或是演唱会上进行演出。像《乐队的夏天》这样的舞台,对个中许多乐队而言都是第一次。而对付综艺节目的不雅观众,个中的大部分乐队或许更是所知者甚少。
《乐队的夏天》节目截图。
海内综艺节目的勃兴,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早期的日韩以及其后的中国台湾综艺节目 的带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欧美综艺节目形式也被复制,形成了最近几年大火的综艺热潮。综艺节目的一个主要功能便是其所具有的娱乐性,通过各种演出与丰富形式给不雅观众带来诙谐与欢快。我们或容许以说,当代综艺节目是范例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娱乐和利润是作为最紧张的核心,常常使得原来具有理性和逻辑性的公共议题谈论,变得分开语境、肤浅和碎片化,从而削弱乃至淹没了议题本身。
由于综艺自身的特色,使得它一定是普通、易懂且大众化的,因此当强调自我、个性和异类的摇滚乐碰上综艺,一种险些是天生的不折衷便会涌现。
在《乐队的夏天》中,这一点在马东和诸多摇滚乐手之间的对话和互动中表露得十分光鲜。一些摇滚乐手对马东综艺式的谈天和问题颇为尴尬,或是很难形成有效的互换。就如高晓松所说的,在马东和摇滚乐手之间存在着互换鸿沟,它一方面由于性情造成,但更紧张的缘故原由还是在于,综艺模式对摇滚乐手来说是种陌生的模式,娱乐性或许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传统上对付娱乐圈的哀求和规训中,他们每每被塑造或希望成为某种艺术家,但综艺须要的是“艺人”:懂得如何去娱乐、逗笑不雅观众以及带动流量。摇滚乐自身的精神使然,也让《乐队的夏天》的制作群和不雅观众,反复涌现了对付个性的哀求和期待,无论是对乐队的乐手还是他们的作品与性情。就如乐队所说的,个性是一个摇滚乐队的灵魂;张亚东说“乐队便是要有不同的态度”,高晓松则指出摇滚乐一个主要特色便是“不合营,不搭理”,而这些与综艺的哀求截然相反。
在面孔和痛仰1V1的比赛中,他们的得分普遍都低,评委指出这些摇滚乐队没有把比赛这事放在心上,意思是说他们该当考虑以不雅观众的喜好来调度和改变自己的演出,以此得到由100名80、90后所组成的乐迷投票。而许多乐队对付比赛名次之事,也都没有太放在心上,而是希望能只管即便展现自己乐队的个性和特色。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冲突,即综艺作为一个以不雅观众为主体的娱乐节目,就一定哀求个中的演出者能够尽最大可能的投其所好,而这一哀求又会与成本的哀求合流,从而形成类型和套路。但摇滚乐正好是反类型和反套路的,因此让他们贴合不雅观众的喜好来进行调度,很大程度上也就抽掉了这些摇滚乐队最核心的灵魂。
《马克思与<成本论>》作者: [英] 大卫·哈维 ,译者: 周大昕,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5月
而颇为吊诡的一点是,综艺和盛行都以大众化为目的,它们强势的复制和再生产能力终极会霸占全体市场份额中的紧张部分,而把其他类型挤到边缘。比较较于当下形形色色的综艺节目和盛行音乐,摇滚乐是处在边缘的那个。如今,综艺节目对后者伸出橄榄枝,与其说是希望分一杯羹给它,毋宁说是消费主义逻辑创造了边缘类型的潜在商业代价,而希望对其进行挖掘与开采,从而把它纳入自己的利润生产环节中,这便是大卫·哈维在《马克思与<成本论>》中所指出的,随着成本主义经济模式进一步扩大(尤其在当下环球成本主义的框架下),曾经那些被排斥在成本主义经济生产循环之外的许多领域也开始为其影响和主宰,从而变成成本累积和再生产中的一部分。在这个中,无论是像哈维在书中作为例子谈论的家庭劳动,还是诸如在音乐场域中的边缘类型,都从曾经的被排斥走向如今的被同化,而彻底失落去了对抗或是毁坏成本主义经济逻辑的能力。《乐队的夏天》之以是如此火,个中一个主要缘故原由便与此点有关,即曾经为主流音乐消费市场忽略的摇滚乐如今“受到关注”,进入综艺这一电视娱乐形式中,成为促进消费和成本累积的主要一环,所谓“异类同样(或许更加)能创造收视率”。
如果说,强权是摇滚乐面对的第一个巨人对手,那么娱乐与消费的逻辑完备与政治和权力不同,在它们背后还站在成本这一强势且诱人的力量。这或许是摇滚乐所面对的第二个巨人对手——即随着商业、娱乐和消费主义不雅观念的进一步扩散,在这种态势之下,摇滚乐终极是否还能坚持其在半个多世纪中所摸索和建构出的精神与特色?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有摇滚乐把矛头指向成本主义,指向娱乐至去世的消费主义以及终极它们所可能导致的同质化问题。在《乐队的夏天》中,90后盘尼西林乐队收成许多好评,对其的夸奖首先是他们踏实的演出和创意,然后是个性与态度,并且他们与其他同龄人的摇滚乐队颇为不同。个性与态度都带“刺”,且很多时候并非那么浅白,当它们遇上那些看似没有任何限定,实则处处规范与禁止的综艺时,是否还能够表达?或者能够表达多少,始终是个问题。
魔岩三杰,左起依次为张楚、何勇、窦唯。
高晓松说,非常高兴像面孔和痛仰这样的老牌乐队乐意来参加《乐队的夏天》,倒不是为了复兴中国摇滚,而是想向年轻一代的不雅观众展示下中国曾经也有过这么精彩的摇滚乐队,并且曾有一个黄金时期。如果对中国摇滚稍有理解的人实在都会知道那些大名鼎鼎的乐队和歌手(如“魔岩三杰”),但他们的有名度每每很难达到一个盛行歌手的程度。这本身是正常且无可厚非的,但问题就如张亚东所指出的,随着人们对音乐理解的越来越有限且狭隘,原来就处于边缘的摇滚乐的处境也便会变得更加糟糕。在这背后,既有成本和娱乐的手在操纵着,也有社会的力量在无休止地规训着它,因此问题本身实在更为繁芜,而非仅仅只是摇滚乐。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摇滚乐登上《乐队的夏天》也并非百害而无一利,它至少给了这些新老乐队一个舞台,向不雅观众展现他们的作品和精神。如果由此能引起人们对付摇滚乐的关注,则同样是件喜事。但无论如何,对付摇滚乐迷而言,喜好摇滚乐险些都有着十分相似的心情与渴望,即对付个中个性的迷恋、对付自由和独立的神往,对付墨守成规、各种“正常”与偶像的揶揄与攻击、对付公共问题的关注、对付强权的批驳以及那股躁动的精神。在面孔和痛仰的演出中,他们身上的那股劲,那股傲气与不合营,便是摇滚之所以为摇滚的一个主要特点。而综艺彷佛很难实现这一点,很多时候它乃至有些反感这些品质。
摇滚乐常常成为一根刺,引人讨厌,敬而远之;综艺则大都温和平顺,轻松诙谐地希望谄媚所有人。当它们在《乐队的夏天》中相遇,彼此彷佛都在摸索和熟习着对方的办法,无论是节目后期开始让摇滚乐改编盛行歌曲,还是摇滚乐手绝不买马东综艺的一套,都表现出了二者在这一场域中的角力。中国摇滚乐终极是否能利用综艺的力量,使自身得到更广泛的关注而又不会为其收编或妥协?
在我看来,要做到这一点彷佛很难,既由于中国当下摇滚乐的力量完备无法与综艺反抗,更不必说当它面对雄厚的成本和消费大潮时,其本身所具有的消费性便会自然而然地把它们引往大众化方向;并且在中国的综艺节目中,摇滚乐时常难以真正地表达自身的公共不雅观点。因此,它处在权力、成本、消费和娱乐这些繁芜的场域之间,饱受各类束缚、重重限定,终极导致它难以发出自己的真实声音。对付这一点,一个综艺节目或许很难有所改变。
作者:重木 编辑:徐伟、张婷
校正: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