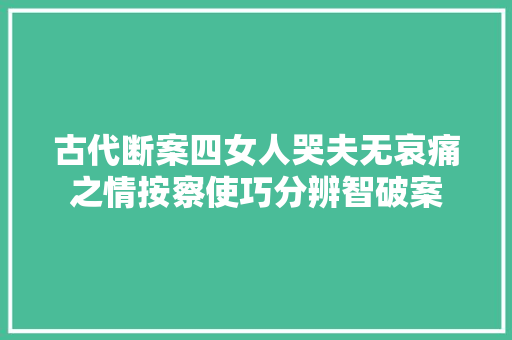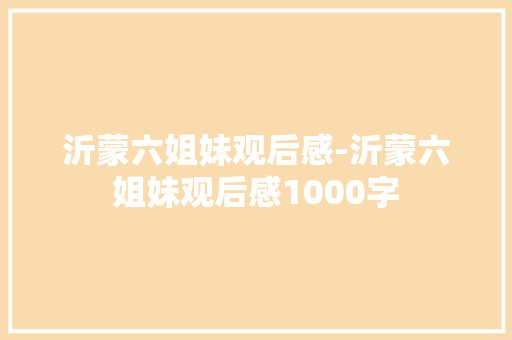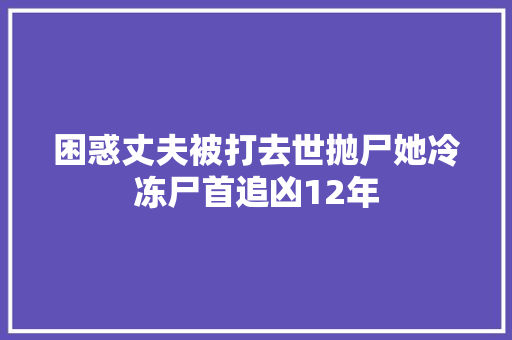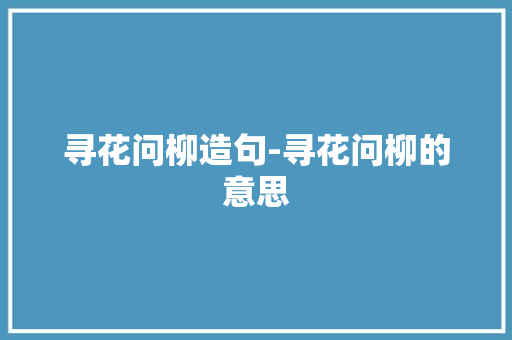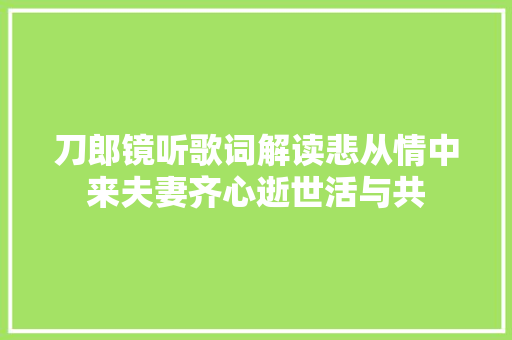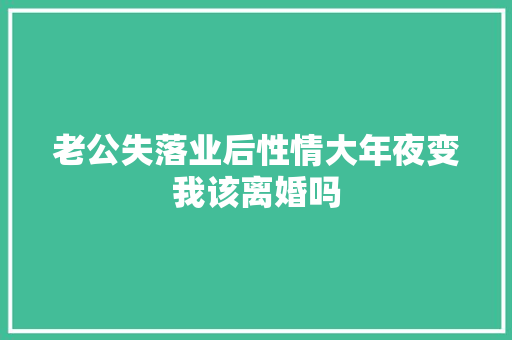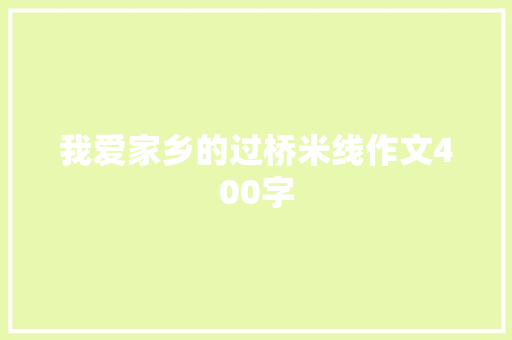《依兰爱情故事》之于《你好,李焕英》,就犹如《直到天下尽头》或《好想大声说爱你》之于《灌篮高手》——只管内容上关联不大,但能让不雅观众在剧情与旋律之间建构起情绪上的奇妙遐想。当你听到《好想大声说爱你》的前奏,你的运动希望很随意马虎被引发出来;当你听到《直到天下的尽头》,很自然地会为三井的境遇唏嘘不已。同样地,当《依兰爱情故事》的旋律响起,你很随意马虎想起贾玲和她妈妈的动听故事。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依兰爱情故事》讲了一个和《你好,李焕英》完备不同的故事。歌里的剧情大家也都猜得七七八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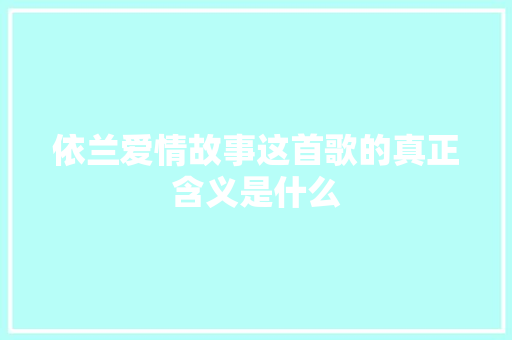
1.男孩样貌平平,看好了一位很俊秀的女孩子,想追求她。(“美女儿啊 屌丝儿啊 他整不到一块堆儿啊”)
2.好在男孩很会说话,加上各种去世缠烂打,成功把女孩追得手,两人顺利成婚。(“咱俩破个闷儿啊”;“你一笑啊 我刺挠啊浑身都得劲儿啊 你一哭啊 我胆儿突啊 就掐我消消气儿吧”)
3.一开始两口子还过了一段挺甜蜜的日子,并生了个女儿。(“媳妇儿啊 进门儿啊 咱俩过日子儿啊 我有情 你故意 生了个胖闺女儿啊”)
4.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妻子每天出去打麻将,丈夫每天在家里干家务、照顾女儿。(“鸡毛啊 蒜皮儿啊 那都是我的事儿啊 你搂宝儿啊 座屉儿啊 每天呐都有局儿啊”)
5.随后,妻子出轨,并以丈夫“没出息”为由离开家庭。(“谁家的 爷们儿啊 藏进下屋碗架柜儿啊 你红啦 我绿儿啊 还骂我没出息儿啊”)
6.两人离婚后(可能没有办离婚手续),丈夫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任务。之以是“我活着是你的人儿……看你睡啦,我心里美滋味儿”会重复,不是由于丈夫在被戴绿帽后还想着妻子,是丈夫把曾经对妻子的感情投入到“上辈子小情人”身上,父女二人从此相依为命。
问题在于故事的后半段,丈夫每天在家里干家务、妻子每天出去打麻将,两人不事情么?妻子为什么会溘然离开家?真的是由于“美女屌丝过不到一块堆儿”么?结合词曲作者方磊的东北小镇出身,同时考虑到小说、电影都将背景设定在国企时期,我们大概可以还原出一些歌词之外的剧情,虽然会偏离词曲作者的原意。
上述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东北下岗潮中找到一些答案。国企改制、大下岗给东北职工家庭带来的冲击不用多说,下岗潮同时也是离婚潮。
歌词里的两个人一开始日子还能过,是由于还没下岗,事情有保障。之以是外面条件差距大、却还能过到一起,是由于男方是正式国营工人,在八十年代的婚恋市场里也算抢手,只管没上过大学、也不是干部。可能考过大学,但落榜后还是回工厂接父母的班了,由于在八十年代,上了大学顶多回来当干部,而坐办公室的干部的社会地位在当时并不比流水线工人高多少,而且高考落榜的“大学漏”在工人军队里也很稀缺(刘庆邦小说《红煤》里的男主也是如此)。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便是两人虽没考过大学,但考上技校了,走了读技校-进工厂认大工匠当师傅-正式上岗的路线,很多学徒和师傅成为生平的朋友。在国企时期,技校的录取难度、流程、社会荣誉与作为“预备干部培训中央”的大学并无二致。进入九十年代,尤其是大下岗往后,技校成为杀马特、打群架的代名词。
好日子不才岗之后结束了。上面一纸令下,不好意思,你们要“从头再来”了。两口子的“再就业”之路并不顺利。买断工龄的钱可能要攒着留给孩子上学用,可能投钱做了买卖,赔了。当然,也有可能把钱都砸进传销组织里打水漂儿了。传销组织、邪教、黑社会一度成为东北的代名词,是由于国企以及与国企高度绑定的各种基层组织从基层管理中退出或“家当化”了。所谓“权力厌恶真空”,你不补充,处在同一“生态位”的别的组织就要去补充了。
丈夫每天在家里干家务,实在是没什么正经事情干。《钢的琴》反响了部分东北的现实,里面的男主角能花那么多韶光和精力去做一架钢琴,也解释他也没什么正经的班儿去上。“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由于那些能雇人的老板,有的在以前单位里混得很差的、早早退出系统编制去经商,有的乃至是劳改犯、没有单位吸收、不得不做生意,这类人是不会被下岗工人们看得上的。还有一些老板虽然也是过去单位里混得不错的,但属于单位里跑供销的,这些人在国企时期就很善于和人打交道,他们常日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所不齿。可以看出下岗工人们骨子里有那么一股子傲气,除了看不起当官的、看不起有钱人,还认同“买不如造”,能用钱买的东西我偏要用手做出来,就像《钢的琴》里的父亲非要做出一架钢琴出来。实在没钱买。
不过丈夫好歹还能顾着家里,许多同龄的工友就不那么会过日子了。他们没事儿饮酒,喝完就回家耍酒疯。丈夫打老婆打得狠,老婆骂人骂更狠,丈夫打得更更狠……把老婆孩子都打跑了,然后连续饮酒,肝硬化、肝腹水让好几个工友都没活过五十岁。这些病实在不难治,为什么治不好?买断工龄的钱在九十年代的物价水平看来还是很可不雅观的,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病贵了起来,做手术还要给红包,一场大病可以让那些钱瞬间打水漂。九十年代末医患抵牾开始频发,或有家属扛着女人和婴儿的尸体在妇产科门前静坐,或有家属拿着一把剪刀去找外科大夫理论——并不是拿刀威胁,而是这把形状有些奇怪的剪刀是从刚火化完的骨灰里创造的。那时的媒体并不站在年夜夫这边,这与本日截然不同。
说回妻子这边。离开的妻子值得训斥吗?当然不是,由于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你可以不给我买新衣服、买我喜好的围巾,但老人生病了你也拿不出钱吗?物价不断上涨,但家里哪哪都须要用钱。在表面碰着别的男人,很有可能是更有钱、也更乐意花心思去赢利的人。这个男的也属于前面提到的国营工人“看不上”的人,通过“看不上”的办法在市场化浪潮中赚了第一桶金,有了自己的小公司,在牌局上认识了曾经大家追求的厂花,从此组建新的家庭。
再醮往后,妻子的日子好过了很多,但并没有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而是进入到第二任丈夫的公司里,没日没夜地打理大小业务。她不会不管女儿,会定期给女儿打学费生活费(前夫依然赚不到什么钱)。她还有一堆找不到活儿干的亲戚也都投奔而来,在丈夫的公司里担当各种职务。(至于这家公司在改开四十年大潮中的沉浮,这个“暗黑版”李焕英离开家庭后的经历,可能更加传奇,但这便是另一个故事了……)
总之,《你好,李焕英》是部好电影,它还原了部分历史事实(马督工乃至说这是“国企大院记录片”),但也只是“部分”。胜利化工厂末了还在么?为什么厂长一家(沈光林、王琴夫妇)过得比其他人都好?沈光林的女儿去美国读大学一定用度不菲,钱是哪儿来的?比较之下,《依兰爱情故事》里那些与《你好,李焕英》相冲突、被掩蔽的剧情,彷佛也没那么主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