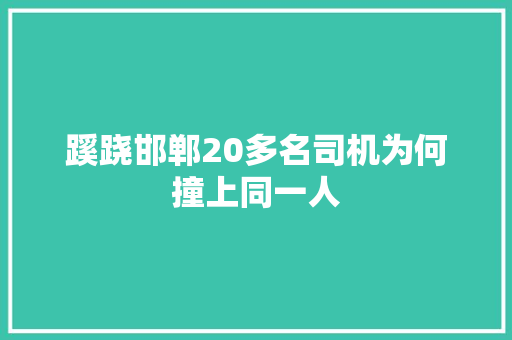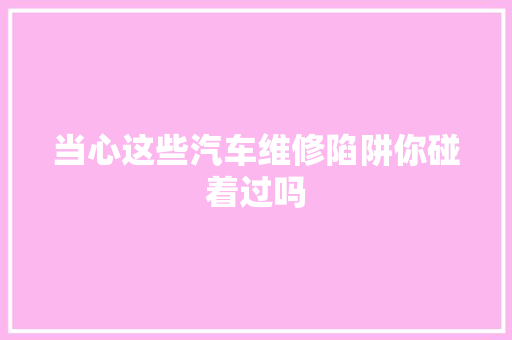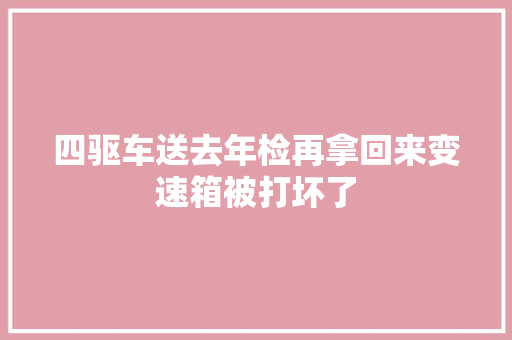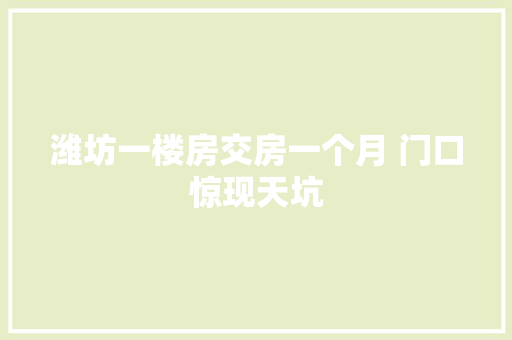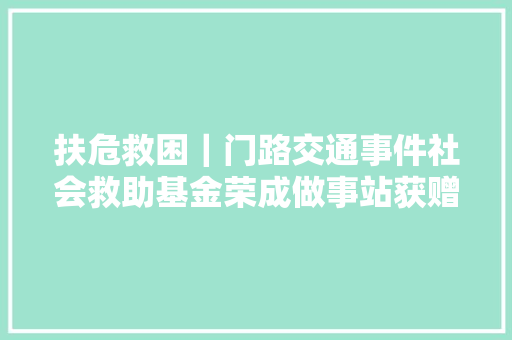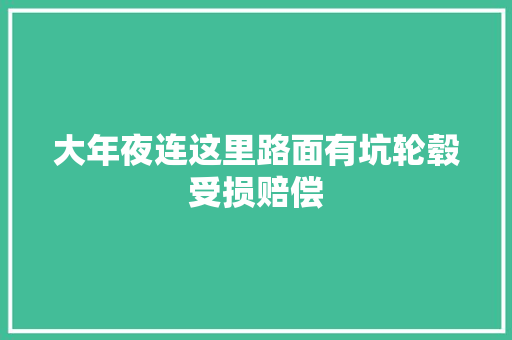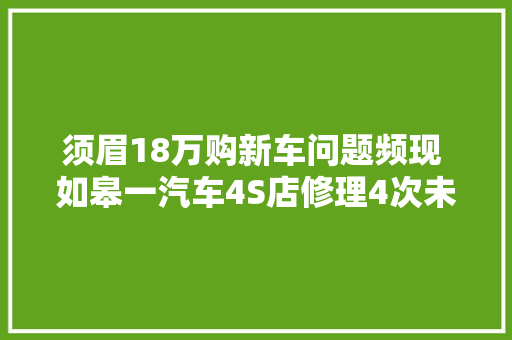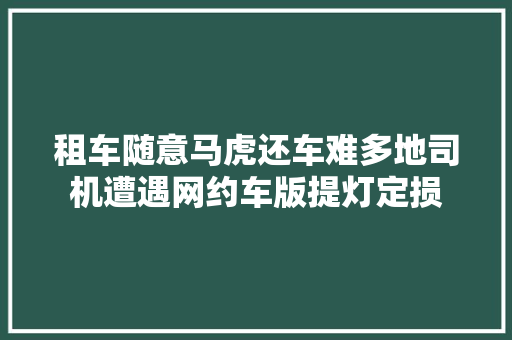由左至右:姜昆、赵炎、马季
从艺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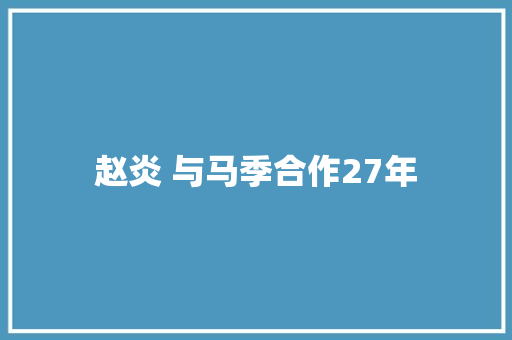
紧贴时期脉搏
11月30日晚上,中国广播艺术团将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举办“相声名家赵炎从艺50周年庆典晚会”,姜昆、冯巩、刘伟等师兄弟,赵炎的弟子、再传弟子以及文艺界名家将奉献上一台精彩的节目。与其说这是一场晚会,不如说是展示赵炎50年艺术人生的精彩乐章。
50年从艺生涯,赵炎秉承着“相声的笑不应是浅薄的风趣,而应追求高雅的诙谐形式”的信念,陈说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以洒脱稳健的台风,洪亮圆润的嗓音,把每段作品演绎得惟妙惟肖,受到不雅观众的喜好,更得到师父马季师长西席的看重。
我与赵炎的第一次见面是1986年,宝坻影剧院落成,马季师长西席带着赵炎,组团来故乡助兴演出,合说相声《吹牛》,现场效果十分火爆。2007年,赵炎第二次来宝坻,在纪念马季师长西席从艺50年《笑在家乡》文艺晚会上,他与周炜、孙晨合说相声《伯仲无情》,这段相声把马季师长西席的《五官争功》又推进了一步。
我曾到央视影视之家采访赵炎,请他回顾与马季师长西席的点点滴滴。他始终面带笑颜,以一句一顿的语速,清晰悦耳的音色,超强的影象力,电脑一样平常严密的逻辑思维,向我讲述了他与马季师长西席鲜为人知的故事。
2011年3月,我的书《马季生前与身后》出版后,在北京举行发布会,有幸请到赵炎主持,让我再次感想熏染到他的才华。他不假思虑,出口成章:“马季师长西席的家乡有一位有心者,利用业余韶光,冲动于马季师长西席的艺术魅力与人格魅力,采访了几十位乃至上百位当事人,拍了几百幅照片,编著成这么一本书。他是想以此记录马季师长西席的出生、家事、公事、艺事、趣事,当然也记录了马季师长西席的后事,他用这本书表达了家乡人对这位艺术家的热爱。”
特殊是马季艺术研究会成立后,我与赵炎的打仗日渐增多,也就越来越深地体会到他身上所具有的名贵品质。在他方面大耳、仪表堂堂的样子容貌背后,是稳健中带有睿智,诙谐中带着机警是思维意识,与他的师父马季师长西席一样,一贯紧贴着时期的脉搏,饱含着满满的正能量。
生于北京工人家庭
在兵团与相声结缘
赵炎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小时候家住棉花胡同,父亲是摩托车制造厂代销员,爱好书法,也喜好吹口琴,母亲是工人,爱听京剧,放工后总是打开收音机听戏,或带着赵炎到戏院看戏。赵炎天资聪颖,长于模拟,听戏回来,亮开嗓子学上几句,还真有那么一点儿味道。
赵炎的文艺特长在幼儿园时便崭露锋芒,上小学时他的文化课科科满分,当上了中队长,卖力画黑板报,学校组织文艺活动,朗诵时他是领诵,合唱时他是领唱。他就读的北京府学胡同小学很有名气,原是文丞相祠,文天祥蒙难时曾囚禁、就义于此,随处颂扬的《正气歌》便是在这里写成的。传说文天祥收复山河的决心冲动了树木,这里每一株树都是朝南成长。这些小故事,潜移默化影响了赵炎。
赵炎还喜好运动,跳水、单杠、双杆、空翻、体操都能玩儿,爱踢足球,喜好自行车车技,在学校里特殊出名。什刹海体校、八一少年体操队都上门要录取他,但妈妈不让,她希望赵炎上大学。没想到初中还没毕业,17岁时,赵炎就去了黑龙江生产培植兵团插队。
受父亲的职业影响,赵炎喜好摩托车,到了兵团,他对“铁牛”产生了兴趣,成为拖沓机手,驾驶“康麦因”拖沓机奔驰在广袤的野外上,志在乾坤,伸展肚量胸襟,眼里是金色的麦浪,空气中飘荡着豆海的芬芳,他陶醉于此,以深翻黑土,多收粮食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繁重的体力劳动掩饰笼罩不住他的文艺特长,团宣扬科要调他到文艺宣扬队,师傅舍不得他走,他对师傅表态:“您放心吧,我不去宣扬队,只想开着‘铁牛’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
但是团政治部主任动了心思,下去私访,要稽核赵炎。说来也巧,半路恰好碰上赵炎,赵炎给自己说了不少坏话:“这人平时表现不怎么样,他去宣扬队不得当,您还是让得当的人去吧!
”政治部主任不去世心,非要见见这个人。结果赵炎一进门就露馅了,“原来便是你,还敢乱来我,跟我报到去!
”赵炎一脸尴尬,只好服从组织安排。
丢下心爱的“铁牛”,赵炎找回了儿时的自我。刚到文艺宣扬队,团里正在为谁来扮演《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发愁。赵炎亮开嗓子就唱:“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它,里里外外一把手,穷汉的孩子早当家……”嗓音高亢洪亮,神态淡定自若,这身体、这扮相,征服了在场所有的人,导演大喜过望,当场拍板:“李玉和非他莫属!
”
《红灯记》一炮打响,接着团里排《智取威虎山》,赵炎演花脸李勇奇,这个角色更对他的路子,把小时候学的裘盛戎的味道用上了,惊艳全场。团里一鼓作气又排《沙家浜》,赵炎演男一号郭建光,这戏难度大,文武场都有,他仗着在学校练过体操,又一次取得了成功。除了兵团的人,周边的县、公社、村落、工厂的不雅观众也都远道而来,一睹他的风采。他们这个文艺宣扬队边劳动边演出,还要一专多能,除了京剧,还有独唱、舞蹈、话剧、演出唱,赵炎什么都会。1972年三师文艺汇演,他主演的《快乐的投递员》获奖,唱遍全兵团。
赵炎真正与相声结缘,是由于在一次“大会战”扛麻袋中扭伤了肋骨,住了两个多月医院,又规复了半年多,他闲不住,利用这个空档韶光,自编自演相声。马季的《友情颂》播出后,赵炎如获珍宝,他把对口相声改成单口,1975年参加了黑龙江省曲艺调演,自此一发不可收,从团宣扬队、师宣扬队,到兵团宣扬队,还被借调到省里和沈阳军区演出,在当地出了名。
马季师长西席慧眼识珠
把赵炎调回北京
1975年,中国广播说唱团招人,马季带着“红头文件”来到北大荒。广播说唱团的强项是相声,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都在说唱团。当时人才青黄不接,马季、唐杰忠也已经人到中年,最年轻的相声演员郝爱民也三十多岁了,以是马季急于找到相声新人。
在那之前,好多地方都要调赵炎过去,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的文艺团体,还有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心电视台,兵团都没放人。马季也要调赵炎和姜昆,兵团当然还是不放。马季、唐杰忠在当地演出了一段韶光,有时一天演好几场,嗓子都说哑了,兵团领导十分冲动,请他们用饭,问:“你们有什么须要兵团办的事吗?”马季说:“我们须要调两个人,一个姜昆、一个赵炎。”四位领导无法谢绝,只能放人。
姜昆当时人在北京,很快就到广播说唱团宣布了,而赵炎的调动却有些周折。当时他已经到了廊坊,在石油管道局运输汽车修理厂大修车间电工班修电瓶。马季在北大荒打长途电话回广播说唱团,让团里派人去廊坊调赵炎。团里的人没听明白,直接去北京前门的廊坊头条、廊坊二条胡同找人,以为赵炎住在那。找了两天没找到,问派出所也不知道这个人。再打电话到兵团问马季,才知道赵炎去的是天津、北京中间的那个廊坊。马季、唐杰忠干脆自己坐火车到了廊坊,向管道局领导要人。就这样,赵炎终于顺利回到北京。
天缘地缘都是缘,红颜心腹寻梧桐。当年兵团里有一位女副连长叫高红燕,曾一个人扛一百六七十斤粮袋,装满一车,也演过《白毛女》中的喜儿,可谓“文武双全”。高红燕看了赵炎演的《红灯记》,评价说:“李玉和演得真棒,切实其实不亚于电影里的李玉和。”两人由此相识、相恋。
1977年国庆节前夕,赵炎和高红燕结婚。这时赵炎已调到广播说唱团,婚礼那天,马季、唐杰忠、郭全宝、李文华、赵连甲、郝爱民、姜昆等人都来道喜,还来了许多兵团的战友。来宾即兴演出节目,马季说了段单口相声《拔牙》,赵连甲唱了一段山东快书。欢歌笑语,给赵炎留下了一次难忘的婚礼。
1976年与马季首次差错
跻身全国十大笑星之列
赵炎的本名叫赵殿燮,这个名字对付演员来说并不讨巧,念不清是“赵殿下”,不认识的人会念成“赵殿变”。马季让他改名,妻子灵机一动,建议他改为“赵焱”,马季认为还能更好,索性留两个火,成了“赵炎”。
赵炎给马季捧哏的第一段相声是《白骨精现形记》,首演时,赵炎特殊紧张,心跳加速,恐怕演砸了。马季对他说:“别怕,有我兜着呢!
”那是1976年,自此之后,两人互助韶光长达27年,留下了《红眼病》《四字歌》《百吹图》《五官争功》《地逻辑学》《训徒》等经典的声音。
上世纪80年代,马季师长西席意识到相声界不景气,舞台上相称一部分节目属于“低俗差粗”,即格调低、庸俗、质量差、演出粗。为了更好地传承相声艺术,成立了马季相声小队,赵炎担当队长,帮忙马季搞了一台《马季相声作品晚会》,推出一批新作品。他和师父、师兄弟一起深入到全国各地,演出达半年之久,把笑声传遍了工矿企业,山乡野外。一次在湖北演出,其他弟子的车坏在半路上,为了不冷场,赵炎与马季连续不断地演出了一个多小时。
马季和赵炎热爱不雅观众,他们走到哪儿演到哪儿。有一次在开往烟台的列车上,搭客们盛情约请他们演出,但是广播室设备出了故障,两人便挨节车厢送戏上门。
当时马季参与创作了很多电影,赵炎仍与马季合营,出演了《南洋财主》《笑破情网》等电影。1985年“十大笑星评比”,赵炎高居第五名。他还是相声界出色的主持人,马季弟子谢师会、马季从艺50年大型文艺活动,都由他担纲主持。
在马季的十九名弟子中,姜昆是大师兄,赵炎是二师兄,他与师父在一起的韶光最长。马季对赵炎委以重任,故意识地压担子、磨炼他、培养他。赵炎也一贯在不断学习、继续师父的功夫秘闻,积极发展着马季的艺术与精神。
从成为专业团体的相声演员开始,赵炎除了演出单口相声之外,绝大部分韶光都在捧哏。他的捧哏水平可以说是收放自若、绵里藏针,展示出了一定的文化秘闻,有人这样评价他:“诙谐诙谐的演出风格,不断修炼各方面技艺,台上从不哗众取宠,故弄玄虚,台下看重内涵教化,挥洒自如。他的相声给了谛听者思考与欢笑,也让不雅观众感想熏染到演出艺术的博大精湛。”
赵炎回顾
马季相声《宇宙牌喷鼻香烟》
推动小品成为春晚主流
我和姜昆调进中国广播说唱团后,拜在马季老师门下,马季老师齐心专心帮助我们,给我们创造机会。1984年,相声《宇宙牌喷鼻香烟》亮相央视春晚,轰动全国,我参与了创作的全过程。
为什么要创作这么一段相声?当时就觉得到,有些厂家从利润出发,不讲诚信,不择手段骗取顾客,这种征象屡禁不止,马季老师就决定讽刺一下这种不良社会风气。一开始写的不是单口相声,而是对口相声。对口相声有一种演出形式,叫“一头沉”,便是以逗哏为主,复述故事梗概,那么捧哏的呢,就起到一种起承转合的浸染,紧张的内容都在逗哏的那边。那么与其这样,是不是考试测验一下大家久违的艺术形式──单口相声?由于那个时候我已经和马季老师互助了,对口相声是由我和马季老师说,定了单口相声后,就由马季老师一个人说。
在创作过程中,到底是喷鼻香烟呢,还是其他的什么日用品?改过好几次,还改过火柴呢!
定了《宇宙牌喷鼻香烟》往后,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到底有没有这个“宇宙牌”。由于这是一个讽刺的题材,春晚演出影响这么大,难免有人会对号入座,你直接讽刺人家,谁也不干啊!
文艺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把很多征象浓缩了往后,放在一个厂家,放在一个推销员身上,你要实打实地说哪个厂家,人家也受不了。
马季老师很重视:“你们到国家工商局牌号局查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宇宙牌。”我也随着去查了,结果确实没有,那我们就敢说了。春晚播出往后,黑龙江牡丹江有一家香烟厂,这个厂长脑筋很灵光,他就捉住这个商机,注册了一个“宇宙牌”,那是后话。
这段相声也是经由了一些磨难才走上舞台的,有人提出内容是不是太锐利了?总导演黄一鹤坚持说:“艺术上要听专家的,听行家的,听艺术家的,真有问题,我导演卖力。要不然把我拿下去,不把我拿下去,这个节目就得上。”
那年的春晚是直播,马季老师戴着事情帽,穿着蓝色事情服,临时在说唱团借了电工师傅的工具兜子,“全副武装”上场了。全体段子引爆全场,笑声、掌声此起彼伏。这段相声形式新颖,马季老师并没有像说单口相声那样,站在原地演出,而更靠近于小品,也可以说,推动了小品这种艺术形式,使其逐渐成为春晚主流。
演出结束后,一名值夜班的工人把电话打到现场,说没听到,太遗憾了。由于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播。晚会事情职员问黄一鹤怎么办?黄一鹤找到马季老师。马季老师二话没说,拿起电话,又完完全整地把这段相声说了一遍,知足了那位工人师傅的哀求。这段故事,可以说是一个新版的《打电话》。
场内场外对这段相声的反响太热烈了,我卖力现场调动不雅观众,陪衬气氛,结婚时岳父送给我一块梅花牌全自动腕表,听这段相声时,鼓掌给鼓碎了。黄一鹤导演说:“我们这个现场指挥赵炎,他那个表都拍碎了,我得赔他一块!
”可是他一贯也没赔,一见面就跟我说:“赵炎,我还欠你一块表呢!
”后来他还真是个人掏钱去表店买了块新表,送给我,完成了他的这个心愿。
来源: 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