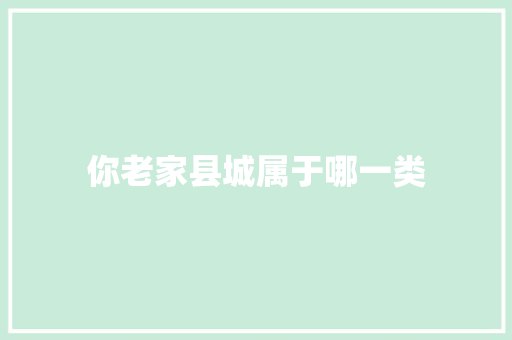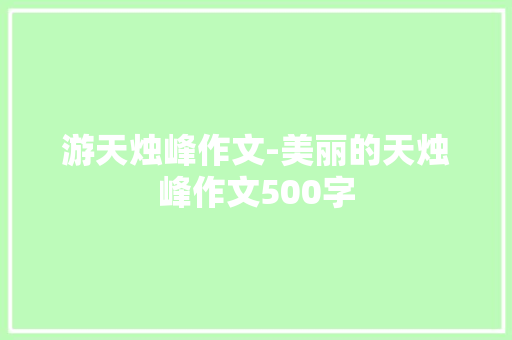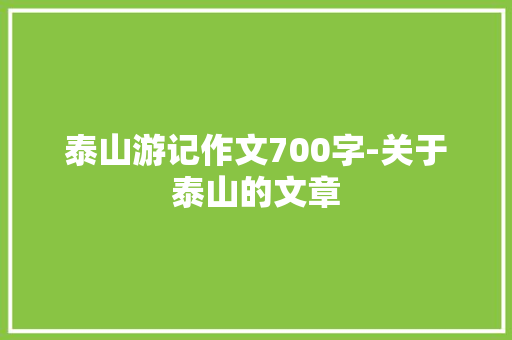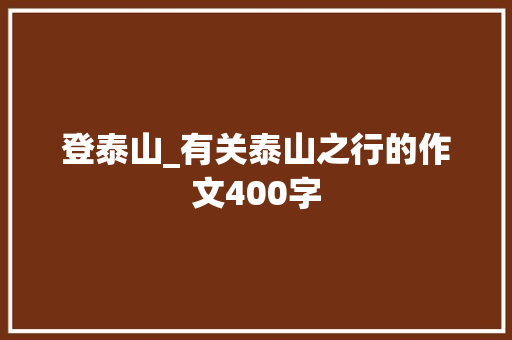文/陈玉莲
十二岁那年我来到了县城读书。当时的曹州县城相称的粗糙和零乱,东一片西一片的屋子。大多都是平房,高低不平,偶尔有几栋楼,都集中在南大街路两边,有政府楼、市委楼、百货大楼。

南大街南北走向,险些横穿全城,如一条大扁担似的,挑着那些高高低低的楼。
毕竟是从屯子到了城市,我的觉得大不同。一个明显的觉得便是汽车多、三轮车多、自行车多,人多。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三轮车,呼呼地,每天在马路上狂跑,尘土飞扬。马路上总是弥漫着一股子浓郁的石油味儿,还有散落的水泥灰味。那味道很刺激,乍一闻特殊不适应,但韶光长了,也就习气了,有时候还会以为石油味挺好闻的。
城里的人都穿得很好看,衣服干净整洁,尤其小女孩夏天里的裙子,天使般洒脱,我很倾慕她们有裙子穿,连小男孩都穿得花花绿绿的。我在外婆家的时候,一到夏天就穿外婆用棉布缝制的短裤短袖。男孩子赤裸着上身疯跑,大人们视若不见。可是到县城就不同了,有一天景象很热,我穿着短袖短裤趿着拖鞋到院子里看她们跳皮筋,惹得院子里几个穿花裙子的女孩嗤嗤地掩面笑,还窃窃密语,指指示点,现在想想还以为挺莫名其妙的。
县城里已经用上了电灯,每间屋子里都有一个长长的灯绳,风一吹晃来晃去的,我躺在床上,“咔”一拉,满屋子顿时亮堂堂的,角角落落都看得见,比屯子三天两头停电点油灯亮堂多了。这也是我开始喜好上县城的缘故原由。我至今还记得大姐让我猜的一则电灯的谜语:一把谷子,撒一屋子。真是太形象了,那时候,谷子是屯子,电灯是县城。把这两样东西奥妙地揉在一起,印在了我的影象里,再也没能抹去。
县城东面是一座不大的山,小葫芦山。了望黑乎乎的,像个小葫芦,再看像平地砌起了一堵城墙。有一条通往山上的路,曲曲弯弯的,中间还要途经一条铁路,那条铁路上每天都有拉煤拉货的火车,哐当哐当经由,还没看清车上装的什么东西,火车像泥鳅一样忽而就过了。“哞”地一声长鸣,吐出一团团白雾,直冲着路旁的人扑过来,如一个浪头打过来似的,挺吓人的。实在山上什么也没有,光秃秃的,除了石头疙瘩和茅草,便是一些松柏,像人一样直直地站着。守着山,守着那些石头。秋日随着父亲上山,偶尔还能摘几粒酸枣吃,红鲜鲜的,味道酸酸的,薄薄的一层皮儿,酸枣核坚硬,实在也没什么嚼头,把核在嘴里磨牙,我和二姐偏偏爱嚼那个酸甜味儿,每天嘴巴里似嚼口喷鼻香糖一样。
城里的电线杆特殊多,不远就一个,街头巷尾,学校商店,到处都是高高的电线杆子,电线架在空里,粗粗细细一把一把的,一点不好着。有好多上面还挂着大喇叭,灰白的颜色,中间还有个花芯样的东西,说是扩音器。喇叭里一天到晚哇哩哇拉地喊个一直,一下子是景象预报,一下子是特大新闻。声音有男有女,都是高亢冲动大方,间或还要扯起嗓子喊几句口号。说上几段广告,某某商开张了,某某商有优惠活动了,等等。此起彼伏,实在聒噪得让民气烦。想想乡下村落落里那种沉着的生活,倒有些不真实了。
那时候县城最高大雄伟的建筑该当算是百货大楼了。百货大楼坐落在南大街东边十字路口右边,楼顶上还有个红亮亮的瓦顶子,当时非常有名,只要一提起百货大楼,就没有人不知道的。
百货大楼后面是个大杂院,高高低低住着各地来矿工挣钱的人,错错落落排开。院子前面还有个电影院,叫光明电影院。小时候大姐常带我去看快散场的结尾电影,或听片尾曲,由于末了几分钟不收电影票,也没有人看守入口了。每当散场出来,我就抱怨大姐不早点进去,前面的情景一定很好看,没头的电影看得摸不着头脑。大姐总说,来日诰日一定早点溜进去。我便冲着夜空一阵高喊,“大姐真好。”现在电影院早就没了,再后来就没人看电影了。电视机代替了电影院。
前些年我回到家乡县城,矿厂那片地方已成了一片废墟,现在有些废墟还在。那个大院子还在,只是风雨飘摇,寂寂无人,显然是荒漠良久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年过“六一”儿童节,矿厂举行一次全县青少年儿童美术展,我那时大概是上小学四年级或是五年级。由于刚刚看过电影《小花》,对里边的小花特殊祟拜,对她的俏丽特殊倾慕,没事儿就用柳枝儿编个圈圈戴头上临摹小花的剧照。便是小花过草地找哥哥的那个镜头,学着画了很多次,让我二舅教,未曾想稀里糊涂地被学校选中参加了矿厂“六一”美术展览。
我清晰地记得,我的作品被镶在一个玻璃框里,高高地悬挂在大厅第一厅入口处上方。人们出出进进,非常能干。有一天我和院里的几个玩伴来看展览,走到第一厅门口时,举头一看,那张画赫然在目。我不禁自满地指给他们看。他们顿时都傻眼了,呆呆地看看那幅画,又呆呆地看看我的脸,嘴里嘀咕说:“真的假的?”小花的侧脸太像了,虽然他们一脸迷惑,实在我在心里默默感谢我二舅,是二舅辅导画得好,知足了我的虚荣心。
随着我和小伙伴们的发展,城市也在变革。而我从我们的县城来到了另一个县城生活。在发展中发生的变革,每每也是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的变革密切干系。
我刚参加事情那会儿,电脑还是奇异物件,笨重的大屁股电脑,我们单位只有两台,领导和办公室。普通人想都别想,偶尔到办公室看上一两眼,给人的觉得高不可攀。
我刚到单位从事统计事情时,制表、填表、汇总、年终成册,全部都是靠手工操作,数字齐备后,先在一张画满空格的白纸上填好,然后才在正式表上工致地填报。那时候,我们科室都是些刚刚参加事情的年轻人,心明眼亮,花季正盛,干事负责麻利,一丝不苟。记得有一次,单位大检讨,为了把几年的统计数据上报,我加班加点完成,废寝忘食,肚子叽哩咕噜的,能急出一头汗来。别的单位都是电脑填报,早已完成,手工终是赶不上电脑。
短短几年间,电脑填报数字取代了手工,统计报表自动天生,提高了事情效率。现在我的事情,只需在电脑上敲敲键盘,动动鼠标,哗哗啦啦,复制、粘贴,十几分钟,多则二三十分钟,一个事情报表就完成了,里面缺点险些是零。
如今,空隙之余,呆坐在电脑前,偶尔想想年轻时候莺歌燕舞地在办公室飘来飘去的我们,真有如前尘往事之感。“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当我们开始沉浸于回顾时,实在也就解释时期变了。无论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这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且当这种怀旧的感情日渐浓郁深厚、不克不及自休时,就会成为一种病。有时候到大街上走走,就会创造人无端地多起来,美女如云,靓仔成堆,行色匆匆,纷至沓来,如过江之鲫。而落寞中已经很难再从中找出一张熟习的面孔来,乃至已经找不到自己该当站的位置了。
人生便是如此,长江后浪推前浪,芳林新叶摧陈叶,原是容不得犹豫不雅观望的。稍不留神,就似一本书中的几行枯躁的笔墨,根本来不及细看,哗哗啦啦就翻过去了,而且翻过去就永久翻过去了,谁也不会再翻回来看了。
这天下每天都在发生着变革,可以说变革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而一成不变、墨守陈规、抱残守缺,究竟会被淘汰。这大街上彭湃而来的滚滚人流,那些风华正茂青春洋溢的新鲜面孔,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大概要不了几年,那个嘴里嚼着糖葫芦、身上穿着古怪精灵的时髦装扮服装依偎在男友身边撒娇的女孩儿,就会为人妻为人母,开始愁眉苦脸地抱怨起生活的艰辛来。大概要不了几年,那个目空一切犹豫满志的翩翩少年,就会在生活的重负之下低下高傲的头颅,把说不出的苦痛连同酒水一起咽进肚子里去。而这些年轻人谁也不会知道,那个蹲在街头摆地摊的头发斑白、身材雍肿的胖妇人,往前推二三十年,却原来便是这个城市万人空巷一票难求的一代名伶。而那个蜷缩在街角无精打采地晒太阳的龙钟老者,原来也曾经是轰动全城、披红挂花、风光一时的劳动模范。以前争的要的,如今都不值得一提,空空如也。
前年深秋我又登了一次泰山。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曾经爬过泰山,那时我刚刚毕业,还不到二十岁,何等的年轻啊!
对泰山的影象也是轻描淡写的,蹦蹦跳跳间,乃至都没有觉得到特殊的累就已经踏遍了泰山。然而再次登泰山时,在山脚下望着那高高的直插云霄的山峰,顿觉山道之难,难于上上苍。我乃至疑惑自己曾经来过?真的来过吗?四顾茫然,群峰耸翠,却找不到一点点我曾经来过的痕迹。
那天走在背阴的山道上,长长的无尽的台阶在一层层地消磨着我残余的激情,嗖嗖刮来的寒风在不断反攻着我的怠倦。我确实感到体力不支了,这是二十多年前登山时我从未有过的,当我试图停下来歇一歇时,满山的砭骨寒气迎面而来,从里到外都是冰凉。
经历了几次痛楚的徘徊和挣扎之后,我终于来到最近的泰山天烛峰。依稀如昨,天烛峰的阳光还是那么妖冶,天空还是那么蔚蓝,放眼望去,山风猎猎,群山如拱。有一刻我真的疑惑我曾经来过这里,左顾右盼,找不到一点点过去的影象。山顶何人初见月,山月何年初照人?实在正如我们的人生,来过没来过,有什么差异呢?山高水长,亘古如此,年年纪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统统都将过去,统统又都会重新开始。
毕竟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日月催人老,我再也无力攀登十八盘了。下山时我颓然坐在索道上,不经意间想起了崔健的一首老歌歌词“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
作者简介:
陈玉莲,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铜川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省市报刊杂志。
摘选自:散文之家,版权属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