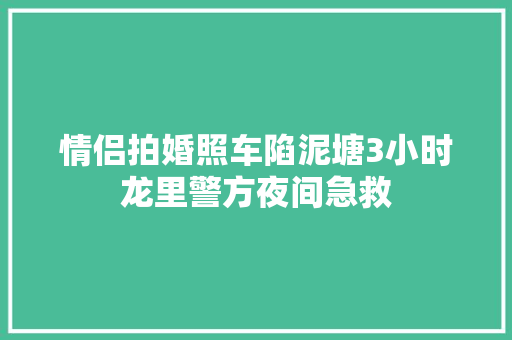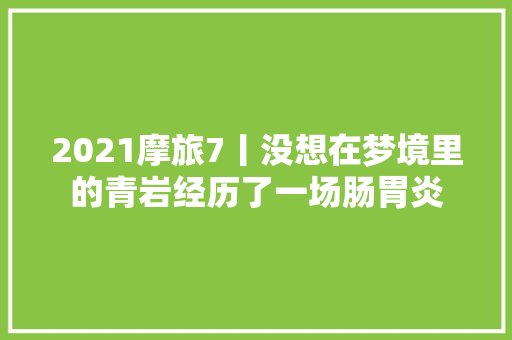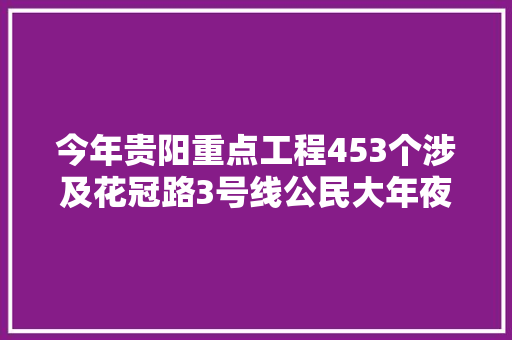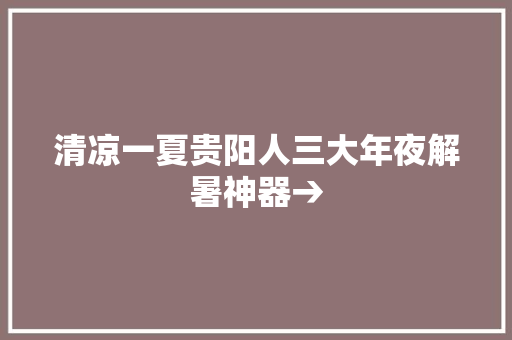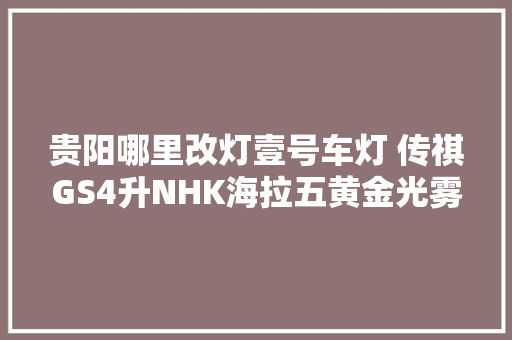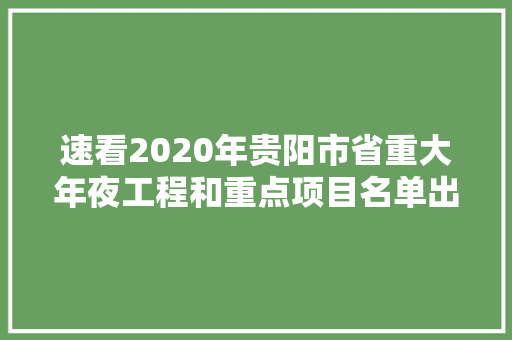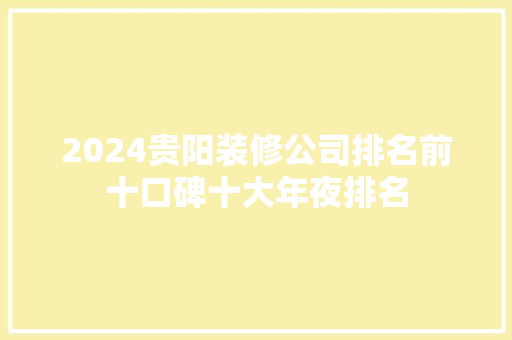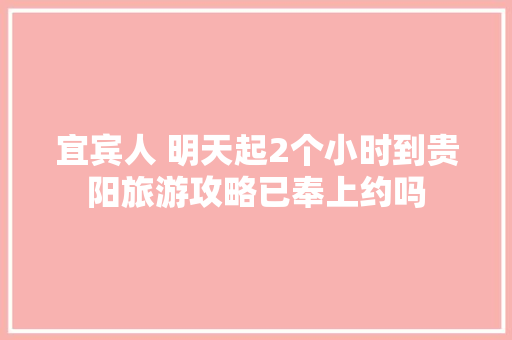还有两个月,李麦宁就93岁了。很难想象,一个93岁的老人有着如此清晰的影象,过往岁月中经历的点点滴滴,幸福与苦难,并没有随着光阴而烟消云散,在老人的回顾中,它们穿过岁月的尘埃,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13岁,因战乱和父母分离,李麦宁从此开始独自面对人生。光彩的是插班就读于达德学校,受教于黄齐生、谢孝思等师长西席,为生命打下了倔强的底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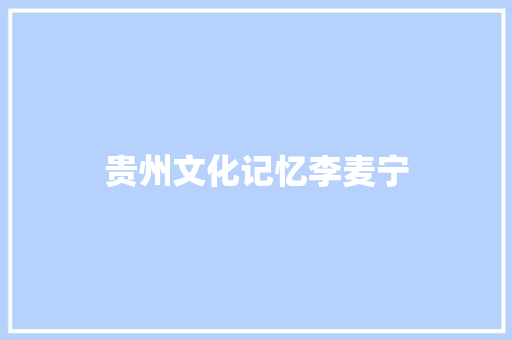
1943年,抗战到了最艰巨阶段。21岁的李麦宁大学毕业就踏上流亡迁徙的路,辗转一年多,颠沛流离中经历了火车撞车、汽车翻车等事件,摔断了一条腿,还差点丧命。
幸好生命中还有诗歌,还可以歌唱,诗歌成了一个迷茫青年的寄托与希望,他说:“只管喉间有把锁,但我仍要歌唱……”
24岁,李麦宁创办了文学刊物《离骚》,刊登诗歌和翻译的外文作品,这本杂志受到当时贵阳文学青年的追捧。
1949年贵阳解放。李麦宁进入“中学西席演习班”学习,那一年他27岁。学习结束后,被分到惠程度易近族中学任教,之后调往龙里中学,一年后再调清镇中学。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就定格在了清镇,定格在西席这个职业。
年轻时贵州文坛上进步墨客形象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逝,直到1997年《贵州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才把他重新发掘出来。我省作家戴明贤、学者刘学洙对李麦宁都有较高评价。戴明贤称他为:“青年墨客老西席。”“读了他的诗选,感慨贵州新诗创作,上世纪四十年代已臻于成熟,在全国毫无逊色。”刘学洙说“李麦宁在贵州当代文学史上霸占一席之地。”学者杜应国用“消隐的歌者”来概述李麦宁的生平。
《贵州新文学大系》的评论者写道:“李麦宁的诗长于表现人们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他“还长于抒写自己的内心天下。”不少诗“写得清丽、隽永……在句子的熬炼高下了不少功夫,读起来使人感到寓意较深,诗味较浓。”
听李老摆故事,读他的《麦宁集》,会让人有这样的认识:他的经历便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侧影。他曾经是一个充满叛逆精神的进步青年,一个才华横溢、激情澎湃的墨客。历经人间沧桑后的李麦宁,如今是一位儒雅谦和的父老、一位敦厚严格的老西席。只有在阐述到人生中的某些难忘的片段时,墨客的气质才会显露出来。采访中,老人几度哽咽,丰富的内心情绪溢于言表。他说:感激你们,让我有机会说出我心里的话!
在李麦宁的阐述中,对他生命中打仗过的人,他都会说一句:他对我很好。文革中,李麦宁被批斗了77次。纵然是对文革中批斗过他的人,他也并不记恨。他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达德学校的思想启蒙
1936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立成经由再三考虑,只管形势不是太好,他还是想回趟老家贵阳,一来修葺前妻的宅兆,二来为编写川黔两地的族谱网络些资料。已经64岁的他,不知道将来还能有几次还乡的机会。13岁的儿子李麦宁从未回过老家,这次他想带上一起回去。李麦宁得知后也非常高兴,自幼成长在北京的他还从来没有到过南方。父子俩大略整顿后,于当年秋日动身。
辗转到年底,父子俩终于抵达贵阳,寄居在李麦宁四伯父家中。未料贵阳的冬季阴雨绵绵,寒冷湿润,无法动工修坟。李立成虽然内心发急,但也没有办法。为了不影响学业,李麦宁作为插班生到达德学校读初二。
“我在达德学校只读了半年,但这半年对我的人生影响巨大,我学到学会了明辨是非,学会怎么做人,学会热爱自己的祖国。”
回顾起在达德中学读书的光阴,李麦宁影象犹新。尤其是黄齐生老师和谢孝思校长两位,给他的教诲和影响最大。
“黄齐生老师教我们国文,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但满头黑发、精力充足,他上课时,常常结合传授教化讲述国家大事乃至家庭小事,上至反帝反封建,下涉为人处世、道德教化。记得我刚入校的时候,班上的男同学欺生,我哭着回家时,黄齐生老师瞥见了,拉着我讯问是什么事,他听了我的答话后,安慰我说找那几个同学谈谈,这之后,班上的同学就再也没有陵暴我了。”
“校长谢孝思每周一都要对全体学生训话,哀求学生除了负责学习外,还哀求大家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哀求学生着衣整洁,不准披衣服和拖着鞋子,走路必须挺胸举头,如果他在路上创造学生走路姿势不对,一定会纠正。他们的教诲对我树立精确的人生不雅观有极大的帮助,在往后的人生中,我随时以此为鉴,不敢轻忽。”
第二年暑假,修坟落成了。父子俩正准备返回北京,遭遇“七七事变”,紧接着北平沦陷,回北平的操持落空。
回不了北平,李立成只好安顿下来,在省培植厅找了份事情。几个月过去了,北平家里没有一点传来,李立成焦急又担心,末了他决定冒险返回北平。李麦宁没想到,这一别,父子竟成永诀,直到1944年父亲在北平去世,李麦宁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一壁。而这趟探亲之旅成了他人生轨迹的迁移转变,从此辗转流落,终极在贵州度过了自己的生平。
在桂林交往文艺大家
1937年,从达德学校毕业后,李麦宁考进了南明高中。在学校期间,他参加了进步组织筑光音乐会、沙驼话剧社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和进步青年们一起积极开展抗日宣扬活动,并因此而受到当局的威吓与阻挡。
1939年发生的“二.四”大轰炸,彻底冲破了贵阳的沉着。大轰炸之后,亲友们都疏散到乡下,李麦宁只好以沦陷区学生的身份,到“战区流亡学生处”报到,结果被该处安置到位于湖南安化的蓝田师范学校求学。1940年毕业后,考入已迁至辰溪的湖南大学文学院。在这里,李麦宁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的早期作品,大都揭橥在湖南大学的校刊上。
1943年秋,湘桂边疆战事告急,学校安排毕业班提前毕业。就这样,李麦宁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告别同学,寻觅安生之处。
1943年的桂林,迎来了全国及港澳等地的许多著名爱国人士和文化名人以及一些文艺团体。文艺家们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此时的桂林,群星云集,被称为“文化城”。
李麦宁也从湖南辗转到了桂林,并在这里遇见了久违的九哥李白凤,经九哥先容,他在桂林中学初中任教。在桂林,他度过了逃难途中最快乐的光阴,结识了田汉、熊佛西、端木蕻良、丰子恺、聂绀弩以及著名的民主人士柳亚子师长西席。
李麦宁说,这些文化人中,熊佛西和端木蕻良与他来往较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达德学校读书时,我就读过戏剧家熊佛西师长西席的《孔雀东南飞》,没想到在逃难到桂林后,竟然在九哥李白凤家里认识了他。在桂林期间,熊师长西席和田汉师长西席、欧阳予倩师长西席一起组办了西南八省戏剧展览。为养家糊口,他的夫人叶子与广西女作家凤子开办了咖啡馆。后来熊师长西席比我先到贵阳,在贵阳期间,他又举办了个人画展,我还组织了报社的来为师长西席的画展发布新闻,听闻戏剧家办画展,来参不雅观买画的人很多,熊师长西席把卖画收入的一半捐出来作为对逃难到贵阳的文化人的救援。”
“当时流亡到桂林的文化人很多,端木蕻良最令人同情,他当时得了肺病,情状也比较窘迫,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人们怕传染,都不太乐意和他来往,只有我不怕,我和我哥哥常常帮助他,常常去看他,给他送吃的。有时他会善意提醒我,为了我的康健,少去看他。那时候我很年轻,对他和萧红的故事也很好奇,相处韶光久了,他也给讲述了他与萧红的经历。我根据当时他的痛楚状况,可以看出萧红的去世对他的打击并不比别人小,由于他们之间是有感情的。
李麦宁回顾:“当时端木蕻良在写一本书《大江》,还没写完,他曾说,如果我不是已经在桂林中学任教,我就可以去给他记录。他对我也很好,后来他逃难到贵阳,我后到贵阳时,他已经去遵义,后来又去了重庆,我们也没再见过面。”
田汉由于年长,李麦宁也很尊重他。田汉很豪放,喜好和年轻人玩,和李麦宁哥哥关系很好。李麦宁说:“哥哥家做了好吃的,就去请田汉来用饭。他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梅娘曲》、《夜半歌声》等等都为同学们所认识和传唱,我还组织了同学们去听田汉师长西席的讲座《屈原之去世》,田汉师长西席的演讲激情四溢而极富煽惑性。”
1944年,随着战役场合排场的恶化,李麦宁和这些文艺界人士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
困境中响亮的《离骚》
经历痛楚和磨难的流亡生涯后,李麦宁再度回到贵阳。
湘、桂大撤退,流亡两省的文化界人士,被卷入逃难者年夜水滞留贵阳。前后两段期间,由于频繁地和他们打仗,在青年李麦宁心中植下进步的思想和热爱文艺的火种。
当时的贵阳虽然有10来种报刊出版物,但文艺副刊却很少,纯文艺刊物则属空缺。李麦宁在回顾录中写道:“只管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聚拢在一起的时候也评论辩论过该当冲破这种沉寂的局势,创办一个纯文艺刊物,但要实现这个欲望,必须具备两个主要条件,首先要向国民党机关办理申请并获批准,其次要钱——当时办文艺刊物是要赔钱的。”
也是机缘巧合。1946年,李麦宁在出版自己的散文集《百合花与墨客》的过程中,在贵阳文通书局认识了印刷厂的张志毅厂长和两位喜好文学和美术的年轻人张公达和吴剑光。并通过他们,认识了大同银行的襄理(注:相称于副经理)陈海涵。这几个人,连同大同银行的其余两位爱好文学的青年,经由几次磋商,决定创办一份文学刊物,在李麦宁的倡议下,刊物名称定为“离骚”。李麦宁说,之以是将刊物命名为《离骚》,是由于对伟大爱国墨客屈原的崇敬和仰慕,用他的代表作为刊物名,以纪念他的爱国情怀和精彩的文学才能。
李麦宁清楚地记得杂志创办伊始的每一个细节。陈海涵担当发行人,卖力杂志的登记申请及经费的张罗,很快就约集了一个“积金会”,用利息支付印刷等用度;李麦宁任主编,卖力征稿、审稿、定稿、排版;经费进出由张公达卖力;其余两位大同银行的职员帮忙李麦宁事情;吴剑光卖力美术设计。
在大家的同心协力下,《离骚》创刊号出身。
《麦宁集》详细记载了创刊号揭橥的作品目录和作者。杂志采取稿件的标准因此鼓吹爱国主义思想,宣扬自由、进步为紧张内容的文艺作品。刊登的文体也丰富: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及音乐、美术作品等。
《离骚》杂志创办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几经磨难。首先是经费问题,办到第七期,无法支付稿酬乃至印刷用度甚至停刊,结果李麦宁靠卖诗集攒钱复刊。后又发生一期杂志因戳穿某医院院长贪污文章被全部没收的事,为此李麦宁还被警察局传讯。接着一次以杂志社名义筹办的纪念屈原音乐诗歌晚会被勒令取消。之后,李麦宁在妻子支持下,靠变卖首饰和衣物来支撑,在困难中编辑出版第十一、第十二末了两期杂志。
《离骚》1946年创刊,1948年停刊,共出了12期。这本小小的文学杂志,在那个国共对峙、战云密布的时期,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共鸣,产生了不小的反响。戴明贤老师在为《麦宁集》写的序里提到:收入《诗文史料汇辑》的同时期人黄炜回顾文章中说:“《离骚》出版后,给山城一大批爱好文学的青年开辟了新园地,许多从未揭橥过的‘处女作’纷纭投向《离骚》,每期出版后青年学生争相传阅。……《离骚》杂志对贵阳文艺活动,起了促进浸染。”
怀念九哥李白凤
李麦宁同父异母的哥哥,他称呼九哥(族中排行第九),是著名学者、墨客李白凤。
兄弟两在1940年代湘、桂大撤退期间相逢,之后,由于战役期间形势所迫,哥哥离开贵州另谋他处,弟弟留了下来,从此再未相逢。
李麦宁在《血写哀思泪写情》这篇怀念哥哥的文章里写到,1981年,在九哥去世两年多后才在一本杂志里获悉这个噩耗,之后,才通过杂志编辑部联系上九嫂及诸侄。
李麦宁的少年时期,和九哥一同生活在北京,结下深厚的兄弟情。
1933年,李白凤在北京考上民国大学国文系,麦宁也小学毕业,考入北京第四中学。
“九哥当时是家中最大的孩子,在父亲的严格教诲下,他能背诵《唐诗三百首》、《诗经》、《楚辞》以及其他古典书本中的许多诗词和文章。他偏爱英语,清晨起床后,就到院中树下朗读原来的莎翁名著《奥赛罗》、《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片段。每天早餐后,他骑车先送我到北京四中,然后径直去民国大学,在途中,就向我讲述这些书中的故事情节……我对几位天下著名的文学家、墨客如高尔基、托尔斯泰、普希金、歌德、雪莱、海涅等人的印象和浓厚兴趣都来自九哥的口述。”李麦宁回顾道。少年时期,李麦宁的两次生病住院,也是年长的九哥主动探望照料,这些,给李麦宁心中留下温暖的回顾,并永生铭记。
李麦宁就读湖南大学期间,在芷江和已在《中心日报》担当编辑的九哥意外相逢,之后九哥离开湖南到西安,兄弟分别。1943年,李麦宁成为战区流亡学生到了广西桂林,在桂林又惊喜地和早前来到这里的九哥相聚。在桂林,李麦宁和九哥一起生活了半年多,并通过九哥结识了许多文化界名人:田汉、熊佛西、端木蕻良等。1944年夏,由于战役形势恶化,九哥一家迁居,李麦宁洒泪送别哥哥后,独自踏上流落路。
两兄弟末了一次异地相逢是在独山扶轮中学。1944年10月,由于日军逼近柳州,独山危急,学校奉命终结,全校师生各奔东西。九哥离开贵州,麦宁留了下来,这次分离竟成永诀。
后来,李麦宁是通过九嫂刘朱樱写的《忆白凤》一文理解到九哥之后的经历、遭遇:成为大学教授,创作了不少精良的文学作品,在那个分外期间被打为“极右派”,受尽磨难……1978年,李白凤平反,规复了河南大学事情,郑州大学也准备聘他去做教授。此时,九哥却由于长期操劳病倒,并于1978年8月18日与世长辞。
不后悔当老师
1949年贵阳解放后,李麦宁接到关照前往“贵阳市中小学西席学习班”宣布。此时,由于之前出版诗集和办《离骚》杂志的经历,李麦宁受到贵州省军事牵制委员会新闻接管处刘子毅处长的关注。在一次发言中,刘处长表示想让李麦宁到即将成立的贵州公民出版社从事编辑事情。李麦宁很高兴,表示先接管师训班分配到学校事情一个学期后再来。
结果李麦宁服从分配到了惠程度易近族中学。
“到了学校,看到学生们穿着低廉甜头的土布衣服,破褴褛烂的,头发又长,在操场上打球、投篮。我每天看着学生,就跟校长说,这些学生太可怜了。那时候为了政治的须要,要开斗争会,这些学生的家长,有好多都是贫下中农。每个学生上去,看他们的爸爸妈妈斗争地主时都哭,我也忍不住哭。这时候我的思想就起了变革,我爱人那时候还没有事情,我回去就跟她讲,我说灵珠,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我说我起初到惠水不习气,想在贵阳做公民出版社的编辑。现在看到这些同学又可怜又可爱,我同他们感情很好。学生们到我家来,我和他们谈天,建立了感情,我不想当编辑了。我爱人说,好嘛,你既然喜好,就这样去做好了。”
又一次周末李麦宁从惠水放假回家,去找刘处长,把他的想法见告刘。“我说我同情这些学生,我喜好他们,我要为他们事情。”刘子毅处长对我的想法和做法表示支持和理解,并鼓励李麦宁好好事情。
“我就这样教书了。”回顾起这些事情,李麦宁老人的口气是沉着的。当年,凭着对学生纯挚的同情和热爱,他放弃留在省城做编辑的机会,携家带口到偏远的县城做老师,他是真的不后悔。
在惠水事情5年之后,李麦宁调到龙里中学教书,一年之后,他和妻子同时被调到清镇,任教清镇,从此在这里扎下了根,投入生平的心血。
文革期间,李麦宁被批斗77次。本日,提及这些事,他依然会难过,依然表示难以理解。但他说,对付整我的人,我并不恨他们。我也没有想过要报复他们,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也是受害者。
在清镇几十年的传授教化事情,让李麦宁和这里结下深厚的感情。他说,“在这里有很好的兄弟姊妹、父老乡亲。现在我在写一篇文章《清镇,我的第二故乡》”。从这个标题就可以看出麦宁老人和清镇的感情。
“我教得最早的一届,第一个班,现在的学生都有70岁了,他们的孩子又是我的学生。教他们两代人。我对学生是比较爱护的。我喜好的同学比较多,喜好我的同学也比较多。”
李麦宁说最让他顾虑的还是学生,他离不开学生。最近做梦都是在给学生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