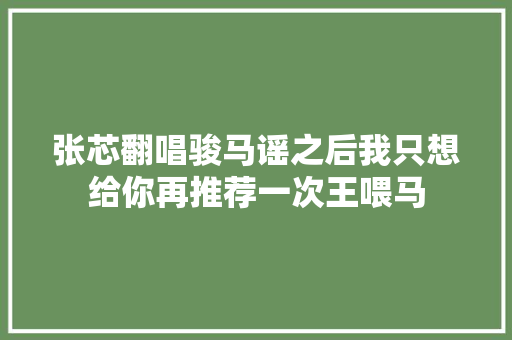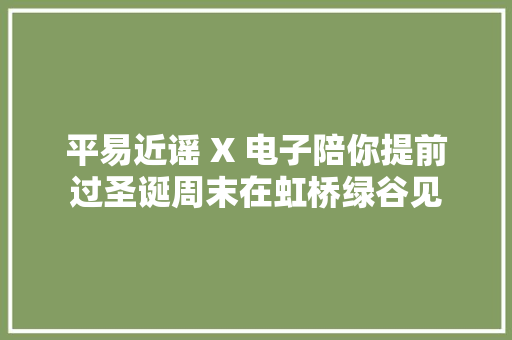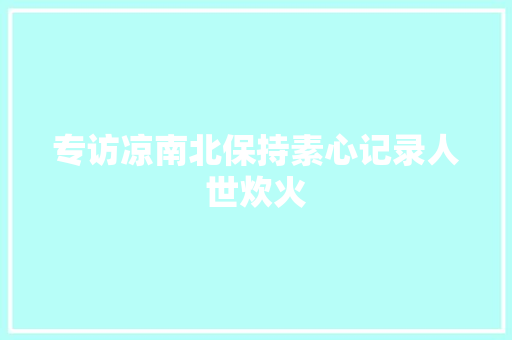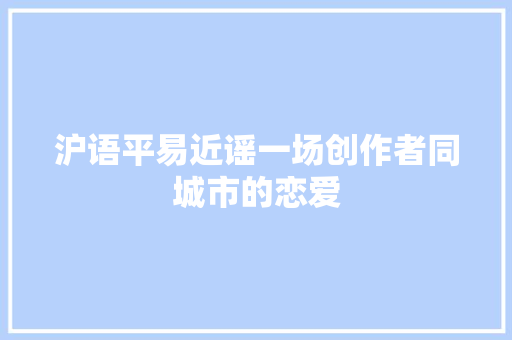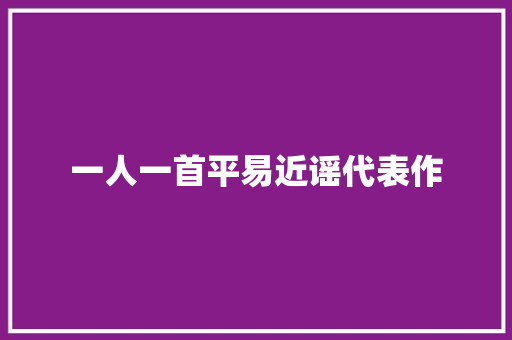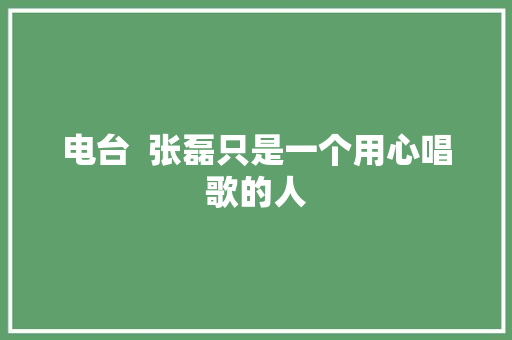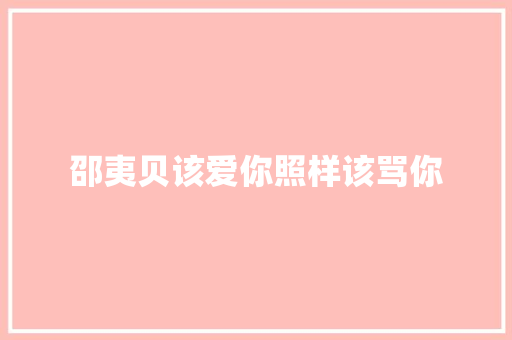鲍勃·迪伦在美国民谣界的地位,就算不理解的人恐怕也从昨天刷屏的那些文章中知道了抗议民谣,知道了他确切的一些业绩。
宋冬野的《董小姐》,只管随处颂扬但全曲除了著名的开头“董小姐”三个字我能哼出来,以及“兰州”这熟习的字眼之外,整首歌没有任何一点冲动我。此外他更著名的《安河桥北》我听过一遍但毫无印象。不可否认,《斑马,斑马》听了之后有听《夜空中最亮的星》时的那种冲动和代入感,但很抱歉,我听的是中国好声音里面张婧懿演唱的版本,搜到宋冬野的版本听了四句就赶紧切回去了。

民谣歌手在中国音乐界里始终是个边缘、疏松的群体,现当代的民谣作为一种音乐类型也始终没成景象,家当就更谈不上。因此在中国,一首民谣歌曲能红遍大江南北是一件很怪异的事情,就像《董小姐》、《斑马,斑马》因选秀节目走红,在人们眼里这些歌和《那些花儿》、《平凡之路》有没有差异?在人们眼里宋冬野和张杰有没有差异?
不是抱把木吉他,再加个口琴,好吧,再加个手鼓(不能再多啦),便是民谣了。我曾在大理古城里徜徉过半月,在这个手鼓各处的地界,有时候容身听那些面色黝黑的男人们抱着吉他在酒吧门口唱那些得不到的、留不住的人和事,我只有一个觉得:矫情。
但我喜好民谣。
6年前,当我在兰州的一个酒吧第一次听着李建傧弹着冬不拉闭着眼唱《夜夜的晚夕里梦见》,我浑身是过电般的觉得。他闭着眼睛唱,娴熟的弹着冬不拉或者吉他,吹着口琴,没有苦大仇深、没有落魄,全体人散发出阔别尘世的淡泊和沉着。强大的气场让在场的每个听众都安静、专注的听着。从他的现场演唱你能感想熏染到音乐的力量,能从他身上看到的那种对音乐的热爱和超越凡人的心肠和聪慧。
此后,又听到了野孩子的歌,这支同样来自甘肃的民谣乐队,让我惊叹民间的音乐这么丰富和有魅力,远远不是电视上、网络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浮华表象,他们手风琴伴奏的风格对后继者也影响深远。还从一起在师大读书的青姐那里知道了兰州的六个国王、低苦艾,宁夏的苏阳等等西北的民谣歌手、乐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师大自己有个民谣乐队花爵鼓,他们原创一首《小街》在当时也让不少人听后浑身过电,吉他、手风琴和手鼓,我能单曲循环一整天,逢人就推举。
再后来,又在兰州的音乐小酒馆葵live house听了万晓利,听到了带着一种表面荒诞不经却暗含着讽刺意味的《狐狸》,也是愉快。
后来来到北京,我以为能听到更多民谣,但创造能打动我的太少了。和朋友谈天谈起来,我说:“经济发达地区的民谣听着都挺矫情的。”
民谣必须成长自大地,必须从它的土壤中汲取营养,它和盛行音乐不同的便是纯“创作”出来的歌曲总是少了灵魂,少了灵魂的就不会再是民谣。
民谣注定是为了生活、为了爱情以及为了空想而惆怅、而歌唱。这种惆怅必须诚挚,当失落去了生活的根基,歌者有感而发越来越少,为了唱而唱越来越多,注定造作。
比如低苦艾,在虾米上面他们的标签是城市民谣。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是在兰州商学院附近的一个类似798的文化创意园区,当时听的是《仲春的素描与光》,再后来便是那首令他们声名大噪的《兰州,兰州》了。青姐当时还叫我一起去西安看《兰州,兰州》的演出。
是不是由于火了、商业了呢?在此之后,低苦艾仿佛进入了瓶颈,自由、肆意的音乐少了很多。去年他们在北京有演出,在比葵live house大不了多少的摩登天空 live house,还是那个喜好轻微弓一点点背对着麦克风唱歌的刘堃,能感想熏染到乐队想在新作品上进行曲风打破的考试测验,但听过之后终于还是少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宋冬野涉嫌吸毒和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由于时差的关系,巧合的发生在了同一天,不少人说鲍勃·迪伦也吸过大麻,但是从无数刷屏的文章和那些搜得到的电影、传记片中,不理解的人也能知道鲍勃·迪伦对美国历史是产生过影响力的人。宋冬野们呢?
只管在美国部分地区吸食大麻合法,但菲尔普斯吸大麻的事情被曝光不也成为了他最大的丑闻吗?退一万步宋冬野即便现在是和鲍勃·迪伦一样“教父级”的人物,吸毒的事情曝光也该是被唾弃的吧。
刚才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去虾米搜李建傧的歌,看到了他在虾米的自我介绍:佛教徒,食素,禁烟酒及统统麻醉品。我对他的钦佩之情又多了几分。生命中有所“禁”,不该只是佛教徒的戒律,而应是每个人的昂首三尺的神明。
伟大的朝阳群众这次有立了功 ,乃至有不少网友调侃p图
但是 这不影响我喜好他的歌 毕竟当时陪我走过好长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