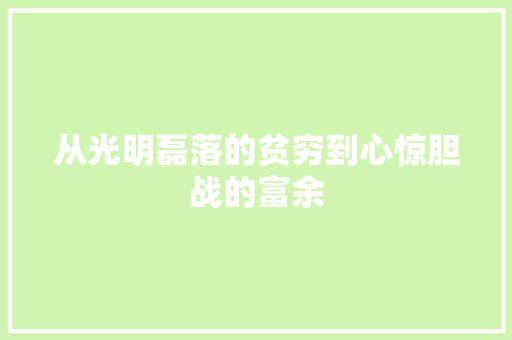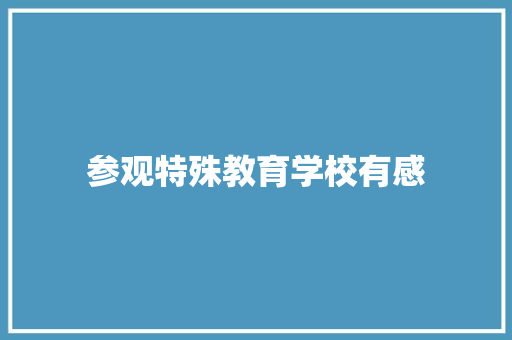2009年9月12日晚上,在北京Mao,正在上演Joyside终结前在海内的末了一场演出,这场演出用他们的一首歌命名的,叫做“The last song for the endless party”(无尽派对的终曲),他们在歌中唱道:
“now is time to live,do you dare to go

现在是时候离开了,但是你真的敢吗?
This is the last kiss for our endless love
这是我们无尽爱意的末了一吻”
演完这场,Joyside就到这里。这之后的十年,新的乐队还会源源不断地到来,满地上破碎的啤酒瓶像一代人逝去的青春,隔天就会被这座城市清理地再没有痕迹,“摇滚之王”变成一个笑话,飘浮在一个时期的上空。
01
边远在乐夏上不能说的故事
2019年愚人节那天,Joyside发布了一条微博,上面写着“the joker is back”。
有位乐迷留言说“我的遗嘱清单要更新了,我真的好想哭。”
对许多老乐迷来讲,joyside不止是一支乐队,而是承载着他们青春的一个载体,Joyside的每一步发展都曾和自己息息相关,在他们终结后的十年里他们有和Joyside一样各自走向属于自己人生。
在乐夏第一轮亮相的采访中,边远说:“那时候特殊愉快,由于每天都有很多故意思的事情可做。”
导演问:“比如说呢?”
边远答:“比如不能说。”
那些边远在乐夏中不能说的故事,却被影像保存在了有关他们的一部部记录片里,从《北京浪花》到《颓废的东方》《欧洲巡演记录片》再到末了的《破碎》,留下了Joyside一起的成长轨迹。
那时边远住在北京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夏天太热的时候,他只能搬到表面的露天阳台上去睡觉,他尤其喜好下雨的时候待在阳台上,不过最近他交了女朋友,不能常常自己一个人待在阳台了。
边远总是缺钱,从家人朋友到经纪人都被他借过钱,有时候出门坐公交车由于打扮的有些邋遢,阁下的人会宁肯站着也不坐在他身边。
刘昊的家人并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干些什么,弗成思议还会有人给他们拍记录片。只知道他每天都在饮酒、玩乐队,他也不想去和家人详细阐明,由于他以为自己在做故意义的事,并没有摧残浪费蹂躏生命。不过想饮酒的时候他只买得起啤酒,再好一点的酒就要偷了。
虹位那时候在脖子上搞了一个纹身,追着他问:“为什么想要在这纹个身啊?你家人知道吗?”虹位淡淡地说:由于我喜好,想在这纹就纹了。
关铮回顾那时候从来没叫妈妈来看过自己演出,由于很少有一场演出能彻底演完的,不是喝了太多酒,便是打起了架。
这些都只是十年前joyside的一角,就像边远在《北京浪花》的一开头就说:“人类是奇怪的,大部分人并不明白我在做些什么,他们永久都不会明白的。”
这句话出自边远的偶像Jim Morrison的大门乐队那首《People are strange》,作为“27岁俱乐部”(注释1)的一员,Jim Morrison的生平虽然短暂但非常闪耀,他不仅是摇滚音乐史上的明星,还出版过两本诗集,导演过一部电影,写作电影剧本。
(Jim Morrison)
注释1:
27岁俱乐部:是一个盛行文化观点,指一群去世于27岁的、主要的摇滚音乐家。个中最著名的三位是吉姆·莫里森、吉米·亨德里克斯、贾尼斯·乔普林。
大门是60年代最主要的摇滚乐队之一,他们的音乐领悟了布鲁斯、重金属和东方神秘主义,加之莫里森充满文学性的歌词,让大门身上有一种酒神的狂欢与悲剧的惨淡感共存的气质。
显然这种气质也影响了后来的Joyside,造就了他们本日充满文学性的表达。不过虽然在歌词里写满了宇宙星空火焰,但他们的骨子里依然是朋克的。,带着一种游走在危险边缘的陶醉和迷人。
他们的浪漫是从缭乱的出租屋,买不起的好酒、一站一站的绿皮火车……那些不被天下理解的青春中成长出来的,带着薄弱、孤独和叛逆,以是也一定吸引相似的灵魂。
02
做各种类型的音乐,那便是没事干呗
我第一次看Joyside的现场演出是2019冬天,舞台上的灯光暗淡下去,一颗粉色的心脏在阴郁中缓缓跳动,舞台上写出了那一句:Joy will always be your side。
(拍照:我自己)
那一场演出是令人冲动的,在《fire》这首歌里,乐队设计了一个空拍,舞台的灯光都熄灭了,天下安静下来,一片漆黑中只有自己的声音变得最为清晰。接着音乐又起,灯光重新亮起来,就像时隔十年重新回到舞台的他们一样。
只管我可能永久都无法理解老乐迷们那种在台下看着台上人和自己一起度过青春再一起经历人生逐渐老去的心情,但那场演出让我感想熏染到了一种唱片难以传达的生命力。
今年在知道Joyside要去乐夏的时候,我最早是非常愉快的。但在节目播出后,乐夏中的Joyside再也没有让我感想熏染过现场的那种心动。节目组彷佛一贯在试图消解Joyside与酒神相连的那种狂欢的激情和颓废的浪漫,把他们拉回大众娱乐的天下。
从第一次在乐夏亮相,大张伟调侃边远在唱《太空浪子》时候撒的是不是瓜子;
到和miumiu的互助赛把现场的舞台魅力全部归功于没有人能抵抗对小孩的喜好。
再到反反复复聊得都是当初为什么终结,现在为什么重组。
我不知道在乐夏节目组的眼中Joyside是不是便是一群爱饮酒的忘八,以是每天想着各种方法怎么能让他们乖乖听话,乐夏展现出的Joyside总是带着一种软弱无趣的正经。
直到我把稳到在乐队我做东里马东和其他乐队谈天时提到边远见告他分开的十年自己一贯在做不同的音乐,马东说:“我想这不便是没事干吗?”说完,抚掌大笑,节目后期还在此处给他加上了“总结到位”几个大字。
看着那个充满综艺感的欢快镜头,我的真的挤不出一点笑颜,乃至开始有些难过。
03
后浪漫时期的silly boy
十年之后,Joyside在乐夏的舞台“最在意的人”这个赛段又唱起了这首他们的老歌《Silly Girl》,这也险些是这个节目播到过半,他们第一次独自演出自己的老歌。
Joyside选择这首歌的情由非常大略,便是由于在意女孩子,想要给女孩子写歌。
只管这个版本的《Silly Girl》比较之前的现场要精细华美了很多,但至少是比较放松的。而每次Joyside在舞台上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以为忽然间忘却了韶光,忘却了他们的年事,在音乐的时空里,青春彷佛是可以永驻的。
但这场比赛Joyside拿到的大众乐迷评分并不高,或者说,从Joyside一开始在乐夏亮相,关于“摇滚之王”徒有浮名的争议就始终存在。这个天下存在一个保质期的彷佛不但是王家卫电影里的凤梨罐头,还有silly boy身上的那种浪漫。
在漫长的生平中,保持浪漫是一件很难的事。在Joyside上乐队我做东时,马东提问他们假如有一天醒来创造天降一个亿,会怎么利用这笔钱的时候。
刘昊说要把这笔钱给他父亲,让他知道自己儿子有出息,或者去做慈善。
像是转了一个圈,十年前那个穿着皮衣站在胡同里说家人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们也不能理解我的刘昊,彷佛还在纠结这件事,但是他从
虹位说要拿这笔钱去成立一个基金,让一个亿运作成十个亿,就像他过去十年一贯在为之努力的买卖一样。
只有边远的回答最不着边际,他说他要雇个人开着敞篷车客岁夜街上撒钱,一个城市撒上一百万那种。
这十年的韶光彷佛从来没有浸染在边远身上一样,他还是那么异想天开,但过去的十年里边远过远算不上世俗标准上的“幸福”。
他在酒吧当过做事生,从此再也不往烟灰缸里吐口喷鼻香糖,由于太难清理;
他组了很多不同的乐队,末了开始一个人写歌出唱片;
他在北京住了很多很多地方,以至于自己常常调侃某某地区是边远故居;
为了去见父母的时候让自己看起来“正常点”,他按照自己的理解穿了一身像中介一样的西装……
在边远身上,你总是能感想熏染到一种为了自己的浪漫心甘情愿耐劳的勇气。哪怕是在这个silly boy已经成为综艺节目的一个笑点。,“浪漫”已经可以用各种物质去包装的“后浪漫”时期,他依然是个浪漫的人。
一位朋友曾和我说:“这个天下是那么不浪漫,而我们却是那么浪漫的人。”后来我把这句话写成了这个公号的slogon:“我们不能停滞浪漫”。
愿我们在这个时期都拥有浪漫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