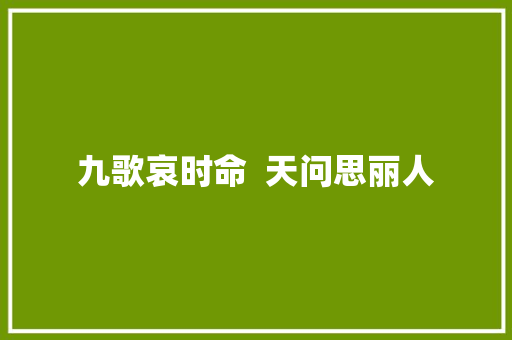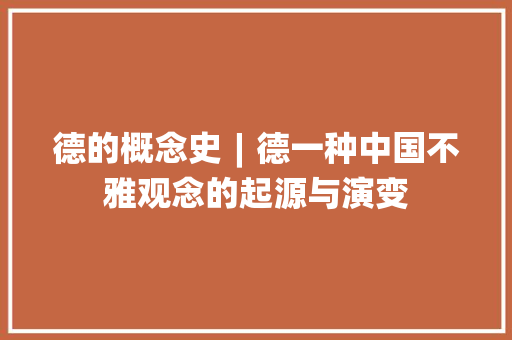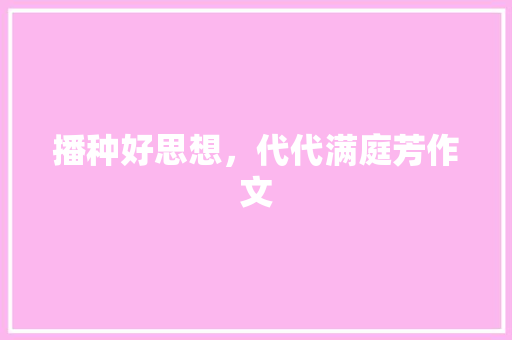择要: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道义”与希腊哲学家所说的“正义”有着相同的意义。道义不雅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商末周初,到了春秋期间,道义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主题。先秦儒家在继承春秋期间人们的道义不雅观念的根本上,对道义问题做了系统的理论阐释。先秦儒家的道义论表示了思想家对付优秀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追求。先秦儒家把道义原则理解为社会政治生活必须遵照的法则和代价判断的标准,强调道义原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优先性,认为只有符合道义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由于玄学素养的相对不敷,先秦儒家紧张通过履历性的历史过程来理解道义原则,在很长的韶光里,他们把“道”等同于“先王之道”。先秦儒家试图通过先王来解释道义原则是至高无上的,但却无法在普遍一定性的层面上实现对“道”的理解;同时,也使得儒家政治思想带有了浓重的复古情趣,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汉魏往后的儒家。
道义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历代思想家对付这一问题的认识以及在此根本上形成的道义理念,表示了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层面的理解,也代表了不同历史期间人们的代价取向。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说的“道义”与古希腊苏格拉底哲学的“正义”是意义相同的观点,但在以往的政治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对希腊哲学中的正义理念予以了很多的关注,却很少提及传统儒家的道义论。事实上,先秦儒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比希腊哲学家还要早些。生活在春秋战国期间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先秦儒家,在接管以往的道义不雅观念的根本上,形成了内容完备的道义理念。先秦儒家有关道义问题的认识,从根本上决定了秦汉往后儒家伦理政治学说的发展路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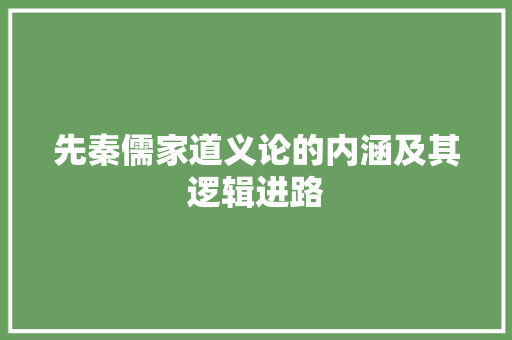
一、道义观点的源流与先秦儒家的理性
把握中国古代道义不雅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商末周初,这一不雅观念是伴随着人们对付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当性的认识而萌生的。从《尚书·洪范》所说的“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以及西周初年统治者提出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主见来看,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正当行使权力的问题。到了春秋期间(1),如何使社会政治生活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逐渐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其表现便是“道”和“义”成为人们频繁利用的观点。
由于措辞方面的缘故原由,“道”与“义”在最初是被当作内容上既有差异又有联系的观点分别利用的。从《左传》《国语》等有关文献的记载来看,春秋期间的人们对这两个观点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理解,在这一期间人们的不雅观念中,“道”和“义”都具有规则的含义。关于“道”,据《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随国大夫季良曾说:“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郑国大役夫大叔曾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里所说的“地之义”,也是把“义”看作人们该当遵照的规则。
“道”和“义”被理解为社会生活所应遵照的原则,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看作是代价判断的标准。春秋期间的人们认为,只有符合“道”和“义”的生活才是有代价的生活,而违反“道”和“义”的社会生活状态或者个人行为便是“无道”或者“不义”;“无道”“不义”的行为不仅在道德上是不可接管的,而且人们也相信,“不道”“不义”必将招致不良的社会后果,即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春秋期间人们的不雅观念中,“道”和“义”这两个观点也有细微的差别。在对“道”的理解方面,人们每每把“道”和“天”联系在一起,进而有了“天之道”的不雅观念,如《左传》哀公十一年有“盈必毁,天之道也”;又如《左传》文公十五年记载,鲁国执政大夫季文子曾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这表明,人们在利用“道”的观点时,强调的是“道”的客不雅观一定属性。与“道”的观点相较,“义”在大多数情形下不是具有客不雅观一定意义的观点。据《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解扬曾说:“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落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把“义”与君主能够“制命”联系在一起,把“信”解为臣下能够“承命”,表明当时人们在是特定的人际关系中来理解“义”的观点的。在这里,“义”虽然也是人们该当遵守的道德规范,但它所指的是特定人际关系下行为的适当。
由于“道”和“义”这两个观点的上述差别,当它们被用来解释人们的行为是否正当的时候,也隐含着不尽相同的逻辑。由于“道”是更具客不雅观性的观点,其本身便意味着绝对意义的正当,它既可以用来解释整体的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即所谓“天下有道”(《左传》成公十二年),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个人行为是否正当,例如称某一国君“有道”或者“无道”。而“义”则不同,由于“义”不是绝对的客不雅观原则和尺度,有关“义”与“不义”的判断,常日都要放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加以阐明,如“君义臣行”(《左传》隐公三年)。同时,“义”与“不义”的判断也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权衡,如前面引述的:“信载义而行之为利”,《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又有:“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左传》中“义”与“利”“信”联系在一起的议论多见,这表明,春秋期间的人们在把“义”做为代价判断尺度的时候,紧张是出于对行为主体间的适当性的考虑。
虽然春秋期间的人们已经对“道”和“义”有了基本的理解,并且在此根本上形成了较为朴素的道义不雅观念,但是,由于这一期间的人们对“道”和“义”的分别利用和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他们对道义问题的抽象理解。春秋期间的人们虽然常常用“有道”“无道”“义”“不义”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详细行为做出判断,但却很少就“道”和“义”的观点做出阐明。由于短缺对观点定义的把握,在这一期间人们的不雅观念里,“道”和“义”还不是普遍意义的道德法则。当先秦儒家开始谈论道义问题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便是这样的思想条件。这决定了先秦儒家一方面要遵照春秋期间人们对“道”和“义”观点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在更抽象的水平上实现对道义观点的把握。
沿袭以往人们对付“道”和“义”观点的理解,先秦儒家虽然大多是分别利用“道”和“义”的,但较之以往,先秦儒家的一个主要进步,便是他们开始考试测验为这两个观点给出自己的定义。关于“道”,《说文》阐明:“所行道也”,《说文》为汉儒所作,但其释义却是本于先秦儒家。关于“义”,《礼记·中庸》阐明:“义者,宜也”,唐人孔颖达阐明说:“宜,谓于事得其宜即是其义,故云‘义者,宜也’”,这一说法符合《中庸》的原意。这是古代中国人最早为“道”和“义”给出的定义。
在对道义观点的理解方面,先秦儒家更故意义的进步,是他们把客不雅观一定的含义授予了“义”的观点。孟子说:“仁,民气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在另一处,孟子又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孟子所说的“义”已不仅仅是“适当”,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了客不雅观法则的含义,也便是说,符合“义”的行为既是适当的,也是符合客不雅观法则的。
当战国儒家把“义”也理解为具有客不雅观一定性的观点时,“道”和“义”之间的差别也逐渐变得不再主要。到了战国晚期,便有了把“道”和“义”合并在一起来利用的环境。荀子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荀子·修身》)《周易·系辞》也有“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的说法。虽然按照传统的说法,《易传》为孔子所作,但从其行文与思想内容来看,成书年代该当不会很早。“道”和“义”这两个观点被合并利用的环境,预示着人们对这两个观点的理解愈益趋近,更为看重这两个观点共有的“规则”含义。
通过“道”和“义”观点的定义,先秦儒家在更抽象的水平上理解道义问题成为可能。虽然在许多时候,先秦儒家所说的“道”,如“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上》)都是详细的“道”,但有些时候他们所说的“道”和“义”也应被理解为抽象的观点。例如,孔子每每说“天下有道”,“天下无道”,在评论齐、鲁等国的政治生活质量时,孔子又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壅也》)。对这句话,朱熹阐明说:“道则先王之道也”(《论语集注》)。实在,朱熹的说法并不符合原意,在这里,“道”该当是抽象的观点。此外,孔子也常常说到“义”,如“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在这里,“义”也是抽象的观点。
当“道”和“义”被理解为抽象的观点的时候,人们便考试测验分开社会生活中的事实来解释道义原则。据《论语·学而》记载,孔子的学生有若曾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对付这句话,自朱熹往后,历代注家大多做了缺点的阐明。如朱熹《集注》说:“信,约信也;义者,事之宜也;复,践言也……言约信而合其宜,则言必可践矣。”杨伯峻师长西席的《论语译注》也把这句话译为:“所守的约言符合义,说的话就能兑现”,(2)实在,“复言”是春秋期间的习语,其意为出言反复,《左传》僖公九年记载,晋国荀息说:“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又据《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叶公说:“吾闻胜也好复言,……复言,非信也”,便是这方面的例证。有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信靠近于义但并不是义,有些时候诺言是可以不履行的。这是由于,信守诺言是社会生活中的详细行为,而“义”是规范社会行为的一样平常原则,“义”可以用来解释取信的行为是否正当,但却不可以反过来用老实取信来解释“义”的原则。到了战国期间,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意亦如此。
遵守道义并不即是信守诺言,古希腊思想家也有与此附近的认识。柏拉图的《空想国》有一段关于正义是否便是“有话实说”“有债照还”的议论,“譬如说,你有个朋友在头脑正常的时候,曾经把武器交给你,如果后来他疯了,再跟你要回去,任何人都会说不能还给他。如果竟还给了他,那倒是不正义的。把全体真实情形见告疯子也是不正义的。”(3)这与有若的那句话有着相同的意义,这表明,在东西方的思想家对道义或者正义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把道德原则与详细的社会行为分离开来是他们的共同努力。
把“道”和“义”理解为抽象的观点,对付先秦儒家来说尤其主要。思想家把“道”和“义”的观点从详细的社会条件下抽象出来,从而分开对道义原则的相对性理解,在这样的思想过程中,道义原则才有可能被理解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只不过由于玄学素养的相对不敷,这一思想过程并没有在先秦儒家那里得以完结。但是,对付中国传统道义理念的发展,先秦儒家已经迈出了十分主要的一步。
二、先秦儒家对道义原则的理论阐释
在先秦儒家走上历史舞台,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层面进行思考之前,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紧张是在道德习俗的规范下运行的。人们对道德习俗的遵守更多的是由于习气。虽然春秋期间的人们已经形成了朴素的道义不雅观念,但是,为什么要拥有符合道义的社会生活,道义原则之于社会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符合道义的生活,对付这些问题人们还未能给出合乎逻辑的回答。于是,对道义原则的理论阐释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先秦儒家的任务。
在春秋战国期间,对“道”的观点有着深刻理解的不止儒家,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学派便曾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对“道”做了论证。“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十五章)在道家那里,“道”既是物质天下的本原,又是规范物质天下的根本法则。就对普遍一定性的关注而言,道家对“道”的理解是先秦儒家所不及的。但是,道家学派在强调“道”的普遍一定属性的同时,却认为“道”与现实的伦理生活原则是根本对立的,“大道废,有仁义;聪慧出,有大伪;六亲反面,有孝慈”。(《老子》第十八章)道家学派认为,要实现与“道”相符合的社会生活,就必须放弃人类在既往的生活实践中得到的全部文明成果,即所谓“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由于不承认作为普遍法则的“道”与人类社会伦理原则之间的联系,在如何匆匆进社会生活质量,担保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当性这一问题上,先秦道家没有给出可靠的答案。
与道家学派相反,先秦儒家强调道义原则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试图通过现实的社会生活对道义原则做出阐明,“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在先秦儒家看来,道义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原则是同等的,符合道义的生活得以实现的路子,不是放弃既有的道德习俗和伦理原则,而是伦理原则的完善。
人们不仅该当拥有符合道义的社会生活,而且符合道义的社会生活也是完备可能的。这种可能性,或者如孟子所说,源自于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或者如荀子认为的那样,在人的道德自觉不敷依凭的情形下,通过礼义约束与道德教养得以实现。虽然先秦儒家对付人性善恶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是他们都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道德前景充满希望。因此,他们也自觉地承担起了在理论上阐释道义原则的理论任务。
先秦儒家认为,道义是规范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原则,在社会生活中,道义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乃至要比人的生命更为主要,如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战国末年的荀子也说,“荣辱之大分,安危短长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荀子·荣辱》)道义原则具有绝对的优先性,是先秦儒家的同等认识。
道义原则谢绝利益的权衡,“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荀子·荣辱》)先秦儒家尤其重视义利之别,他们把对待义、利的态度当作判别君子与小人的根本标准。《论语·里仁》记载孔子的话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清朝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引用范氏的话:“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度仁义,则为小人”,这一说法十分准确,所谓“晓货利而度仁义”,便是用利益的得失落来权衡道义原则,这是先秦儒家武断反对的。
先秦儒家不仅用道义原则判别君子、小人,同时,也把道义原则当作判断社会政治生活善恶良否的标准,符合道义的政治为“王道”,反之便是“霸道”,“王道”是他们所能理解到的尽善尽美的政治生活。先秦儒家认为,践行“王道”是统治者无可推脱的道德任务,而“王道”政治的关键则是统治者以正当的办法得到权力和行使权力。先秦儒家认为,相对付“功利”,道义原则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如果违反了道义原则,任何成功都是没故意义的,“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先秦儒家虽然强调道义优先,但他们并不完备否认统治者在政治上得到成功的意义,在他们的不雅观念中,符合道义的政治本来就该当是成功的,只不过“成功”要以合乎道义的办法来实现。先秦儒家之以是谢绝承认春秋期间的齐桓、晋文为“王道”,便是由于在他们看来,齐桓、晋文实现霸业的办法不符合道义。纵然儒家创始人孔子有些时候对管仲、齐桓公的霸业也有所称道,但在主导的方面,先秦儒家在道德层面上对齐桓、晋文为代表的五霸是否定的。到了战国期间,荀子和孟子都不谋而合地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孟子·梁惠王上》)。至于儒家学派何以不谈春秋五霸,荀子说出了个中的道理:齐桓公虽然“有天下之大节”,是“五伯之盛者”,但却“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春秋五霸不过是“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荀子·仲尼》)先秦儒家用道义的不雅观点判别好的政治与不好的政治的时候,他们也谢绝了却果主义的考虑。
符合道义的政治也哀求统治者以合乎道德的办法对待民众。由君主专制的政治系统编制所决定,中国古代的国家不是公共意义上的国家,在古代中国人的不雅观念中,统治者对国家的管理便是“治民”。由于这一缘故原由,先秦儒家十分重视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办法。孔子在评论春秋期间郑国的政治家子产时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这之中,“养民也惠”“使民也义”,所强调的便是统治者善待民众的任务和责任。到了战国期间,孟子主见统治者该当施行仁政,而荀子则主见实见礼治,荀孟的主见虽然不尽相同,但在推崇“王道”、反对暴政这一点上却是同等的。
由于对符合道义的政治生活的强烈追求,先秦儒家深切关注民众的生存条件。在他们看来,改进民众的生存条件,至少该当不使民众生存条件恶化,是统治者无可逃脱的道德任务。春秋末年的孔子曾呼吁统治者对付民众该当“富之”“教之”,战国期间的孟子则认为,使民众“养生丧去世无憾”,便是“王道之始”(《孟子·梁惠王上》)。战国晚期的荀子更认为民众富余是国家富强之道,“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主见统治者该当按照礼的规定征取赋税。《大学》更直截了当地提出,专制国家不能与民众争夺财利,德为本,财为末,因此管理国家不应该以谋取财利为目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荀子以及《大学》的思想主见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社会财富该当如何分配的问题,虽然他们所理解到的分配原则远不是当代意义的“公正分配”,但就他们所生活的历史时期而言,反对专制国家与民争利,谢绝统治者把攫取财富作为国家管理的目的,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先秦儒家道义论的逻辑进路及局限
在逻辑上说,我们之以是认为在社会生活中该当遵守某种道德原则,是由于在我们看来那些原则具有绝对的主要性。当先秦儒家倡导道义原则的时候,他们也须要解释道义原则对付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性。按照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习气,便是要用普遍一定性的不雅观点对道义原则做出阐明,从而解释道义原则既是至高无上的,又是普遍的和永恒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近代思想家所说的“绝对”。事实上,先秦儒家在理论上阐释道义原则的过程,便是在不雅观念天下里把他们所认可的道德原则推向“绝对”的过程。
先秦儒家有关道义原则的客不雅观性论证,紧张表示在对“道”的理解上。为相识释“道”是人们必须遵照的普遍法则,先秦儒家所做的紧张努力便是为“道”找到一个神圣的来处,进而解释道义原则的至高无上属性,这是孔子及其身后孟子和荀子的论证逻辑。
为了证明“道”是至高无上的普遍法则,先秦儒家把“道”还原到履历性的历史过程中加以阐明,把“道”归结为“先王之道”。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到了战国期间的荀子,则更进一步说:“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以是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儒家所说的“先王之道”是一个含义颇多的观点,它既是先王留下来的治国履历,也是先王所奉行的治国原则。先秦儒家认为,“先王之道”不仅是先王以是成功的缘故原由,而且也适用于他们所生活的时期,只要以先王之道治国,便一定会实现天下大治。“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弗成先王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先王之道”可以为万世效法。
先秦儒家论证道义原则的逻辑十分大略:作为普遍法则的“道”来自于先王,由于以尧舜文武为代表的先王是神圣的,以是“道”也是至高无上的。这种推崇先王的思想办法,实际上根源于远古时期先人崇拜的习气。商代后期甲骨卜辞中卜问先人的记载表明,当时人们是把先人当作神明来看待的。商王盘庚在向臣民陈说迁殷的情由时以“古我先王”为说辞,《尚书》中保留的西周初年文献也有许多文、武膺天受命的说法。先秦儒家把道义原则托于先王,与远古期间的先人崇拜的习俗是一脉相承的。由于先秦儒家不像道家那样从本体论的层面来理解“道”,先王便成为他们能够为“道”找到的最神圣的来源。可是,当先秦儒家把作为普遍法则的“道”还原到履历性的历史过程中去,把“道”等同于先王之道的时候,也在故意无意间遭遇了无法战胜的理论困难。
首先,先秦儒家把“道”等同于先王之道,使得他们无法在普遍一定性的层面上对道义原则做出阐释。先秦儒家忽略了一个至关主要的问题,那便是他们所说的“先王”,是一个从尧舜至文武的十分宽泛的观点。可是,这些“先王”所处的历史时期各不相同,他们的治国履历和原则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详细实践,于是,如何通过先王的详细实践来解释道义原则的普遍性,这本身便成一个问题。事实上,当先秦儒家说“百王之道,一是矣”(《荀子·儒效》)的时候,他们也意识到每一个先王都有各自的特点。那么,往古先王之中哪一个才真正值得效法,便成为儒家学派内部辩论不休的问题。对付这个问题,孔子给出的答案很是模糊。孔子用损益的不雅观点阐明三代以前的历史,以为西周是最好的历史时期,但他又以为尧舜时期才是真正美好的时期,以为尧时的“韶乐”尽美尽善,而西周期间的乐曲“大武”却是“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尧舜、文武,哪一个时期的政治更好,在孔子那里是没有确切答案的。这一问题延至战国,便有了孟子、荀子之间“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辩论。孟子“言必称尧舜”,把尧舜当作先王的空想样本,而更晚一些的荀子则认为“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观观。”(《荀子·王制》)如此见地不合,正好表明了先秦儒家在理解道义原则的普遍性方面所存在的理论毛病。
其次,先秦儒家把“道”理解为“先王之道”,使得他们所倡导的道义原则无法有效地约束现实的政治生活。如何约束现实生活中的权力,是东西方思想家共同面对的主题。实在,先秦儒家用“先王之道”来解释“道”的观点,通过先王的神圣来解释道义原则的至上属性,这一做法是很有深意的。他们的主不雅观意图是要使道义原则对现实的政治生活具有可靠的约束力。而道义原则对现实生活的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示为对君主权力的约束。可是,先秦儒家却忽略了至关主要的一点,商周以来的人们强调先公先王的神圣性还别有另一方面的含义,那便是,先王的统统都是由今王继续的,即所谓“正体于上”(《仪礼·丧服》)。在逻辑上,今王是代理先王管理国家的,以是,先王的神圣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现今统治者的神圣。如果说“道”是先王留下来的法则,而今王却是先王权力的继续者。这样,君与“道“便有了共同的来源,二者之中哪一个更具至上的属性,便成为逻辑上难解的问题。事实上,在先秦儒家身后,历代儒家一贯环绕君道关系这一问题辩论不休,直至宋明之期间,也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足以服人的答案。如此看来,先秦儒家把“道”等同于“先王之道”,为道义原则设定了“先王”这一貌似神圣的来源,却在故意无意中消解了道义原则的至上性。这是先秦儒家未曾意识到的。
再次,先秦儒家通过履历性的历史过程理解道义原则,使得先秦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具有了浓重的复古方向,这在根本上影响了儒家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代价判断。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思想家对道德原则的理论阐释,总是要涉及到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应然性判断。思想家在若何的程度上理解了道德原则,也就会在若何的程度上对该当的政治生活做出判断。先秦儒家理解道义原则的目的,终极也是要对他们所理解到的空想的政治生活做出解释。
在每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家那里,空想的政治生活都是根据其所认定的道德原则所做的构想。以是,历史上的思想家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应然判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乌托邦色彩。古希腊的柏拉图便坦白地说到,他所设计的完美无缺的城邦不过是一种理念,这种城邦“无论在希腊还是在希腊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得到。(4)作为理性思维的结果,空想的社会政治生活只是存在于人们的不雅观念天下里。可是,当先秦儒家把道义原则理解为先王之道的时候,他们在认识上便走进了一个误区。在他们看来,他们所追求的空想的政治生活虽然与现实的政治生活迥然有别,但空想的政治生活并不是纯粹的主不雅观想象,而是既往历史过程中的真实存在,先王统治的时期便是空想社会的原型。实现空想的社会政治生活,无非是规复那些曾经的历史片断。于是,“复古”便成为儒家学派共同的思想方向。就代价指向而言,先秦儒家所关注的无疑是社会未来,但在理论上他们却要把社会推神往古,这不啻是荒诞的逻辑怪圈。先秦儒家的复古方向深深影响了汉魏往后的历代儒家,人们对空想社会生活的追求愈是强烈,对现实的政治生活的批驳愈是年夜胆,其复古情趣也就愈是浓重。直到明清之际,人们也仍旧没有从这种复古情趣中走出来。
一样平常地说,古典时期是本体论哲学盛行的时期。思想家的哲学思考大多是从对宇宙本体或者终极缘故原由的追问入手的,古希腊以泰利士、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以及苏格拉底期间的哲学家大抵如此。本体论哲学在春秋战国期间紧张是在道家的思想学说中表示出来的。先秦儒家之以是诉诸于履历性的历史过程,用“先王之道”来诠释作为普遍法则的“道”,一个主要的缘故原由是孔子以及战国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没有养成形而上的思维办法,这使得他们无法用逻辑的办法对道义原则做出论证。以是,通过“先王之道”来解释作为普遍法则的“道“便成为先秦儒家无奈的选择。然而,这种诉诸于履历性的历史过程的论证逻辑,显然无法知足在更抽象的水平上理解道义原则的须要,这决定了儒家本身也一定要从这种论证逻辑中走出来,从诉诸于履历的论证逻辑向玄学的论证逻辑转换。事实上,这种转换在战国后期已经发生了,《礼记·中庸》有关“道”的普遍一定属性的认识以及《易传》在本体论层面上对“道”的解释便是其详细表示。
关于“道”,《礼记·中庸》开宗明义地说,“定命之谓性,任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朱熹《集注》阐明说:“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朱熹这段话显然加入了他自己的理解,战国儒家的认识能力并没有达到这一认识水平,不过,《中庸》的作者分开“先王之道”来解释“道”,在“定命”“性”与“道”这些观点之间建立起了某种逻辑关系,无疑比孔子、孟子、荀子更进了一步。
与《中庸》一样,《周易·系辞》的作者也看重对“道”的普遍属性的把握,并且从本体论的层面上对“道”做出了玄学的阐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系辞》所说的形而上之道实际上是被当作天下的终极缘故原由看待的,它既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也是善的来源,世间万物的属性也是通过“道”得到的,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系辞上》)由于“道”决定着世间万物的属性,它也决定着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秩序。“道”是至高无上的普遍法则,不是由于发轫于先王,而在于它是天下的终极缘故原由。
《周易·系辞》的玄学思想是先秦儒家原来没有的。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周易》的玄学思想源于道家,《易传》是深受老、庄和黄老学派影响的作品(5),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不过,须要澄清的是,只管《易传》的玄学思想可能与道家存在某种联系,但并不能由此断定《易传》是道家学派的作品,由于《易传》的道德关注是道家学派所没有的。《易传》的涌现,实际上是儒家有关道义问题的论证逻辑发生转换的标志。
在春秋战国期间的思想家群体中,儒家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有着强烈的关注,但囿于诉诸于履历性的历史过程的论证逻辑,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以及荀子却短缺在抽象的水平上对道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中庸》以及成书于战国后期的《易传》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用“先王之道”来理解道义原则的理论局限,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接管了源自于道家的玄学思维办法,它预示着儒家的道德关注与玄学的思想办法相结合的趋向,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也将随着二者的结合而开启哲理化的进程。可以说,先秦儒家在道义问题上论证逻辑的转换,是儒家伦理政治学说哲理化进程的出发点,只不过,由于思维水平的限定以及社会历史环境的变革,这一转换过程并没有在先秦儒家那里得以完结,这一任务只能留待汉魏往后的思想家去完成。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