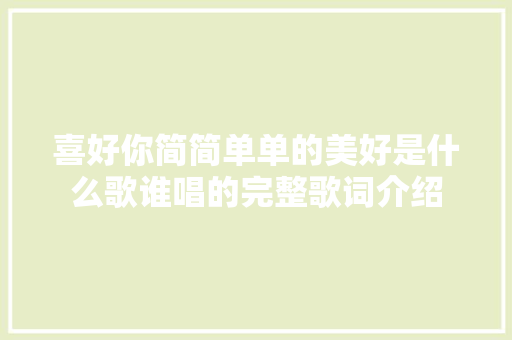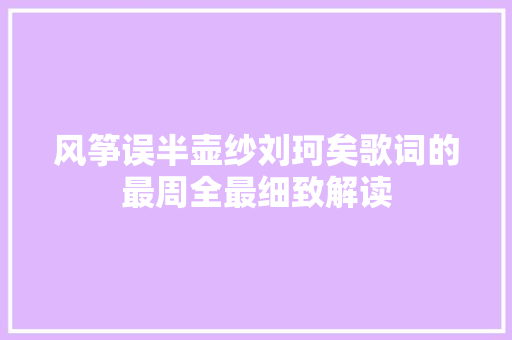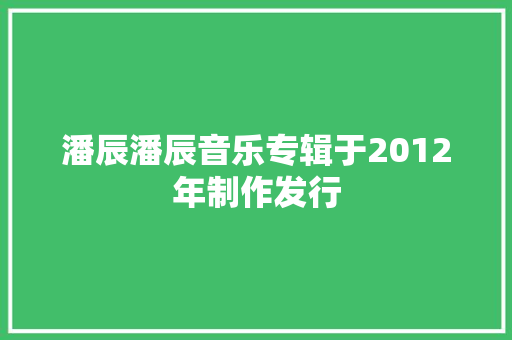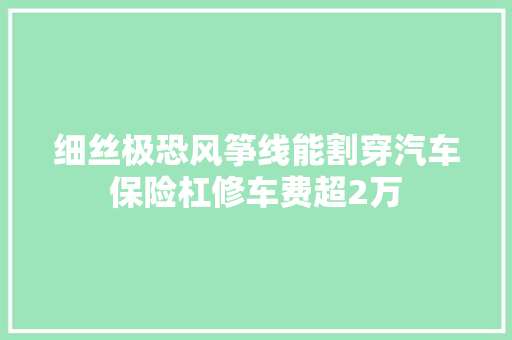鹞子来自地摊,地摊摆在广场一角,品种不多,只三五种。我问中年人:何不自己动手来扎?回答:说随意马虎,动手却难。都能动手,这鹞子咋卖?说得也是,想想从前自己也算扎过鹞子,累加起来也有一堆,但许多飞不起来,能飞好的寥若晨星。
这么想着,也就信手买只来玩。薄暮的风很轻,却能送鹞子扶摇而起。天空明净,鹞子斑斓,俊秀如画,充满灵动。卖鹞子的男人见我不像生手,说一看你就玩过。我说:儿时玩过,相隔多年,手生了。边谈天,边把鹞子放起来,无意中顺便也不雅观察一下周边的鹞子人群,一看,除孩子便是老人,中青年人不多。

玩鹞子的老人,手艺多是打小学的,想起梁实秋《人生,没有太晚》里的话: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鹞子,“偷闲学少年”,那自然有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半老徐娘,留着“刘海”,躲在茅房里穿高跟鞋当作踩高跷般练习走路,那也是惨事。便以为梁实秋看事还是准的。
小鹞子,大乾坤。听说曹雪芹也曾迷恋过鹞子,《南鹞北鸢考工志》上就记录过他的鹞子制作与放飞;戏曲家李渔在《鹞子误》里写的儋氏两女,一美而才,一拙而陋,也是因的鹞子题诗各就的姻缘。
鹞子始于春秋,《武林往事》里记述过宋代鹞子;五代北朝齐宣帝曾用鹞子载过人,载人的鹞子最远一回跑出了五里地。
上世纪50年代,中法合拍过一部叫《鹞子》的电影,彩色的,儿童片,电影好看,我连看了三遍。表现天下、儿童与民族文化间沟通与理解的主题,载体是只鹞子,那鹞子在自得其乐的自然色中飞啊飞,飞得让我着迷。
春天,放鹞子的多,春季有风的天多,风力也相对大。里手说春天的风向上扬,冬天的风向下压。立春后,地表回暖快,但高空还坚持着较冷状态,上冷下暖随意马虎产生对流,上升的气流会把鹞子轻而易举地送到天上。
我把这道理说与中年人听,阁下一戴草帽的老夫人听了不服,说热天咋就不能放呢?鹞子之上无时节,有风就该能放的。这才创造她手里也扯了盘墨绿色的鹞子线。“莫说眼下秋到了,便是大热的三伏天,高兴了我也来放鹞子。”老夫人说自己都是一早一晚的来,这时的阳光弱,好有风,苦处拴在鹞子放出去,会感到人舒畅,心凉爽。
老夫人是个当老师的,说鹞子是老伴扎的,老伴八十岁了。老伴会画画,还会手工活,能恰到好处地把握鹞子构造与平衡。用的竹条,编个“三角”,用火烤过,骨架上抹糨糊,把画了明快颜色的纸面粘上,尾部再拴根布条当尾巴。
是个微风天,老夫人说:风小只放得小鹞子,风要上了三四级,大鹞子才能放起来。老夫人感慨:浅秋风筝知凉薄,鹞子之上乐趣多,热天不觉热,秋来凉先至,是妙不可言的消暑玩具。
夏末秋初,见过许多城市街头的鹞子,西安印象最深。地点钟楼前广场,是个初秋之夜,夜空里竟然飘满了鹞子,都是数米长的鹞子,造型有蜈蚣、蝙蝠,还有龙、凤、鱼、羊,都在寓意吉祥嘉瑞。分歧凡响的是鹞子上装了五颜六色的LED灯,一串串的亮就灿然挂在了天上。
那天,钟楼下与位鹞子老人谈天,聊愉快了,老人的“鹞子话”就细了,见告我为什么要选在晚上放鹞子,由于晚上的风平和,而清晨和晌午的气流乱,鹞子爬高是很费劲的。老人说这大美的秋光,鹞子都能看得到,一只鹞子能通报天地间的美好。看动手边大卷的线送完,老人就把鹞子的线拴到个石墩上,然后坐上石阶吸烟,阁下还有些鹞子人在喝茶。
我常会想,“鹞子人”真了不起,能把人间烟火与传光滑油滑事都周详精细地扎进了鹞子,再奇妙地将它拿去天涯演绎幻化,让民气头明净,寄望高处怀想。听说还有人在鹞子上装过弦、笛一类东西,风吹有声,音色其绝,在空中响过,生出别样意韵。(刘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