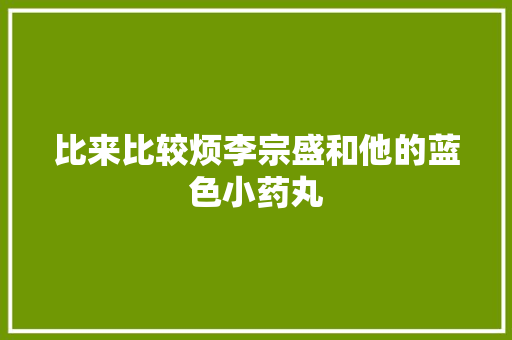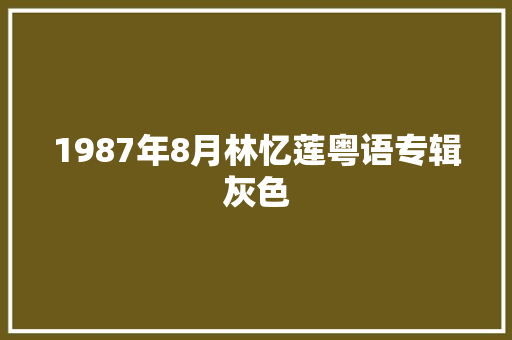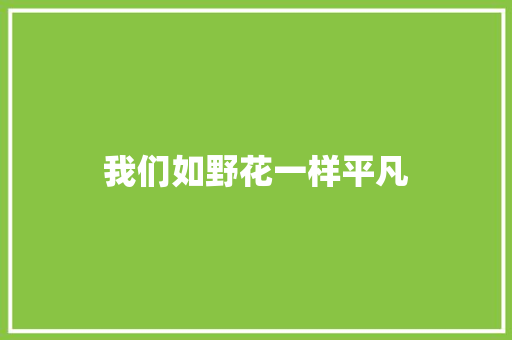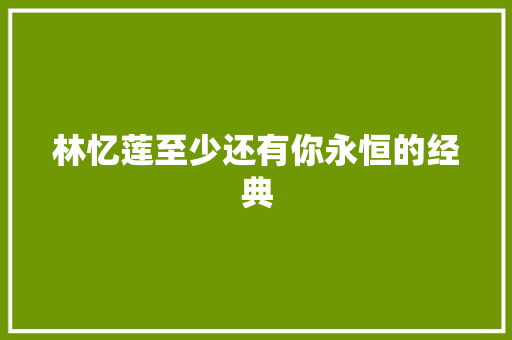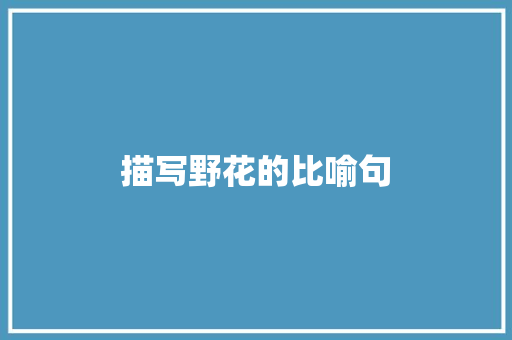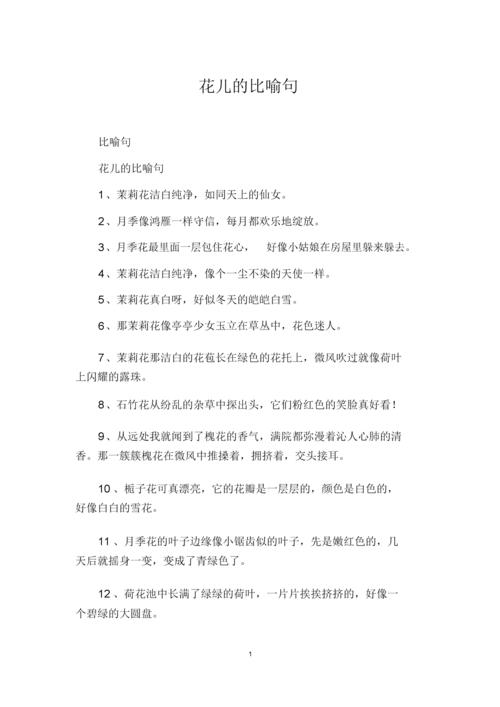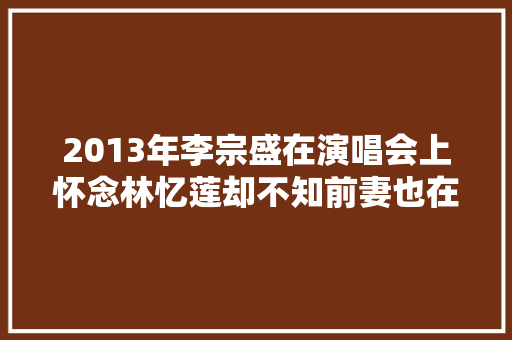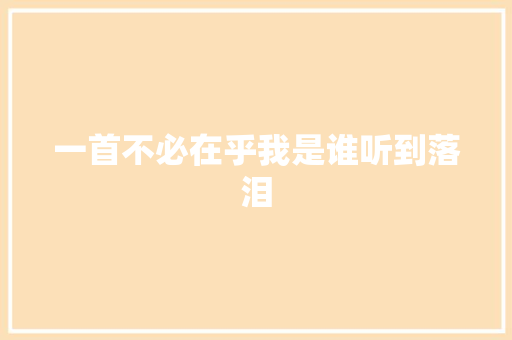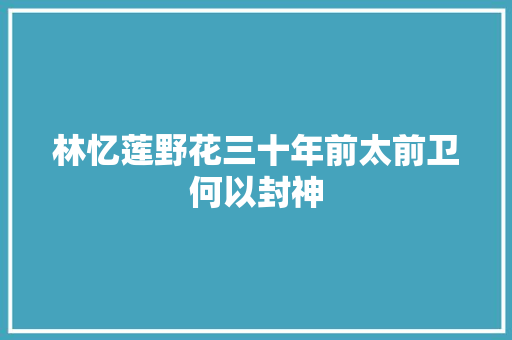1
朋友在日本留学,返国后递给我几本日文的音乐类图书。他那郑重的眼神我懂:这些书才是他真正乐意翻译的,而不是我先前替出版社向他邀约的那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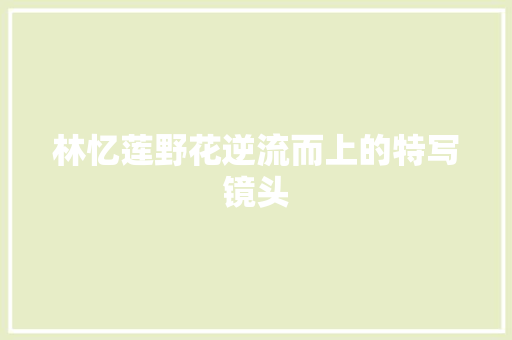
坦白说,朋友给我看的都是好书,可海内很难出版。先说《澤野工房物語》(DU BOOKS,2018年9月版),我估计中国大概没几个人知道日本有一个爵士乐厂牌叫“泽野工房”,如果问的是“三盲鼠”,该当会有不少老乐迷举手。至于“泽野工房”,至于这家位于大阪的鞋铺兼唱片店,它在海内的知情者大概少于三位数,而知道ECM的该当超过六位数。这也阐明了拉斯·缪勒[1]为ECM[2]编的画册为何能汉化,只管《风·落·之·光 ECM唱片的视觉措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版)一书的性价比很低。
位于大阪的泽野工房拥有鞋铺和唱片店的双重身份(图片来自泽野工房官网)
再看第二本,Chee Shimizu[3]编著的《obscure sound 桃源郷的音盤640選》(Rittor Music,2013年6月版),作者这天本DJ,在东京开了一家唱片店叫Organic Music。他于书中推举了各国各流派的冷门精品640张,这些唱片生僻到我举手屈膝降服佩服,在海内的流媒体平台基本也听不到。关于这类书,日本的出版界有一个专属的分类标签叫ディスクガイド(Disc Guide),犹如浩瀚碟海的一位导游,在日本还挺常见,但在海内的图书市场难觅踪迹。我念书时海内出过几本,为匮乏年代的乐迷供应了扶贫教诲,较为经典的作品如《激情歌诗:唱片典藏300张:摇滚乐篇》(文汇出版社,2000年4月版)、《爵士名盘300》(上海公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这两本书都没能重版,不过我能理解海内出版社对此的轻忽,这种书的策划做得太主流就成了一个加强版的豆瓣豆列,做得太偏门——如果我是编辑,在选题会上报了Chee Shimizu的书,估计领导会问:“你以为谁会买这本书?”我该当会答道:“骨灰级的唱片收藏家,还有富有探险精神的乐迷。”然后这个选题就被毙了。
Disc Guide这类书本在日本的音乐类图书里占了不小的比重,颇受乐迷欢迎(图片来自网络)
好了,在进入正题之前总结一下海内对出版当代音乐类图书的态度,归纳起来就看两个字——流量。我们能在市场上见到不少摇滚巨星的传记,爵士大师的为什么少,由于缺流量。“山羊皮”主唱布雷特·安德森(Brett Anderson)的两本自传《漆黑清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1月版)、《拉下百叶窗的午后》(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9月版)相继得到译介;但是他的同侪卢克·海恩斯(Luke Haines)很早之前就写了两本富于洞见的书,Bad Vibes:Britpop and My Part in Its Downfall、Post Everything:Outsider Rock and Roll这两本炭烧吐槽味的回顾录犹如Luke Haines的乐队The Auteurs,可说是1990年代英伦摇滚留给后世的珍宝,可海内搬不动,由于缺流量。海内的出版社在当代音乐这个视角里策划选题时还有一个问题,不喜好特写,偏爱远景,恨不得都是航拍,最好是《清明上河图》。以是市场呈现了不少通史简史,紧张还是在炒摇滚乐的冷饭。
在这种越来越伟大的背景之下,《林忆莲:野花》的出身就像是逆流拍摄的一个特写镜头。这是一本礼赞之书,作者蔡哲轩用了一整本的篇幅去探索、解析林忆莲揭橥于1991年的专辑《野花》。
卢克·海恩斯的两本书和The Auteurs都是1990年代英伦摇滚留给后世的珍宝
2
我认识蔡哲轩快要二十年了,这段岁月里,他向着“林忆莲研究第一人”的高度不断攀登;在我等朋友眼中,跟他聊林忆莲起初就像乒乓球民间高手寻衅上海市的全运会队员,近几年我已经不高兴跟他聊林忆莲了,由于这件事情变得跟马龙对决一样缺少悬念。而且蔡哲轩还是一个出了名的毒舌。他的名言包括:“如果谁还把music publishing(版权管理)翻译成‘音乐出版’,那么此人的文章该当忽略,出的书该当丢垃圾桶。”基本上,他在磋商音乐的时候是一个较真、好斗的猛士。
可我总也忘不了他的另一名言——当时我们在聊电影《探求小糖人》为何成功,他说:“好就好在导演不太懂音乐,如果他是音乐圈的行家那就难说了,如果他是罗德里格兹[4]的狂热粉丝,那这个电影肯定就砸了。”他的见地我完备赞许,以是当我知道他要写他最痴迷的林忆莲,而且是他最喜好的专辑《野花》时,我预估那会是一本曲高和寡的作品,不至于搞砸,但想要成功,也便是引发大众层面的共鸣,该当很难。
《野花》专辑的重版黑胶
三年后,等到我翻开《林忆莲:野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版),序言的第一页就把我逗乐了。果真还是熟习的配方,蔡哲轩是这样登场的:
这几年,彷佛只要谈到李宗盛或者林忆莲的时候,很多人就特殊喜好这样一句话:‘年少不懂李宗盛,终年夜方知林忆莲’。
“每次听到,我都很倾慕(质疑)说这句话的人,由于在我眼里,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那些歌,无一不是最直白最浅近的标准商业盛行曲(口水歌),要‘终年夜’才能听懂这些歌,只能解释这些人依旧还保有‘年少’心态(too young too naive)。(P1)
我要强调的是,引文括号内的笔墨纯粹是我的曲解,与蔡哲轩无关。让我惊异的是,这两段笔墨居然成了蔡式毒舌在整本书里的绝唱。蔡哲轩变了,唯一没变的是他对“老李”的不敬,但是他把这种感情掌握得颇为得体。“李氏情歌”一改往常在他口中毁誉参半的形象,在书中紧张扮演一名造神者(Queen-maker)。当然,“老李”作为已婚人士横刀夺爱的剧情也没少排演。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段笔墨:“关于《野花》,许愿[5]永久不会忘却自己在1988年的台北街头头脑一热捧着专辑坐上出租车奔去滚石唱片的那一幕——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自己把女友送到了她未来的丈夫手里。”(P63)
像这样叫人面前一亮的野史轶事,书中还有许多。我之以是称之为野史,是由于作者网络素材的管道略有瑕疵。正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言,他与许愿做了深度访谈,没能采访到林忆莲最是遗憾(P210)。
2019年11月26日,蔡哲轩去北京第一次采访许愿时留影
借由作者的笔墨,读者轻而易举就能走入许愿的内心深处,或者说,我们听到了许愿希望我们听到的那些话,有时候,我们因此许愿的视角在回顾那段历史。于是,许愿不仅是《野花》专辑的制作人,也成了《林忆莲:野花》这本书的主心骨,正如作者在序言里说的:“我在这本书里便不再过多地赞颂她那些人尽皆知的事,而把紧张精力放在《野花》专辑背后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企划,比如说制作,又比如说影响……”(P7)
企划、制作,都是许愿的事情。难怪读《林忆莲:野花》时,我总以为,仿佛身边一贯有许愿在督导。那种跬步不离的觉得恰如这段笔墨:“1991年夏天,林忆莲和许愿坐下来,开始谈论下一张粤语专辑的主题。当林忆莲对许愿说她要讲‘无根而流落的当代都邑女性’的时候……”在书中,这切实其实成了《野花》十二集电视连续剧的片头曲,一而再再而三地涌现。
3
同蔡哲轩聊音乐,他常用的修辞是“讲求”。比如我夸某某专辑不错,他有可能开沪语这样来接:“当然,制作得多少讲求。”
讲求也是一个适宜评价《林忆莲:野花》的词。蔡哲轩在书的构造上倾注了好些巧思,谋篇布局不乏精妙。这本书的主体由十二章构成,每章对应《野花》专辑的一首歌。比如《野花》的第一轨Wildflower Overture翻唱自加拿大乐队Skylark的名曲Wildflower,《林忆莲:野花》的第一章因故名为“序曲”,而且整章浓墨重彩地谈Wildflower的创作、走红,像是在为读者放映一部以1970年代、1990年代北美为背景的音乐记录片。当读者还在犹疑是不是读到错版书时,作者点破了谜局,原来他神神叨叨了许久的顶级制作人David Foster为喷鼻香港女歌手跨刀之疑云,这位David便是Skylark的键盘手,只可惜他没有选中林忆莲,而是挑了叶倩文。借此细节,《林忆莲:野花》的大幕缓缓拉开,故事也切换到了1991年的喷鼻香港。
1991年,当许愿与林忆莲敲定了新专辑的主题,他当即想到要把加拿大乐队Skylark的名曲Wildflower加进专辑
如此写法,显然是作者在刻意向《野花》致敬。他在序言里这样自陈:“这本书因此《野花》专辑的十二首歌的曲目为线索撰写的,以是它不是一本按韶光线性发展的书,或许这样的笔墨在阅读上会有些难度……”(P7)
有难度吗?我的意见是他这样处理倒是把大众读者伺候得很舒畅。毕竟对那部分读者来说,看小说要比啃学术论文来得轻松。我的意思不是作者故意迎合,他实在是把“追寻野花”的大故事切分成了五十三个与《野花》干系的小故事。五十三这个数字来自《林忆莲:野花》的小节总数,譬如第一章有三小节,第一节爬梳了名曲Wildflower的缘起,第二节钩沉了Wildflower的走红,第三节渲染了David Foster的喷鼻香港跨刀疑云。今后的章节也是如此,读者将会面对许多俨然独立的小故事,它们都在为林忆莲,为《野花》做事。就像一张专辑的出身,除了歌手,还须要词曲作者,须要编曲,须要乐器演奏,须要录音混音。
不得不说,这种写法除了在形式上与《野花》完成了美学对位,还非常讨巧,乃至可以说是狡猾。由于坦白讲,用一本书的篇幅只解析一张专辑原来便是很大的寻衅;《野花》专辑发生在1991年,试问1991年之前或之后的林忆莲能不能写?写了多少算是偏题?
蔡哲轩用十二个平行宇宙的构造奥妙地回避了这些质问,他的答卷具有样板房的示范意义。我在阅读《林忆莲:野花》时,常常惊叹于作者娴熟的多线叙事功力,我估计,这种能力或许得益于他之前翻译的一本书。在那本名为《音乐是怎么变成免费午餐的》(河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的非虚构精品里,作者斯蒂芬·维特动用了三条平行的叙事线来编排一个惊险刺激的侦查故事。
《林忆莲:野花》是一整本的专辑评论,却与传统的评论拉开间隔。作者把想要输出的洞见都融进了叙事,这种软着陆的评论可以称之为“叙事性评论”,很多时候,读者面对的不是一位评论家,而是一个开了天眼的说书人。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杰夫·戴尔的名著《然而,很美》。老辣的杰夫用小说式的虚构来评论七位爵士大师,那种奇特的文体也被他称之为“想象性评论”。
4
以下的笔墨是我对《林忆莲:野花》的想象性评论。在我的想象天下,这本书如果能够据此做一些修订,该当会更美。
他该当采访一下Dick Lee[6]。Dick Lee对《野花》的贡献实在太大,整张专辑,除了演唱者林忆莲,Dick Lee的出镜率最高,包办了半数的曲创作以及大量的编曲事情。作者在书中引用的Dick Lee的素材,大多来自Dick Lee的自传The Adventures of the Mad Chinaman(Times Editions,2004年8月版)。比起采访林忆莲,我以为采访Dick Lee的可行性更大,若能成行,新的战果可以在重版时弥补。
关于Dick Lee,还有一点鄙视法。在阐发《再生恋》的编曲时,作者写Dick Lee将“当代合成器和电吉他与来自印度的印度鼓……”(P123),“来自印度的印度鼓”读起来有点饶舌,不妨改成“来自印度的塔布拉鼓”。
参考文献的征引能否更为透明、严谨?书中有相称篇幅在写李宗盛,很多材料涌现时仿佛源自作者与老李的深度访谈,但事实并非如此。以是我难免会对那些材料的出处有所好奇。比如这段:“歌曲播完,主持人说:‘刚刚是辛晓琪的新歌《自私》,翻唱自英国女歌手贝弗莉·克莱文的Promise Me。’听到这句话,李宗盛才想了起来,那首和《自私》旋律一样的歌,名叫《没有你还是爱你》,出自林忆莲去年在喷鼻香港出版的粤语专辑《野花》——为了滚石能够签到林忆莲,也为了写《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把她之前所有的专辑都听了一遍。”(P172)
我还有一点苛求:这本书该当增加Index,把书中涌现的人物、乐队、专辑、歌曲做一个索引。
说到底,这些哀求因此欧美、日本的音乐类图书的规格来度量我国的出版物,而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好在这种差距正在缩小。最少我在《林忆莲:野花》这本书里感想熏染到了未来的乐不雅观。或许有一天,我那位留日的朋友能够翻译到贰心仪的那几本书。
注释
1.Lars Müller,瑞士设计师、独立出版人。
2.德国独立唱片厂牌。
3.日本著名DJ、唱片收藏家、作家。
4.Sixto Rodriguez,墨西哥裔美国民谣歌手,《探求小糖人》中的主角。
5.喷鼻香港著名音乐人、明星导师,学生包括林忆莲、张学友、陈小春等。
6.新加坡著名音乐人,曾给诸多华语歌手作曲,包括张学友、孙燕姿、张国荣等。
《林忆莲:野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全新推出的华语音乐文化系列丛书“大声”中的一本,同期推出的还有《邓丽君:淡淡幽情》
任务编辑:顾明
校正: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