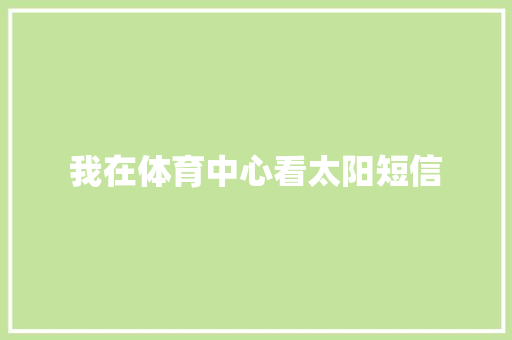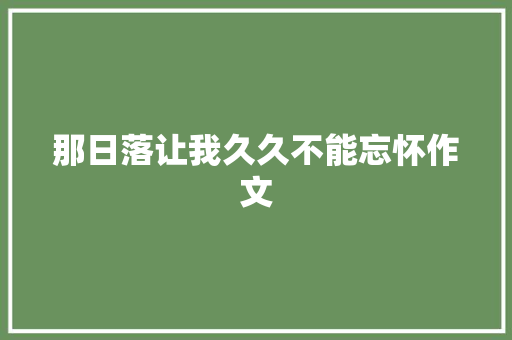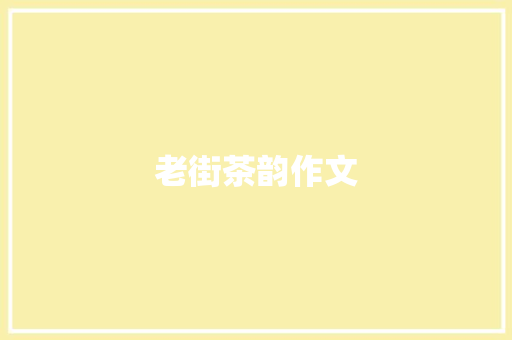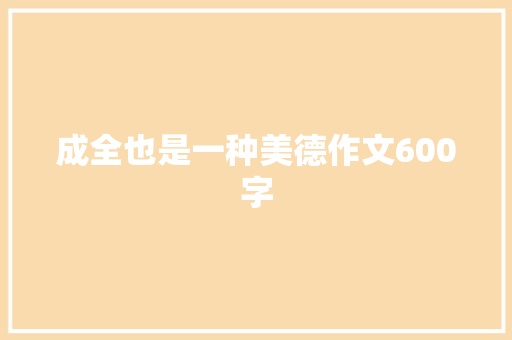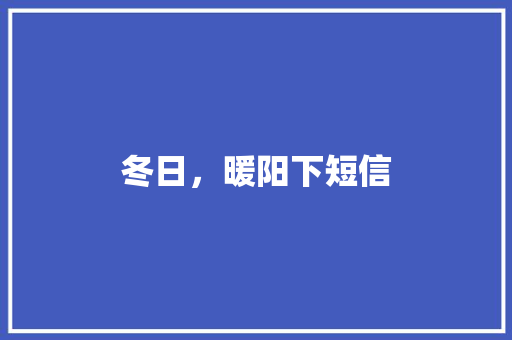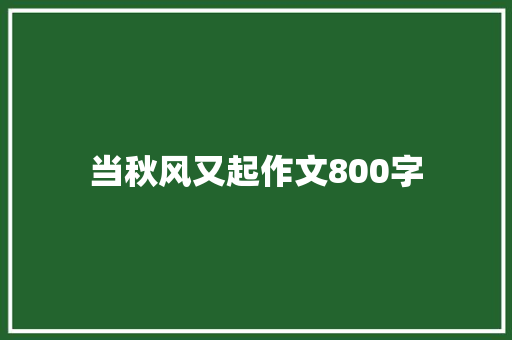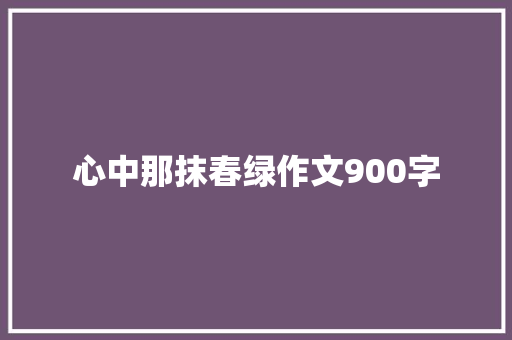这是话剧《陌生人》的第三场大戏,整组画面在舞台上是连贯的,仿佛韶光就这样一秒一秒地流逝。不雅观众看到这一幕时,心里会犯嘀咕:这是悬疑吗?这是科幻吗?这是女儿和那个男人设下的什么圈套吗?都不是。
在这一幕之前,故事只是井井有条地阐述着,女儿打算去伦敦,可身处巴黎的老人却须要人照顾,女儿帮老人找了几个护工,老人都不满意,以各种办法将她们逼退。

这是一个传统文本下的开场,在这个开场里我们创造,老人老了须要人照顾,可老人自己不肯望被人照顾,老人的影象力有时会不太行,比如他就常常忘却自己的腕表被放在何处,女儿爱上了一个男人,想要去伦敦拥有自己的生活。
只管传统,但这个开头依旧能够让我们感想熏染到这出话剧的几种抵牾:女儿的个人生活与老人的生活的抵牾、老人与这个“不友好”的天下的抵牾,老人与自己的抵牾。
实话说,这些抵牾并没有多出彩,在险些所有的类似故事里都会有这样的抵牾,但如何呈现这样的抵牾才是磨练编剧和演员的地方。常日来说,编剧会设计一些生活中的片段,让这些抵牾随着韶光推移而走向高潮,然后一并办理。
但既然何冰选择了这样一部话剧,那显然就不可能这么“诚笃”地完成这个故事。
《陌生人》海报
在《陌生人》的宣扬海报里,编剧一栏写的是“弗洛里安·泽勒 [法]”,这是一部西方人所写的话剧,原作叫《父亲》,是弗洛里安·泽勒的代表作。一出以西方家庭为背景的话剧,移植到中国来,是否会显得突兀呢?
更何况,何冰的台词中自始至终都带着一口京电影。这个问题在《白鹿原》里尤其明显。只管何冰的鹿子霖演得惟妙惟肖,把鹿子霖的小算计都表现了出来,但这部陕西话打底的电视剧,何冰演嗨了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飙出一两句北京话来,从这一点来看,是有损剧集质量的,虽然无伤大雅但毕竟有些遗憾。
然而在话剧《陌生人》里,他的京电影一点不影响对文本的诠释,反倒是几个年轻辈的,会受剧本台词的影响,时时时冒出几句翻译腔来。
毕竟口音是外在的,但情绪是人类共通的。
话剧《陌生人》里的情绪既强烈又平和,它所涉及到的内容没有太多西方文化底色的(这与赵立新去年年底的话剧《父亲》恰好相反,那是赵立新的骄傲和情结,因此他毅然将这部西方天下的作品搬上了小舞台),而是那些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最为关心的那些: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疾病与去世亡,而这统统都被反响在岁月的流逝上。
在本日的中国,中产阶级数量日渐增多,而放在中年人面前的个人生活与老人生活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凸显,这是这出话剧能在中国本土有情绪根本的缘故原由之一。另一处缘故原由则在于中国文化里始终被安顿着一个叫做“孝”的核心不雅观念,只管西方文化里并不存在这一观点,但这出话剧依旧能让不雅观众感想熏染到子女对父母的关怀——当然,在西方文化里这并不被定义为“孝”,因此不雅观众在不雅观看这部话剧时可能会对某些人物的行为产生些许不适。
这无关紧要。由于这出话剧最大的看点,实在是剧本的表现形式和主演(即何冰)的演出技巧。
从文首讲述的一场片段来看,我们并不能确切地得出它讲述的将是什么样的谜团,但随着环绕在老人身边类似的情形越来越多,当老人说着说着场景就从客厅变成了病房,当老人说着说着韶光就超过了好几年时,我们终于明白了话剧名字“陌生人”的含义,以及故事的表现办法。
老人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这个角色中外都有许多名家演过,几年前李雪健也在《嘿,老头!
》里成功塑造过这样的角色。但《陌生人》可以算作一部实验话剧,它讲述的办法很奇妙:它在以患者的视角看待这个天下,而不因此子女的视角来看老人。
当不雅观众理解了这一点后,就会迅速明白剧本里看似凌乱无章的段落了。有的场景他们会不断重复,有的对话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但是说的人、说的韶光、说的语气和说的场景都变了,只是剧情不断上演。
由于这统统都发生在老人的脑筋里,或者说,现实天下里发生过,但老人记不得或记不真切了,有时他涌如今客厅里跳起了踢踏舞,有时他把头埋在怀里长久地沉默。
虽然碎片化,但每后一场戏比起前一场戏来,也并不是随意安顿的,编剧在故意不断叠加与增强信息量与传染力,随着故事的进展,老人对这个天下开始逐渐陌生,哪怕他每天见到的都是同样的程序化事宜,伴随着照顾老人的人们的反响,我们能窥伺出老人的内心与老人的过去。
这样的表现形式与《北京法源寺》很像。《北京法源寺》是一场无休止的活人与去世人、正谕与解构之间的对话,反复、加强、碰撞,末了在一曲《清平调》里各声部产生共鸣,达到高潮。《北京法源寺》是我最喜好的话剧。
《北京法源寺》剧照
在阐述《陌生人》剧本构造之前,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过去看过的那些阐述故事的句子,诸如“在良久良久以前”、“早在几百年前”等等,这样的句子每每过于单一:由于在这样的叙事构造中,它将阐述工具和阐述时域牢牢安在了过去,使之成为“历史”中的叙事,它与阐述者的韶光相对固定,缺少灵巧性,在这样的叙工作况下,即便再次涌现“十年后”,依然是那个固定时空中的十年后,而非跳跃式的。
亦即在这样的叙事构造中,韶光是线性的。而再稽核“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衲人跟一个小和尚,有一天老衲人对小和尚讲,从前有座山……”这样的循环,很明显在这个循环中韶光发生了跳跃,它不再拘泥于“从前”的那个时空,而是不断往前跃迁。但即便如此它依然是没有美感的,由于它缺少一个真正的阐述工具,只是改变了阐述时域。
理解了这两点后,我们就知道为何《百年孤独》开头如此迷人了。由于它同时改变了阐述时域和阐述工具的固定性。“许多年之后面对着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忆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迢遥的下午”这句话里涌现了三个时域,“许多年之后”是未来时域,“将会回忆起……那个迢遥的下午”是过去时域,而阐述本身则处于现在时域。当读者阅读到这句话时,会很自然地创造接下来作者将用哪个时域来讲述故事是不愿定的,可以连续承接着该句,也可以去往许多年之后,还可以回到那个迢遥的下午——这里的阐述时域是开放性的。而阐述时域的开放性自然导致了阐述工具的开放性。
韶光不再是线性存在于句子当中,而是仿佛环形构造一样平常,可以从环中的任一节点开启。而这样的无常反过来则会加重读者的虚无感。
回到《陌生人》。通过上面的剖析我们创造,《陌生人》同样包含着一个永恒时域的无指向构造,上一场是未来时域,下一场是过去时域,而阐述本身则处于现在时域。
老人被永久困在凌乱无章的影象里,无法走回现在。
如此实验式的构造对不雅观众来说不得不说是一次寻衅。好在这样的寻衅被何冰大大降落了难度。
在两个小时的话剧里,何冰演出的老人身惩罚歧的时空,脑海中却影象着不同的过去,那是我们局外人眼中的老人。但对老人自己来说,这统统都是线性流逝的。
老人早上起来,要喝咖啡,老人碰着了自称是自己半子的男人,男人和老人“摊牌”,韶光过去没多久,女儿见告老人现在是晚上八点。
老人没法自己看韶光了。话剧刚开始就一直凸显出老人很有韶光不雅观念,他有一块伴随他大半辈子的腕表,但故事的第一幕,老人就找不到了自己的腕表。后来一次又一次地,老人持续赓续地失落去了那块腕表。
失落去的也是韶光与影象。朽迈迎面而来,影象迅疾而去。
留给老人和不雅观众的,只有对天下的逐渐陌生与对人生的逐渐绝望。
故事是碎片的,何冰给出的感情却是线性递进的。从最一开始的不服老,到后来的困惑,到后来的沉默,再到末了的茫然,老人被这个天下“抛弃”了,他永久在现实与过去的巨大惨淡里活着。
如果何冰的演出没有这样层层叠加,那么不雅观众很随意马虎会以为枯燥乏味。可是就由于何冰在不同时空场次里表现出了老人感情上的连贯性,才能让人从心里开始灰暗。
话剧末了,老人失落控了,失落控的他哭喊着在叫一个人。
他在喊:“妈妈!
妈妈!
”
他坐在那里,他站在那里。他想找一个人抱抱他,可他茫然而又孤独,他很朽迈,朽迈到不认识任何一个人,面前的人不知道是谁,脑筋里念着的也混混沌沌,末了只有母亲从内心深处冒了出来。这是他孩提时候的影象,也可能是残余着的唯一的影象。
这是一个永久走不出去的迷宫。在迷宫里的每一次横冲直撞,失落去的都是自己的影象,终于走到末了,腕表丢失了,韶光丢失了,人来人往,可自己谁也不认识,只记得妈妈。
啊,老人的“玫瑰花蕾”。
电影《公民凯恩》里,凯恩临去世前末了说的一句话:“玫瑰花蕾。”
如果没有听错,在话剧快要结束前,奏起了一首插曲《The Dark End Of The Street》。这首歌被大多数人知道是由于一部美剧《相对宇宙》,讲述了一个迷失落在平行宇宙里的故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彷佛也能作为《陌生人》的互文作品。
在这惨淡的街尾,我们无数次相见,循环往来来往,走完生平。
这首歌的歌词本身,就已经可以与我们的话剧相呼应:
“At the dark end of the street(在这惨淡的街尾), hat's where we always meet(我们无数次在这里相见). Hiding in shadows where we don't belong(我们偷偷隐蔽在不属于我们的阴影里), living in darkness to hide our wrong(让阴郁来粉饰我们的缺点). You and me(你和我), at the dark end of the street(在这惨淡的街尾). You and me(你和我), I know time is gonna take it's toll(我知道韶光也会收过路费的). Steal away to the dark end of the street(偷偷地,在街尾的阴郁中). They're gonna to find us(他们会找出我们的). They're gonna to find us(他们会找出我们的). They're gonna to find us(他们会找出我们的). Lord, someday(上帝,总有一天), you and me(你和我), at the dark end of the street(在街尾的阴郁中). You and me(你和我), and when the daylight hours roll round(当新的一天即将都来的时候), and by chance we're both downtown(如果有幸我们都在这座城市), if we should meet just walk on by(就算如果我们该当相见,你只要走你自己的路). Oh, darling(哦,亲爱的), please don't cry(请不要哭), tonight you shall we'll meet(今晚我们会相见的), at the dark end of the street(在街尾的阴郁中).”
孤独的旅人在灯红酒绿后独自一人走在寂静、惨淡的大街,走完他末了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