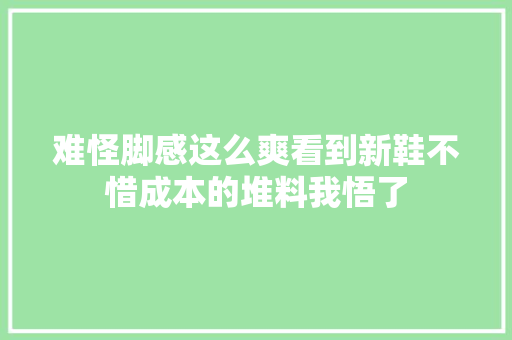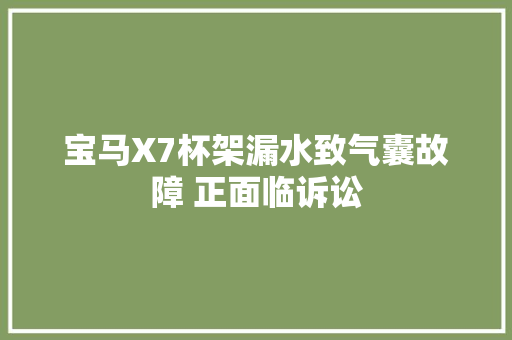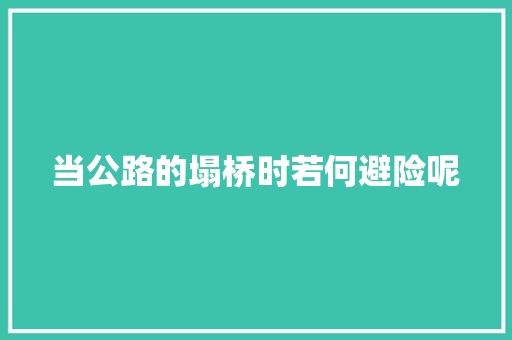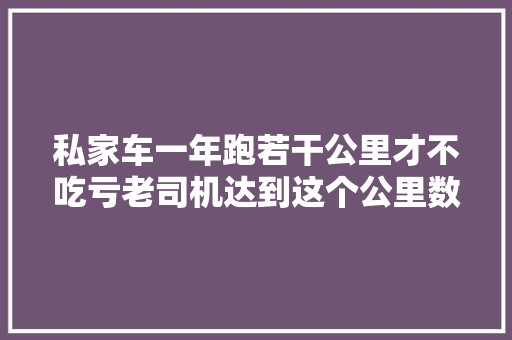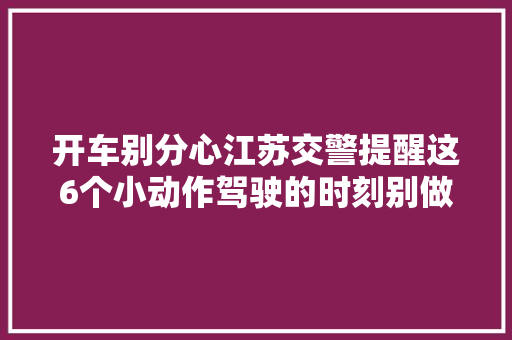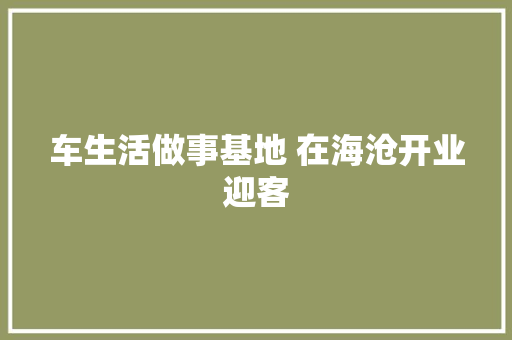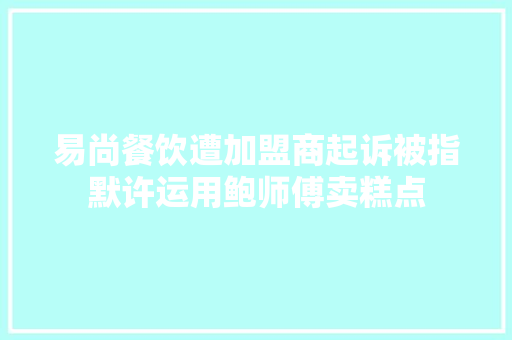阿拉山口属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在塔城地区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之间,到了这里路程就已经由去一半了。连续往南,会经由著名的景点赛里木湖和果子沟大桥,傍晚时分,大巴车终于到了伊宁市。
伊宁是一座不同文化交界的城市,自宋朝开始,经历了喀喇汗王朝和西辽统治之后,元朝这里是察合台汗国领地。到了明末清初,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南下,伊宁地区成为了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个蒙古部落交界处。满洲人击败准噶尔蒙古统治新疆之后,设立伊犁将军,伊宁(并不是现在的伊宁市区,是指霍城县惠远城)成为了新疆地区政治中央,一贯到清末新疆建省,政治中央才迁到乌鲁木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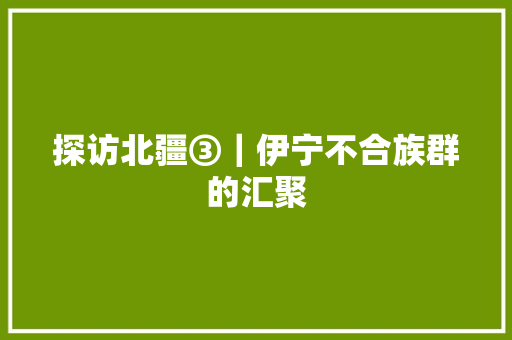
伊宁是非常适宜旅行的地方,周围的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库尔德宁草原、喀拉峻山、果子沟都是旅游胜地。比较于乌鲁木齐和塔城,伊宁是一座更为轻松繁华的城市,这里有业务到凌晨两点的夜市,那里的面肺子、椒麻鸡、酸奶刨冰和格瓦斯是必须要品尝的。但对我来说,这座城市最奇妙的是不同族群的汇聚,沿着我在塔城寻访的俄罗斯文化痕迹,我首先找到了伊宁市东正教堂。
伊宁东正教堂大门口。 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东正教堂的彼得
为了拜访东正教堂,我特意选了一个周日的上午,由于这是东正教宗教活动的韶光,我期待着能不雅观摩他们的仪式。走到东正教堂所在的黎光街四巷,就能看到能干的东正教十字架,教堂管理者克拉斯娜乌索夫·彼得·亚历山大维奇接待了我。
彼得是俄罗斯族,他的爷爷是顿河哥萨克人,三区革命期间的苏联红军义士,彼得本人也是政协委员,自满地说自己是革命红三代。彼得年轻时在伊宁附近放牧,这座教堂的前一位管理者是出生在苏联的汉俄混血,但老人家身体不太好,机缘巧合彼得就接替了他,开始管理照看这座教堂。
这座东正教堂本身并不是老建筑,原来的教堂在文革期间遭到毁坏,只剩下一口铜钟和两幅圣像画保存无缺。到了2002年,俄罗斯墓地修缮,在墓地的西北角划出一块地重修了教堂。彼得本人目前还不是正式的神甫,只能算管理人和领拜人,还要去莫斯科学习之后才能正式成为神职职员。
教堂阁下俄罗斯墓地的后门。
彼得带我参不雅观了教堂墓地,这片墓地里埋葬着一百多年来在伊宁去世的俄罗斯人,但大部分老墓碑都被砸毁了,以是根本无法对照出完全的墓葬名单。在这片面积不大的地皮下,不知道到底安葬了多少人,大部分都已经成为了合葬墓,少数墓葬立着十字架来标识。墓地里目前安葬的大部分都是俄罗斯族,还有少量汉族是俄罗斯族的家属,虽然不一定是东正教徒,但也一同安葬了。
彼得给我先容目前能确认身份的墓碑,很多是近些年的,一些墓碑上还有照片,还有的是后来重修的义士墓。教堂曾经的神甫也安葬这里,但没有明确的墓碑。彼得带我去他爷爷的墓前瞻仰,这里安葬着很多三区革命期间的苏军官兵,彼得的爷爷便是个中一位,共产革命的红五星和东正教十字架同时涌如今墓碑上,也是难得。
在新疆的俄罗斯墓地,不少都受到过毁坏,包括彼得自己祖母的墓也被毁坏过。这些墓地在经历了繁芜的历史后,没有妥善保管的干系方法,也没有直接卖力人,如果不是苏军官兵墓葬就不受政府保护,很多时候只能靠俄罗斯族居民自己去各地与政府和开拓商交涉。
附近中午十二点,开始有人陆续来到教堂,基本都是老年人,有两位略年轻的男士是从俄罗斯来伊宁专程拜访这座教堂的。这些老人们很多是二代三代混血,有的能看出明显的俄罗斯人长相,有的已经是汉人样子容貌了。
大概来了十几个人,彼得开始带领大家走进教堂正厅里,他们先是排队去教堂前面轮流点燃烛炬插在烛台上,然后亲吻圣像。教堂的墙上挂着东正教圣像画,在一个角落有宗教仪式用的帽子、圣水和礼器,一张小桌子上摆着俄文的《圣经》和宗教书本。
东正教堂里面的圣象画和礼仪用具。
仪式开始时,男女在屋子两边分开站立,女人们戴着头巾,有些腿脚未便利的老人坐在墙边的椅子上。彼得开始拿着《圣经》诵念,到了某些段落大家一起年夜声唱祈祷词。诵念的内容都是俄语,我完备听不懂,但是那种悠长的唱腔,我却是熟习的。
作为一个回民,我从小居住在汉族地区,与西北穆斯林聚居区盛大的宗教活动不同,在我印象里,宗教最常见的场景反而是在这样的斗室子里,一群老人们颂主赞圣。我去过很多地方的不同宗教场所,比如南方的清真寺一样平常人不多,却打理的非常干净清新,到了星期韶光,零零落落一些老人来到清真寺,在阿訇的带领下星期,结束后再一起聊谈天拉拉家常。
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兴盛,东正教有种坚守的孤独感。俄罗斯文化中有一种很特殊的对苦难的理解,人们崇拜那些疯疯癫癫肮脏邋遢的圣愚,认为他们放弃了肉体的享受而遁入灵魂的净化。在俄罗斯漫长的冬天和西伯利亚了无边际的冻土荒原上,韶光仿佛是凝固的,人们把苦难理解为生活一定的样子,就犹如一定的冬天一样。
彼得先容,在伊宁的东正教徒并不多,大部分是老年人,由于长期短缺神职职员,很多人也没有正式洗礼过,他们等待有正式的神甫被派到这座教堂里。但即便如此,教堂的活动近些年是不少的,除了日常主持的修缮墓地和婚丧礼节之外,每到宗教节日也会举办活动,让教徒们感想熏染到亲切与温暖。
伊宁本地的俄罗斯族来源比较繁芜,有很早一批来此做生意的俄国贩子后代,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白俄难民后代,有被斯大林驱逐返国的华侨家属,也有苏联红军后代。不管他们的先人因何而来,如今他们都同样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在这座教堂里祈祷。
在教堂的另一侧,有一家世居的俄罗斯族,男主人叫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扎祖林,经营着一家手风琴博物馆。彼得说他们家不是平常的东正教徒,但也不说自己是什么教派,我认识的东正教朋友推测可能是五旬节派,是在新疆地区存在过的两个东正教少数教派之一。我这次去他的店没有开门,很遗憾。不过关于亚历山大与他的手风琴博物馆,网上倒是有不少文章。
六星街
仪式结束后,彼得又要开始劳碌的事情,他还要带俄罗斯来的客人去当地派出所登记,我也告辞离开了教堂,在周围闲步。教堂所在的街区叫做六星街,这片街区是1936年建成的,由德国人设计方案,当时的民国政府仿照欧洲中央辐射式街区,在伊宁以反帝、亲苏、民族平等、和平、培植、清廉六条政策为理念设计了六星街。
在这片六星街里,居住着汉、回、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塔塔尔等民族,由于当时来到伊宁的俄罗斯人大多居住在这片街区里,引领了这里的审美,以是无论哪个民族的房屋,都带有俄罗斯民族风格,斜坡屋顶、雕花装饰的窗框、人字形门廊和俄罗斯蓝色调。在这片街区的北面还有一座俄罗斯学校,只管大部分学生是维吾尔人和汉人,但依然在教授纯洁的俄语。
从六星街出来,沿着解放西路一起向东,就能走到伊犁宾馆,这里曾经是俄国及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宾馆内现在还有四栋俄式建筑,建于1881年,是领事及事情职员的办公室和住宅。在领事办公室北面还有一栋高大的水塔,水塔下端是砖石,上端是木质,整体呈自然石料的灰褐色,木质部分是暗赤色,底端有门可以进入个中。之前,我在塔城的俄国领事馆(现在塔城地区宾馆)看到有一座相似的水塔。
俄国领事馆内的水塔。
俄国驻伊犁最早的领事机构设立在惠远城,1866年惠远城被塔兰奇人暴动攻陷,俄国领事馆被毁坏。俄国从1871到1881盘踞了伊犁十年,1882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后,俄国归还伊犁地区并在宁远城(伊宁市)设立领事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一开始中华民国与苏俄政府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伊宁的俄国领事机构依然被帝俄旧官员把持,直到1924年两国建交,俄国领事馆才改为苏联领事馆。1962年后,苏联关闭了领事馆。
汉人街没汉人
从伊犁宾馆出来沿着胜利北路往南,就能走到公民广场,转西一条街,在街口能看到一排白墙蓝窗蓝屋顶的屋子。现在是小天使幼儿园,曾经这里是文丰泰店铺,伊宁有一句俚语“汉人街没汉人”的典故就从这里开始。
曾经的文丰泰店铺,现在的小天使幼儿园。
1875年的时候,左宗棠的平叛军攻入新疆,击败了白彦虎和阿古柏的军队,当时有很多随军的贩子“赶大营”一同到达新疆。由于军队平叛之地生活物资都很缺少,一旦战乱平息,物资需求又会很高,巨大的利润使令贩子们去赚这些危险钱。这些随军贩子大部分来自天津的杨柳青镇,随着军队跋涉开始了新疆与京津之间的商贸往来,文丰泰店铺的老板安文忠便是这一批赶大营的天津贩子之一。
1881年,俄国归还了伊犁地区,安文忠跟随军队到了伊宁,三年后,新任新疆巡抚刘锦棠热心支持商业,安文忠在伊宁城里开了一家文丰泰京货店,是伊犁实力最雄厚的津帮店铺。1909年,宣统天子登基,大清国走到了尽头,新疆场合排场也开始动荡,安文忠把店铺交给弟弟打理,自己返回了天津开设了洽源店铺,开始投资金融业。1921年,文丰泰店铺关闭,之后这栋屋子几经易主,到了1997年被一位维吾尔贩子买下,改造成了小天使幼儿园。
伊宁的汉人街最早便是汉人居住的地方,这些来自天津杨柳青的贩子们在此开店做生意,把这里变成了一片贸易繁荣的商业街区。宣统天子登基后,京津政治场合排场严厉,一些贩子出于安全考虑返回内地,但依然有一些人一贯留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
四十年代后,三区革命爆发,伊宁是三区革命的中央地带,民族与政治派别抵牾尖锐,贩子们成了斗争的捐躯品,也就扔下买卖逃散了。外地汉族贩子们走了之后,本地维吾尔贩子们连续在这片街区做生意,这条汉人街依然商业繁荣,名字也保留了下来,久而久之就有了“汉人街没汉人”的说法。
三区革命纪念地
谈到三区革命,在本日的伊宁市内有两处三区革命纪念地,一处是公民公园里的三区革命政府政治文化活动中央,走进公民公园,在一大片树林里,能看到一栋蓝白相间的二层大屋子,这栋屋子是三区革命政府准备用于校阅阅兵军队和群众的活动中央,现在被包在公园内。另一处是公民公园以西不远的三区革命义士陵园和革命纪念馆。
三区革命政府政治文化活动中央的正面。
在三区革命义士陵园中,会创造历史给伊犁和新疆一个戏剧性的岔口。1946年,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出任副主席,但谢绝交出军队,不久联合政府分裂。到了1948年阿合买提江在伊宁主持成立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并出任主席,上文提到的活动中央也是在这一期间建筑的。然而在新中国建国前一个月,在即将与新中国中心政府达成协议的时候,革命的紧张领导人阿合买提江、达列力汗、阿不都克里木、伊斯哈克伯克乘飞机失落事,在苏联境内外贝尔加地区全部罹难。
三区革命义士纪念碑。
历史总是这样充满戏剧化,不能不让人想象,如果这些三区革命领导人没有遭遇空难,他们对新疆的场合排场发展会有若何的影响。在伊宁市,为了纪念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便是公民公园东侧这条南北走向的阿合买提江街。
喀赞其街区
把目光移回汉人街,往南连续走,就到了伊宁最著名的老城区——喀赞其民俗区,这是所有到伊宁的游客都会逛的地方。一样平常来说被称为民俗旅游区的地方,总是免不了弄虚作假,搞一堆全国到处都有的店铺和义乌批发的小商品假装当地特产,找一些人穿上奇奇怪怪的民族服装让游客拍照。但喀赞其不是这样,这里是真正有本地人居住的生活区域,是一片平衡了旅游商业与日常生活的街区。
在喀赞其街区的入口,有一座明显的中式传统建筑,这是回民的陕西大寺,我们在前文提到乌鲁木齐也有一座陕西大寺,是陕甘回民迁徙到新疆的紧张文化保留痕迹。伊宁最早的回民清真寺建于1751年,在清军击败准噶尔蒙古之后,个中部分来自陕西的回民士兵留在伊犁地区屯垦。1762年清朝设立伊犁将军,清真寺被命名为永固寺,取安宁永固之意。
陕西大寺整体建筑是中式风格,仿照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建筑,并有三层宣礼塔。须要强调的是,新疆的回民也是分不同期间来到这里的,不同期间又代表着不同的群体。最早跟随清军来屯垦的是一批人是军队出身,到了同治年间来新疆的,则大多是躲避战乱的平民。
提到伊宁的清真寺,可能更多人理解的是地标式建筑拜吐拉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是伊犁最大的清真寺,离喀赞其街区只有两条街的间隔。拜吐拉清真寺建筑于1773年,也是当年伊犁的伊斯兰经学院,位置就在曾经宁远城的城中央。但是,我们本日看到的宏伟的白色清真寺主体建筑是1995年翻新重修的,只有门前那座灰绿色的中式宣礼塔才是真正的老建筑。以是那座清真寺的文物保护标识,写的是拜吐拉清真寺宣礼塔,而不是整座清真寺。
拜吐拉清真寺,白色建筑是新建的,右下角正在掩护的中式宣礼塔才是老建筑。
在喀赞其街区内,有一座俊秀的棕褐色塔楼,拱形窗的砖石雕花格外精美,这座塔曾经也是一座清真寺,叫做乌兹别克清真寺。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一些乌兹别克人由于抗拒苏维埃政权而逃到新疆,这些人当中很多是地主、富商、知识分子、旧军官和宗教人士。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苏联农业集体化改革,又有一批人来到政策相对宽松的新疆定居。
喀赞其民俗区里面的乌兹别克清真寺。
1933年,在伊宁的乌兹别克人集资建筑了乌兹别克清真寺,两年后又在阁下建起了乌兹别克学校。1955年后到六十年代初,大批乌兹别克人离开中国返回乌兹别克斯坦,后来伊犁地方政府规定学校不得涌现民族名称,乌兹别克学校也就改为了伊宁市第五中学。
与这座乌兹别克学校命运相同的是伊宁塔塔尔学校,也便是现在的伊宁市第六小学。从十九世纪开始就有塔塔尔人来到伊犁,他们在学界和商界十分生动,并且热衷于涉足政治。1925年,在塔塔尔人紧张聚居的伊宁老城西北角创办了塔塔尔学校,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学校停办改成现在的样子。
现在的塔塔尔学校只有一片平房还保留着当初的建筑,白墙蓝窗绿瓦,还有一座蓝色的门廊该当是过去老学校的正门。我去的时候,这座门是锁着的,只能从学校另一侧的大门进入。
曾经的塔塔尔学校。
除此之外,喀赞其街区内剩下的就紧张是店铺了,维吾尔手工冰淇淋是这里的一绝,街边维吾尔老奶奶卖的比店铺里的便宜而且更好吃,还有格瓦斯装在大桶里在路边卖,这两样冷饮都是俄国人带来的,和东北一样。喀赞其街区的店铺中,皮具、铁器、地毯、鞋帽、丝绸刺绣都是颇具民族特色的,这片街区很多庭院都被作为开放的接待家庭,游客可以进入参不雅观体验。
所有来到喀赞其的游客都会去拍蓝色的墙壁,更值得把稳的是窗子、门廊和屋顶的设计,这里的窗子都是双层的,窗子上方有遮挡融雪的突出窗檐,玻璃窗外有一层木窗,还有一道斜向的木条,这是俄国人带来的颇为讲求的御寒设计。
喀赞其的房屋窗户设计。
与东北不同的俄国移民文化
我之前探访过东北地区的俄国移民文化,和新疆是略有差异的,由于两地移民构成有所不同。新疆的俄国移民相称一部分来自边疆临近地区,是作为被驱逐返国的华侨家属来到新疆的,贩子中也有很多是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塔塔尔人和乌兹别克人,还有三区革命期间留下来的苏军后代。
但是在东北,早期的移民大多是跟随中东铁路而来的工人、贩子和士兵,这些人来自工业化更发达的俄国西部地区。同样在东北的俄国贩子中,犹太人占了很大比例,亦有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德国人,少量塔塔尔人基本是十月革命后的白俄移民,没有乌兹别克人的记载,也没有苏联军队留下定居的记录,这是与新疆移民构成不同的。
东北早期的俄国移民大多与中东铁路有关,他们沿着铁路线建筑了很多小村落镇,现在铁路沿线很多村落镇都是俄国人平地建起的。但是在新疆的俄国移民则不是作为初期培植者,而是做生意或搬家定居,险些一开始就直接居住在城市,极少去屯子。
比拟两地的俄国移民文化遗留,会创造东北地区由于俄国官方的早期培植,东正教根本发达,虽然目前教徒不多,但是依然保留了不少大型教堂建筑。同时,十月革命后大批的俄国知识分子和旧贵族来到东北,把俄国的文化艺术带到哈尔滨这座大城市当中。新疆地区的俄国移民则更多保留了民族习俗,由于他们当中除了一部分贩子之外,大部分是农牧后代,在社会阶层上与东北的俄裔不太一样。
这一点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场合排场有关系,由于多国干涉军最早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上岸支持白俄军队,以是不少知识分子、旧军人、旧贵族沿着西伯利亚铁路流亡到中国东北,之后又辗转到上海等地。而靠近新疆地区的俄国领土,十月革命后很快就被苏维埃政权掌握,以是过境的俄国人不多,倒是间隔较近的喀山地区,有很多塔塔尔人来到了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