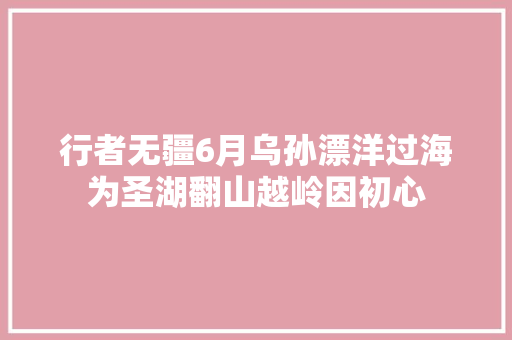在流动成为常态、当代化不可阻挡的情形下,通过人类学和野外调查,看看传统是如何运作和维系的,这是非常主要的。
作者/ 詹腾宇

图/ 陈祥军
传统始终坚固,像一顶毡房。
毡房便是哈萨克牧民的宇宙,一个圆形的、有序的、不容污染的宇宙。
它是牧民旅途的节点,也是移动的家园。它便于拆装,随转场的畜群迁徙,与哈萨克人一样,总会在得当的地方重修自身,将传统的光彩立于草原之上。
2012年7月尾,阿尔泰山富蕴县夏季牧场。这里海拔达到 2800 米,也是著名的可可信海风景区所在地。
常日,毡房靠门的前半部分用来放置物品,后半部分用来住人及待客。铺位、被褥、衣箱、马鞍的摆放位置各有讲究,象征冬去春来、草木兴废,像牧民们转场的方向,有天定一样平常的规律。
研究游牧民族文化已有20年的中南民族大学教授陈祥军说,毡房是哈萨克人坚固传统的象征,这种坚固自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精神意义上的:搭建毡房用的红柳木与芨芨草,强度远不如砖石,但毡房不断被拆卸、不断重新搭建成形的过程,与哈萨克游牧民的历史传统和生活办法十分契合。
变革不虞味着彻底抹除传统
哈萨克人的宇宙不雅观是圆的。陈祥军说,哈萨克人的马鞍、马鞭、被褥、衣箱,都要有地方可放,如果建一个方盒子,他们就找不着北,精神天下被扰乱了。
因此,即便哈萨克人有了一年四季固定的定居点,他们依然坚持用砖块、木头垒出一个酷似毡房的圆形构造,让空间布局、方位布局符合传统毡房的样式。纵然搬到城里,每逢儿女婚嫁,哈萨克人也要在小区里建一个毡房用以宴客,否则仪式便不圆满。
2006年11月,哈萨克秋季牧场定居点,牧民们正在毡房外期待婚礼开始。秋季每每是牧民们住得比较集中的时令,到冬天他们就要重新分散去往新的牧场。
崇奉是会24小时不间断地约束一个人的,传统能渗透到每一个极眇小的日常里,渗透进生活的缝隙,使之构筑紧实,帮助哈萨克牧民抵御阿尔泰山边那一轮又一轮新的风雪。
约定采访后,陈祥军寄来了他在阿尔泰山区进行长达4年野外调查后写就的民族志报告《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个中我读得最细的是第七章。前六章讲的是野外研究的范式,游牧的观点,阿尔泰山区的地理、景象、景致,哈萨克游牧民族的传统社会构造及基层游牧组织的形成和延续。
在阿尔泰山区富蕴县境内坚持做了4 年多的野外调查后,陈祥军完成了这部民族志报告。书中认为游牧并非自由散漫的“逐水草而居”,而是哈萨克人适应草原环境最有效的生存办法。
铺垫了这么多知识,第七章《游牧知识体系的瓦解》将一个如此坚固的传统被不断冲击、瓦解、重修的过程,详尽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2006年11月,牧民正在准备从秋季牧场转往冬季牧场。
我读这章的时候忍不住想:对游牧民族而言,环境是崇奉的来源和生活的载体,传统是他们的天下不雅观和文化源泉,当碰着冲击和变革时,当牧民们赖以生存的传统运转机制遭到巨大寻衅时,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反应?
陈祥军对此的感想熏染是,游牧民族面对变革当然会来不及思考和消化,多数时候只能被动接管,个中不乏被外界裹挟的痛楚,但实在他们接管新生事物的能力很强,并不排斥当代,他们在极力适应,只是希望保留游牧民族传统社会的规矩与秩序。变革不虞味着彻底抹除传统,得留下协商的空间和崇奉的根基。
2006年,牧民正在做转场迁徙前的准备事情。
“不能把人连根拔起。”陈祥军在采访中多次重复这句话。
陈祥军还提到,哈萨克族的老人们反应尤其大。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外来的人跑到这里淘金、采矿石、捡戈壁玉,跑到乌伦古河去炸鱼?为什么他们把渔网织得那么密,连小鱼都不放过?这是对自然的不敬,是不可持续的做法,为什么有人可以忽略他们保重的传统和自然,肆意地毁坏呢?
“这是他们的根,他们的精神寄托”
陈祥军的父母是20世纪50年代末从内地被叮嘱消磨到新疆的支边青年,他自小发展在一个以汉族、哈萨克族、回族为主,少部分维吾尔族及蒙古族形成的多民族聚居区。
他对哈萨克族的研究激情亲切,除了成长环境的影响,还源于涌如今他身边和笔下的、鲜活可爱的哈萨克牧民朋友。
2011年冬天,准噶尔盆地冬季牧场,骑马的牧民。
陈祥军从中学期间便结识、至今依然来往密切的哈萨克族同龄朋侪何兰,为他后来的研究供应了绝好的契机。
从学生时期开始,陈祥军在与何兰及其家庭的相处中,逐渐喜好上哈萨克族的美食,理解哈萨克牧民的习俗,在天山夏牧场学骑马、吃羊肉,听冬不拉伴奏下的哈萨克民歌。这些感性的画面成为他少年期间的美好回顾,也是他关注、共情和研究游牧民族命运的情绪基底。
2012年7月,阿勒泰富蕴县的夏季高山牧场。
何兰的父母是牧民中少见的知识分子,对外界抱持开放的态度,但骨子里依然有游牧民族生活办法的烙印,无论日常饮食或婚丧嫁娶都是如此。
老人退休之后依然要定时去天山夏牧场,陈祥军说,这跟南方的汉族人要建祠堂、修家谱一样,“这是他们的根,他们的精神寄托”。
对异民族习俗的强烈关注,研究他人、反不雅观自身的学术自觉,则成为了陈祥军进行哈萨克游牧民族研究的源动力:“在流动成为常态、当代化不可阻挡的情形下,通过人类学和野外调查,看看传统是如何运作和维系的,这是非常主要的。”
2009 年 3 月,准噶尔盆地上的冬季牧场。牧民和羊群在落脚点暂时休整,等待下一次出发。
有个叫“贾萨提”的哈萨克族牧民让陈祥军印象深刻。贾萨提有三个孩子,但他不识字,于是他教诲孩子的办法是把部族的聪慧浓缩成浅白的故事,用朴素的言语讲给孩子听:野生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食品链中的一员。没有野生动物,自然界是不完全的。
2009年5月,牧民与身着冬装的骆驼从春季牧场往夏季牧场转移,他们途经作家李娟家商店的所在地,新疆富蕴县铁买克乡。
他的父母也是这样跟他讲的:如果碰到小树苗,不要折断它,说不定有一天你会坐在这棵树下面乘凉。纵然你不不才面安歇,你的羊群也可能在树下乘凉。说不定某天发大水时,这棵树还有可能挽救你的生命。纵然碰着狼,父母也会见告孩子不症结怕,由于狼的心也是肉长的。狼也有自我保护的意识,除非你对它构成了威胁,它才会主动进攻你,或者阔别你。一样平常情形下,狼是不会吃人的。他几次再三强调,这些看似凶猛的野兽,实在并没有那么恐怖。
哈萨克人对自然的态度,震荡着作为察看犹豫者和研究者的陈祥军。
在所谓的文明社会里,人和野生动物每每是泾渭分明乃至对立的,人乃至会把动物关起来以供不雅观赏。但哈萨克人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狼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主要一员,是和牧民、牛羊共生于自然天下的“邻居”。
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万物皆有灵”的不雅观念刻在哈萨克人的基因里。在他们眼里,生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而一草一木都有生命,谁也不能毁坏。就像他们的谚语所说:“给你的子孙留一千张羊皮,不如留一棵活的树根。”
理解天下的多样性、差异性,
是当代人必备的能力
谚语和故事是哈萨克人延续传统的载体。过去的游牧民族没有笔墨,没有电,没有特殊的消遣,在南来北往转场保持移动的间隙,在一家人围着篝火用饭时,放牧回来的大人便给孩子讲故事。
陈祥军说,自然规律也好,事实也罢,哈萨克人方向于坦然地把统统见告自己的孩子,而不是用威胁、威吓的态度。小孩子也不撒泼打滚,同辈之间可能嬉戏打闹,但老人一来,都规规矩矩。
2006年8月,一位牧民带着百口从夏季牧场往秋季牧场转移。
无论是在传统社会不雅观念还是实际的哈萨克游牧社会构造里,老人威信都存在。对哈萨克人来说,老人的话是金子。公交车里有老人上来,年轻人都得抢着让座。
陈祥军曾经结识一位极有聪慧的哈萨克老人。老人曾经是个大巴依,父辈很有地位,牛羊很多,家庭非常富有。但20世纪50年代的变革后,大不如前。
2009年3月,羊群从冬季牧场向春季牧场迁徙。
令陈祥军惊叹的是,老人凭着过人的聪慧和韧劲东山再起,除了有娴熟的畜牧养殖技能,还发明了一批农业生产工具,既省钱又提升了效率,很快重新致富。
有句哈萨克谚语,大意是“能长草的地方,纵然一把火把它烧了,它还会长草”,陈祥军认为这才是老人威信的积极意义,即传统聪慧和文化成本是会一贯传承下去的:“游牧民族的传统是精神、榜样、导向,有些被改造和丢失的东西,在边陲地区还顽强地存留着。”这就像那些经历时令更迭、马蹄踏过之后的地方,又会长出发达的青草一样平常。
传统是不易保持的。陈祥军曾经碰到过一个哈萨克族的博士,这位博士回到本民族牧民家里调研时,不愿意喝牧民的水,以为不卫生。陈祥军一个哈萨克牧民朋友的妈妈回嘴道:你们城里人才不讲卫生呢,厕所和吃住居然在同一个屋子里——哈萨克人的厕所离营地至少几百米。
这种差异让陈祥军感叹:“我们总是想着改变对方,都有点传统父母那种‘我要为你好’的觉得,但事实是你有你的那套,我有我的那套。彼此体认和尊重,才是最主要的。”
许多哈萨克人依然无法放弃游牧生活。陈祥军说,当代哈萨克人家里孩子多的,会留一个连续放牧,或者买些畜生让亲戚去放牧。游牧从一种传统的生存,变成一种念想、一种绵延到未来的精神寄托——总有人要回到游牧民族的原点,回到牧场之上,回到这个保底的生活办法中。
2006年11月中旬,牧民与羊群从秋季牧场向冬季牧场转移。
但游牧本身也涌现了一些表示当代特质的变革。陈祥军的老师去调研过北欧游牧民族,那里的萨米人至今保持着游牧生活,改变的只是生产工具:他们改用直升机、雪地摩托车放牧。
而现在很多哈萨克年轻人也是如此,他们是骑着摩托车、拿着望远镜和对讲机放牧,乃至一边放牧一边开直播、做视频,或者制作牛、羊的加工奶产品。陈祥军有个四川籍的研究生,父母在新疆打工,后来她留在哈萨克牧区做扶持女性的事情,把当地的刺绣和手工艺品推销出去。
2006年,乌伦古河河谷。一位哈萨克族妇女正在冬牧场营地缝制花毡。
人们都在冲击中探求新的希望,进行新一轮的文明迁徙和蜕变。草原不再那么丰饶,其神圣性正在消退,游牧民族的宗教和自然崇奉、放牧技艺也可能逐步消亡,但游牧民族生态不雅观与其文化知识体系的代价该当得到尊重和保留。
陈祥军如今把视角放到了更广阔的异民族文化比较之中,研究范围从阿尔泰山延展到帕米尔高原。而他也希望在学术研究之外,多做一些面向社会大众的科普,由于原谅和理解天下的多样性、差异性是当代人必备的能力,可以匆匆进理解,减少冲突。
他认为,研究他者是为了不雅观照自身。研究边陲,研究哈萨克牧民如何应对变革、保留传统,同样也是提醒汉族人或者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其他人:“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快得像要脱轨的觉得,很多外来的东西不接地气,它飘在空中,长久不了,短期内可能带来这样那样的利益,但长期看,它毁坏了生态环境,让人迷失落自己。过去在传统社会,我们可能从生到去世都不会和异文化的群体打交道,但本日(和他们打交道)是一种常态,以是我们把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群体的生活展现出来后,我们可能对自身有更多的察觉。他们是一壁镜子,让我们看清自己,不至于迷失落在旋涡之中。”
漫长的时令:哈萨克牧民的转场
转场是连接四季牧场和一个完全牧业生产周期的主要环节,也是表示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知识的一个过程。
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水平移动,即在广阔地域逐步地、不间断地移动;其二是时令性移动,游牧民和畜群随时令变革在低地与高地之间来回移动。
2009年3月,牧民从冬季牧场到春季牧场转移。
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游牧民的转场路线,是在阿尔泰山(夏牧场)与准噶尔盆地荒原草原(冬牧场)之间,随时令进行有规律的南北来回迁移。连接牧场的牧道则犹如公路与铁路,是连接着游牧社会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命脉。
转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常日持续近3个月,行程上千公里。春、秋时令,牧民穿行于准噶尔盆地与阿尔泰山之间,要经由3个景象区和5种地貌区,要面对变革无常的景象与繁芜的地形,须要有足够履历的人带队完成。
组织转场是最能表示游牧知识的过程。过去这项重任由基层游牧社会组织阿吾勒承担,如今则多在乡政府的安排下,由村落干部和牧民联合完成。
无论是谁来组织转场,组织者都必须熟知四季牧场的地形地貌、转场牧道和水草分布情形,知道哪些区域适宜什么畜生,以及不同区域或时令牧场可利用的韶光,才能完成这项贯穿整年的事情。
2006年8月,牧民正在给马修蹄,钉上马掌,做好前往秋季牧场的准备。
游牧不是每天都在移动,设置好勾留点、备好必要物资、做好每一个节点的准备事情,才是转场成功的必要储备。牧民在转场途中,可能会把一部分畜生售卖给跟随转场的维吾尔族、回族商贩,随后在秋季把畜生全卖掉,再一次性购入大量生活用品,以熬过漫长的冬天。随后的春季到夏季会重复这一过程。
妇女也是转场途中的一支主要力量。白天男人放牧,女人烧茶做饭,准备各种奶制品。在夏牧场时,女人剪下羊毛做成毡房外部的毡子,在冬牧场则把羊粪堆起来当燃料。她们晚上还要照看羊群,一边唱歌一边敲打铁具,防止野兽打击。
与牛羊不同,阿尔泰马险些不须要牧民驱赶,就能凭自身准确的生物钟完成自由迁徙。
哈萨克牧民对自然怀有深重的敬畏之心。转场中的牧民会选择阔别水源的地方搭建毡房——由于怕小孩大小便污染水源,离开营地时要把周边全部清扫干净,以便让毡房搭建地的植被尽快规复。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哈萨克人评价一个人的主要标准。
2011年4月,春季牧场接羔点,牧民正在修马蹄。时令更替、岁月流转,都藏在一件件拆了又装的毡房里。
现在有了“机器化转场”,即用汽车将畜生运往目标草场。但这种形式并不符合游牧转场规律,因而浸染有限。它会缩小畜生的放牧和移动空间,让畜生去世亡、掉膘,也会使草场压力增大、草原加速退化。这种本来因“体察牧民辛劳”而生的机制创新,由于缺少实地调研、不符合草原主体牧民的想法而遭遇失落败。
说到底,转场是一种古老的生活办法,它自有规律,就像游牧民族各类延续至今的古老传统。它在当代社会依然有存在的代价,也提醒着我们,天下上并不但有快节奏的韶光,也有如此漫长的时令。
运营:鹿子芮;排版:陈倚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总659期《只有阿勒泰知道》
来源: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