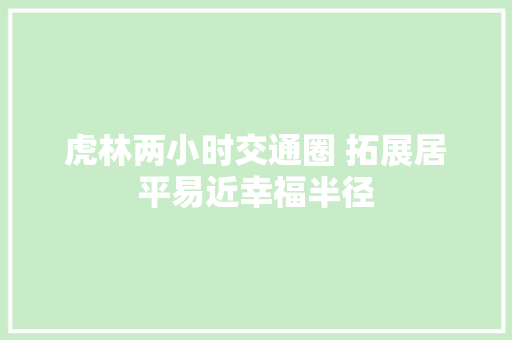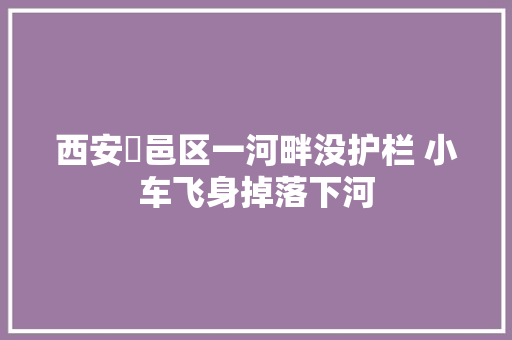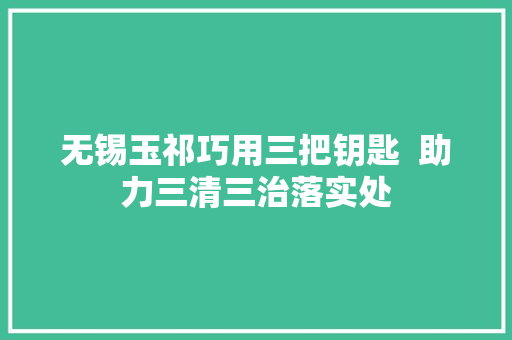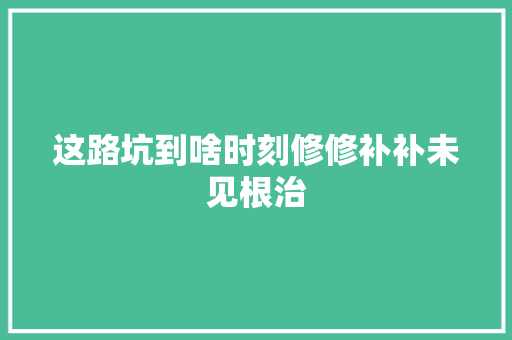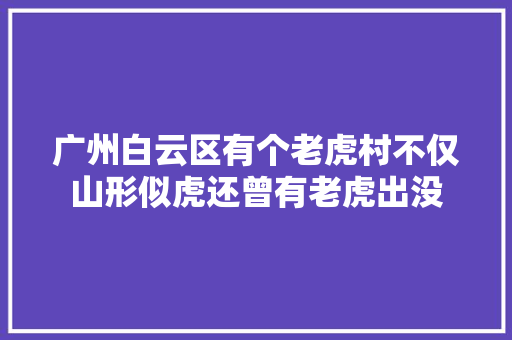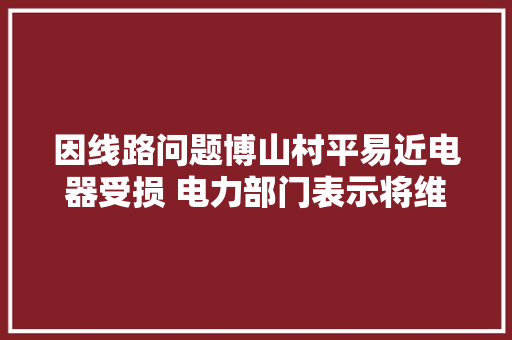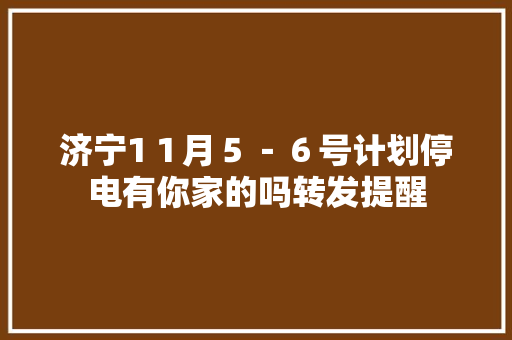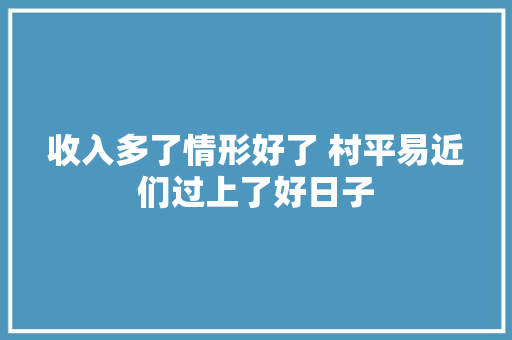创作第一部反响上海工人新村落题材的舞台剧《暖·光》,编剧管燕草构思和酝酿了五年之久。三万字不到的剧本,对她来说既难也不难——她从小生活在工人新村落,对这片地皮上的点滴故事和温暖人情再熟习不过;但要写好大时期下的新村落变迁却不易,光是剧本修正就经历了一年。
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落出身的城市,以其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和赤色文化是城市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正值上海解放往后首批工人新村落成70周年之际,由杨浦区文化和旅游局出品、上海当代人剧社演出制作的《暖·光》日前在YOUNG戏院首演,以话剧谱写了一曲工人新村落的歌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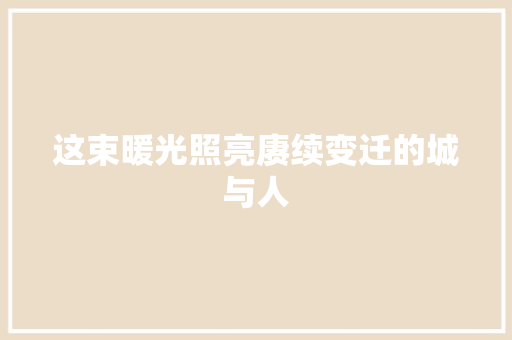
将工人新村落70年变迁“装”进舞台
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东风拂过大地,为表彰劳动模范与技能骨干,一批工人新村落应运而生。《暖·光》讲述了张家三代人和师兄李家三代人在建造、扩建、改造工人新村落的过程中,从搬入、搬离到再度回归工人新村落的故事。“在似水年华的人生窗棂上,工人新村落犹如那一抹温顺的暖光,穿透韶光的缝隙,照亮了岁月的台阶。”写到作品的创作缘起时,管燕草的笔触充满温情。
少年时期,管燕草从石库门里弄搬进控江新村落,“当代化”的气息迎面而来。彼时石库门居民大多还过着生煤球炉、倒马桶的生活,工人新村落里则是煤气灶、抽水马桶一应俱全。《暖·光》开篇,第一代工人张阿根和妻子从苏北来到上海,搬进工人新村落后止不住地愉快,一直地拖地和擦玻璃,表达对新家的爱不释手。在管燕草看来,工人新村落自带着一种不同于石库门和新式住宅的独占气质,由于职业、学历的相似背景,住在这里的人们分享着更紧密的邻里之情。“谁家家里烧了好菜,会端来一小份给大家尝尝。谁家没空,也会拜托邻居接小孩时顺便把自己的孩子接上。”
对付管燕草来说,将这份浓郁的情绪与回顾落成笔墨并不是第一次。此前,她就曾与父亲、著名工人作家管新生合著过三卷本长篇小说《工人》。然而,过往的履历并不全部适用于这次创作,话剧两小时旁边的常规体量让她探求起其他叙事入口,好将工人新村落70年的变迁“装”进舞台中。
四个时空来回切换,展现温和淳厚的质感
《暖·光》舞台场景还原了上世纪50年代第一批工人新村落的景象,照理说,工人新村落公用空间里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故事,这无疑是剧本天然的素材。但在创作过程中,管燕草给自己提出哀求,把时期感放在首位,不让作品显得过于市井化。《暖·光》中,父亲、儿子、孙子三代人皆以28岁风华正茂的样子容貌登场。上世纪50年代、上世纪80年代、新世纪、当下四个时空来回切换,见证着他们对工人新村落欣喜、无奈、怀念各不相同的情绪,而时期的流转亦通过他们的人生一览无余。可以说,台上呈现的那一段段故事和剧中人物的生活、命运,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一段文脉。
作为曾在工人新村落生活足足42年的上海人,著名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认为《暖·光》是一部抒发人文关怀、向共和国“致青春”的话剧作品,“这是一个多少被人们忽略而完备不应该被忽略的创作,真切地表现了中国大地独占的受益广大的工人新村落的生活”。
《暖·光》落幕,孙子从外洋留学归国,参与了工人新村落的改造工程,并为爷爷购置了一套与当年同样户型的屋子,让父辈在晚年找到熟习的归属感。剧中的景象是现实中工人新村落迭代的缩影,位于杨浦区的“长白一村落”就已华美转身成为城市新地标“长白228街坊”,这处曾经上海首批完成的“两万户”工人新村落连续肩负着为老百姓所用的义务。
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陈思和在剧中看到了许多微波不惊、却很有深度的细节,譬如上世纪50年代单位分配住房、上世纪80年代结婚无房、新世纪旧工房改造等等,都成了时期的缩影,让上了年纪的不雅观众看后感到唏嘘,让年轻不雅观众看后冲动。不追求流量,也没有太多“燃点”,《暖·光》展现出了一份温和淳厚的质感,它补上了城市影象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想讲述的正是平凡生活中的深奥深厚况味。
来源: 文申报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