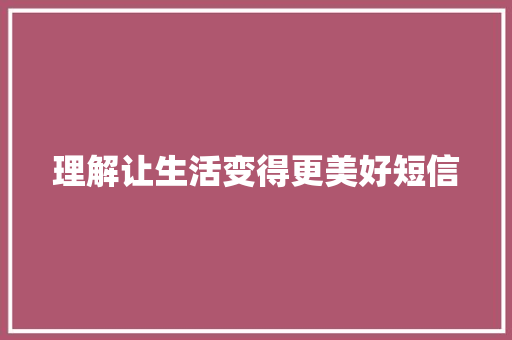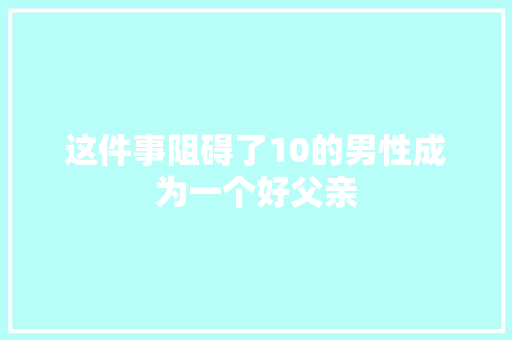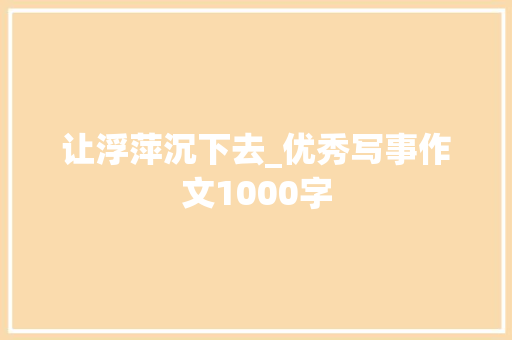父亲肺里有点炎症,我陪他去输液。
父亲推出他的老年代步车,头也不回地说,上去。我有些犹豫,商量似的说,还是我骑车带着你吧?我的犹豫有两层意思,一是我不忍心让父亲带我,二却是我从来没骑过这种车,对自己是否能骑车带他没有信心。父亲语气里含着不耐烦,不用,快上来。我听话地坐进车后座,心里装着几许羞赧。不等我坐稳,父亲已经麻利地骑了出去。起初沿路边逆行,我提醒道,爸,你逆行了。父亲一壁躲避着劈面而来的电动车,一壁说,就一小段,拐过去就顺了,这会儿人少。我只好沉默。

父亲流畅地过街穿巷。清晨的冷风呼呼地打在我脸上,我却分明以为脸在发热:我一个中年人,却让满头白发的父亲载着,怎么说都无法心安理得。我感到,过往的每个人都在心里骂我和嘲笑我,但我别无他法。
父亲的倔强和耿直是刻在骨子里的,轻易无法撼动。就像这次输液,我们老早就劝他去看看,他便是不听,从年前咳到了现在。还是母亲说动了他,老两口谁都没见告,自己悄悄地去了医院,拍了电影,做了检讨。年夜夫说须要输液,父亲才乖乖地听了话。
我迈进父母家门的时候,他们刚刚从医院检讨回来。母亲一脸惊愕,她没想到我会去。我说,我不来还不会知道你们要去输液。他们不服气似的分辨,根本不用你,我俩就行,骑车去,骑车回,啥都不延误。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根本就不想让父亲骑车去,骑车回,但这话我不敢跟他们说。不仅由于代步车是他们的出行工具,父亲爱如珍宝,还由于我们谁都做不到每天守着他们,帮他们办理统统问题。
最初几年,父亲骑自行车接送孩子,后来体力不济,就买了辆代步车。只可惜,刚买了没几天,新鲜劲儿还没过呢,就被偷了。父亲心疼不已,好几天缓不过来,但离了它又高低弗成,忍着心中的痛和气,父亲又买了一辆,便是现在骑的这辆。它一贯随着父亲,可没少着力呢。
父亲刚开始说换代步车时,我们都不赞许,以为他这么大年纪,反应不那么灵敏了,街上的行人和车辆又那么多,万一磕着碰到了,可不是闹着玩的。但父亲的倔脾气上来了,眼一瞪,非要买。我们谁也不敢吱声,只好依他。
新车买来,终于安上了电动“腿”,父亲愉快得跟个孩子似的,见人就显摆:“别看这车小,可它灵巧啊,再窄的道儿,只要能走人,它就能走,上哪去都不用发愁了。”
骑上心爱的代步车,的确上哪去都不用发愁。除了接送孩子高下学,父亲还带母亲去公园,打柔力球、舞蹈,拜访住在附近的新朋故人故友,买买菜走走街,方便得很。不仅如此,小小代步车在父亲手里,还变成了搬家的“主力军”。
父母的新家离原来的小区不远,从老屋子往这边搬时,多亏不起眼的它了。新家是电梯房,装修完后,晾了一段韶光,然后买了点新家具,再把日用品一搬,就齐活。小弟说了,到时候找辆车,一趟搬利索。父亲说,你们忙你们的,不用管,我们不焦急搬。
嘴上说不焦急,脚下却一刻也没闲着。父亲骑着他的代步车,一趟趟地,就像不辞辛劳的蚂蚁,将旧家那边的东西一件件运到了新家。一床被子,一把椅子,几件衣服,或者锅碗瓢勺,不知不觉,竟然搬得差不多了。
确定了搬家的日期,我提前两天过去,想着帮他们拾掇拾掇,进门一看,不仅窗明几净,而且已经颇有家的样子了。我满脸迷惑,母亲说,这都是你爸的功劳,骑着他的小三轮一趟一趟运来的。
我埋怨弟弟,抽空找辆车,一趟就拉来了,干嘛叫父母一点点往这挪?多不屈安。不等小弟辩驳,父亲抢过话头说,是我不让,这家具都是新买的,直接送货上门,剩下的便是日常用品,我和你娘每天跟玩儿似的,捎带脚就捎来了,哪用得着叫车?他超市那么忙,犯不着再拖累他。
中午在新家开伙,包水饺。拉开架势,才创造削皮器、捣蒜器、喷鼻香油等等必备用品还没有。母亲说,老屋子那边有,叫你爸去拿,用不了多大工夫。
父亲应声去换衣服。爱人和弟弟都争着想去,父亲不让,一边穿鞋一边说,你们找不着,我骑车去,快。
儿子也坐过一次他姥爷的“专车”,回来后跟我一通“告状”:妈,我姥爷他骑车真是见缝插针啊,太吓人了,你一定要提醒他,叫他骑慢点。我苦笑着点头,一壁问他,你没提醒他吗?我提醒了呀,可我姥爷说,贰心中有数。儿子有些懊恼地辩白。
哪能不提醒?我和弟弟都不止一次提醒过,但奏效甚微。我嘴上答应着儿子,心里却无奈地叹着气。
父亲从十七八岁拥有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到如今“升级”为老年代步车,几十年的光阴里,遭遇过多少危险和困境,都被他遇沟过沟,遇坎过坎,逐一化解了,但个性却未有丝毫改变。在贰心里,事情放在首位,个人安危位于次席。
有一次去学区开会,赶高下大雨,母亲劝他跟领导说一声,不要去了,但父亲像没听见似的,披上雨衣就冲进了雨幕里。回来的时候才创造,村落西的桥被冲塌了,中间裂开了一道宽一米旁边的深沟。父亲扛起车子,奋力想跨过去,却脚下一滑,跌了下去。无法想象父亲是若何困难地挣扎出来的,等他一瘸一拐地回到家,已是下午,一头栽倒床上再也无法起来。母亲劝他去看年夜夫,父亲去世活不去,夜里疼得实在坚持不住了,熬到天亮去看了年夜夫,才创造摔断了肋骨。
还有一回是送我去汽车站。那时我还在县城读书,乡里通县城的公共汽车一天两班,上午一班,下午一班,我家离乡驻地还有八里地。一个周日下午,父亲带我去赶车,离车站大约还有三百米时,汽车逐步启动了,远远地可以看见它蠕动着的样子,父亲急了,一壁挥动手,大声喊着:等一等!
一壁加快了蹬车的频率。只见他全体人站了起来,将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了两只脚蹬上,自行车仿佛飞了起来。
我在车后阻挡父亲:肯定赶不上了,别追了。他熟视无睹,大概是真的没听见,依然奋力地蹬着车,不仅如此,他还命令我随着喊。司机显然也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唤,还在往前挪动,并逐渐提速。这时我们才拐上大路,眼见着汽车越开越快,父亲又扬声喊了一嗓子,脚下蹬得更加不顾统统了。自行车剧烈地旁边扭捏,我坐在车后座上,随着车子扭捏,心紧张得快要蹦出胸腔。就在快要追上时,对向开来一辆车,把父亲夹在了中间,如果不能立时退下来或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候,父亲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他以不可思议的速率骑到了公共汽车前面,并在它前方不远处停了下来。父亲歉意地向司机师傅摆动手,示意让我上车。汽车停下了。父亲弯着腰大喘着粗气,朝我挥了挥手。我跃上汽车的踏阶,转头跟父亲告别时,才把稳到他那蒸腾着热气的头发和挂满汗水的脸。
飞扬的思绪随着车速的减慢戛然而止。父亲逐步拐上医院门前的缓坡,将车稳稳地停在距无障碍通道一米远的停车位上。我下了车,想上前搀父亲一下,他却已自顾自撩开门帘走了进去,我只好跟在后面马首是瞻。从小到大,我已经习气走在父亲的身后。
躺在病床上,父亲溘然变小了,变乖了,年轻的小护士弯下腰,柔声细语地问这问那,又细细叮嘱着,像安抚一个孩子,父亲听话地嗯嗯着。护士挂好吊瓶,端起托盘,又叮嘱道,这只手可不要用力哟,小心再挨一针。父亲绽开谄媚似的的笑颜,笑吟吟地说,我听你的。
我借口送护士跟了出来。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回忆刚才的一幕,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我那执拗的、不听劝的父亲啊。
作者简介:闲云落雪,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齐鲁·青未了副刊签约作家,德州市作协会员,江山文学网逝水流年社团编辑。作品散见于《山东文学》《微型小说月报》《星星·散文诗》《西南作家》《屯子大众》《德州》《公主岭报》等多种杂志和报刊。
壹点号落雪有声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运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800位在线等你来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