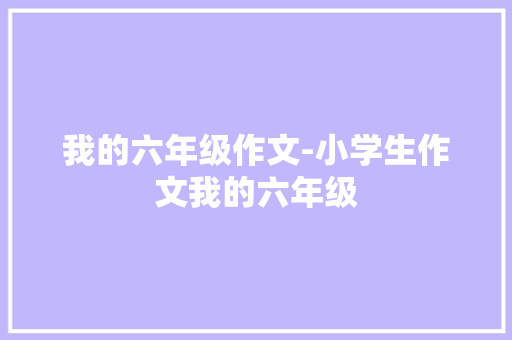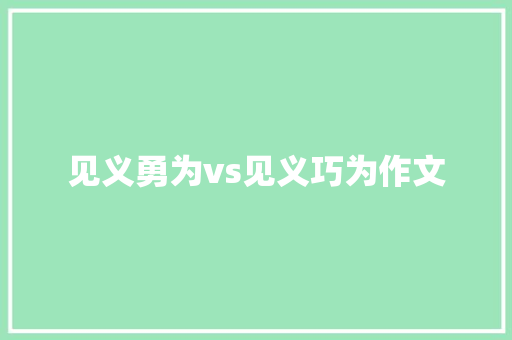十年后,这群昔日十五六岁、穿着校服的少男少女已经终年夜,生活的重心也从学习变成了事情、结婚、生子。
班上的女生陆春桥把镜头对准他们中的三个人,拍摄了一段32分钟的记录片,取名为《初三四班》。

“太多的电影在讲地震后的悲哀痛楚,却没有人去讲我们对生活的珍惜”,陆春桥提起拍摄的初衷,是希望记录下他们这代人的发展,讲讲他们是如何在经历灾害后,去理解家庭与爱的。
2008年9月,地震后初三四班第一次合影。受访者供图
揭开伤疤
12月26日,陆春桥拍摄的记录片将在腾讯视频上线。记录片的开始,是一场同学聚会。
2016年大年初三,陆春桥组织了一场初三四班同学会。那天,她扎着高高的丸子头,带着摄像机回到北川中学。
在陆春桥的镜头中:阳光铺满整间教室,蓝色桌椅整洁地摆放着。八年未见的同学按初中毕业时的座位坐下。
大家显得有些生疏。有人发起,轮流站上讲台,重新做自我介绍,分享这些年的经历。
女生母志雪穿了身亮眼的红大衣,化了淡妆,她站上讲台,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几年过得特殊好”,同学们在底下都笑开了。
在陆春桥的影象中,母志雪是个内向的人。初中时,她坐在陆春桥后面的座位,扎马尾辫,穿最大略的T恤和牛仔裤,非常文静,不爱说话。
但现在,她跟每个人都热络地开玩笑。她说她现在在施工队事情,梦想是当个包工头。
2016年大年初三,母志雪在同学会上发言。受访者供图
男生何林烛也站上了讲台做自我介绍,镜头中他平头,浓眉大眼。和初中时比较,变革不大,依旧外向、长于交际。
他高三辍学,留在北川,送过外卖、当过KTV做事员、开过婚庆用品店,是同学们心中的励志担当。
聚会那天,陆春桥拍了不少视频和照片。回去翻看时,她创造,同学们虽然都很年轻,但是看上去要比同龄人更成熟一些。陆春桥很好奇,“那场大地震到底是如何改变了我们这群人的生活?”
多年来,陆春桥和同学们很有默契,鲜少评论辩论与地震有关的话题。上大学去了外地,他们也不会主动跟同学提起自己来自北川。
陆春桥想,他们这些年的故事值得记录下来。地震过去8年,关于北川的故事,别人已经讲得够多了,如果换作自己来讲,会不会不一样?
要重新揭开这块伤疤,并不随意马虎。幸好是陆春桥来做这件事。初三四班的刘文静说,“别的来采访,总会有被消费的觉得,但她不一样”。她相信,陆春桥和他们是同类,对那段过往能产生共情。
幸存者陆春桥
陆春桥曾是班上最爱好文艺的女孩。上高中后,开始跟市里来的艺术老师学编导,大学在南京学拍照,毕业后去了上海的一家电影公司事情。
2015年6月,陆春桥上大四,和制片人韩轶谈天时,提及了那园地动。韩轶发起,这帮孩子的发展或许能拍个记录片。陆春桥被打动了。
她先是挨个给同学们打电话,久疏联系,陆春桥创造,原来她对老同学这么不理解:地震后,他们失落去了哪个家人、经历了哪些痛楚、有没有走出来……她一无所知。于是,陆春桥回到北川,开始跟同学和他们的家长详细访谈。
在记录片中,陆春桥访谈了自己的父亲,那天,父亲开着车,母亲躺在后座。父亲心不在焉地聊道:
“地震那天买了四吨多厚朴花,碰着地震了,就全部变成垃圾了,跟你妈在片口困了两天。屋子摇过去摇过来,就像舞蹈一样。第二天用柴油机发的电,看到新闻,说北川中学三楼变成一楼了。我想女儿肯定去世了,你妈就哭了,她整天都在哭,末了就要来找。”
2008年5月12日地震来的时候,初三四班所有同学都在室外上体育课,陆春桥站在报栏前看报。一瞬间,天下开始扭捏,传授教化楼倒了,漫天的灰尘扑过来,不远处的山被滚落的巨石、泥土包裹住,由绿变黄。
幸运的是,在操场的初三四班同学们都活了下来。
地震过后,北川中学的学生都被转移到了六十公里外的绵阳长虹影剧院。每天,影剧院都会播放寻人广播,“XXX同学,你的家人在找你”。第三天晚上,陆春桥躺在纸板上准备睡觉时,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她匆匆穿上长虹发的拖鞋,赶到影剧院门口。瞥见母亲站在人群中,背着一个双肩包,拄着一把伞,衣服破褴褛烂,脚上还穿着陆春桥留在家里的胶鞋。母亲原来白皙的皮肤也变得黝黑,一下子老了十岁。陆春桥想给她换上自己的拖鞋,才创造胶鞋已经陷进了妈妈的肉里,根本脱不下来。
陆春桥的父母接管采访。受访者供图
母亲阁下不见父亲的身影,她见告陆春桥,父亲的哮喘犯了,只好在家等着。这个从没落过泪的男人,还偷偷钻到了厕所里哭。
那年10月,陆春桥的妈妈生了一场重病。年夜夫说,是由于地震之后,她的精神处在崩溃边缘,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导致她患上了植物神经紊乱。生理上的表现是焦虑、烦闷,生理上则表现为胸闷、憋气等症状。
在此之前,陆春桥一贯以为,电视里演的烦闷症等生理疾病都只是纯挚的心情不好。妈妈罹病往后,她才知道,“原来感情也可以杀去世人”。
许多同学的家庭都被这园地动拆散了。母志雪失落去了父亲,地震时,他正在矿山上事情,没跑出来。何林烛失落去了六岁的弟弟,那是一个活泼聪明的小男孩,头顶有两个旋。
陆春桥一家是幸存者,同学黄金城一家也一样。他见告陆春桥,有时走在街上,会碰到一些故去同学的父母,他总会低着头,绕得远远的,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打呼唤。
“生活像吃糖一样甜”
母志雪父亲在世时,希望她将来能当老师或者司帐,过安稳轻松的生活。高考填志愿,她却决定去南充的一所专科学校学土木工程,“修出结实的屋子、结实的路,会特殊有造诣感。”
在大学,同学听说她来自北川,免不了问几句地震时的情形,母志雪并不抗拒。但他们听说她父亲罹难后,总会用同情的目光打量她,这让母志雪受不了,“我会跟他们说,不要心疼我,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只是比你们多经历了一点”。
2016年,陆春桥找到母志雪时,母志雪正在成都的一个工程队事情。她卖力做施工资料,记录施工的全过程,要整天随着工程队到处跑,“和工人待在一起很愉快,特殊喜好这样的生活”。
那时,她刚开始谈恋爱,没过多久就决定结婚,“随时都像吃了糖一样甜”。丈夫陈翔性情内向,陆春桥来家里拍摄时,他会含羞,藏到厕所里。母志雪笑称他是“贤内助”,和自己的性情恰好互补。
结婚后,母志雪一闲下来,就会带着陈翔回老北川走走,给他讲自己玩过的地方、读书的地方、和父母一起去过的地方。
进入老北川,要经由一条尘土飞扬的道路,狭窄到只能容纳两辆车经由。曾经热闹的县城只剩下了断壁残垣,四处是东倒西歪的楼房。一扇扇破碎的窗户里,藏着剥落的墙面和倾倒的家具。从地缝中探出头的杂草和野花,是这里仅剩的活气。
陆春桥说,她回小坝乡时,也会经由老县城,“到现在都彷佛还能闻到当年石灰粉和消毒水的味道”。
地震后,母志雪的母亲以为母志雪已经不在了,带着小儿子到北川中学,打算“翻去世人”。见母志雪还活着,仨人哭作一团。母志雪问,爸爸呢?母亲只是摇了摇头。
失落去丈夫往后,母志雪的妈妈整天以泪洗面,也吃不下饭。为了逗母亲愉快,母志雪每天给妈妈打电话,讲笑话、打趣。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她也逼着自己爽朗起来,没心没肺地笑,不肯望被分外对待。
逐步地,母志雪创造,她喜好这个“把心放得很大”的自己。“对我来说,我已经够幸运了,至少老天还给我留下了妈妈和弟弟”,母志雪说。原来,母亲要和父亲一起去矿上上工,那天却阴差阳错地没有去。
母志雪的母亲在领了几个月的救援金后,回绝了外界的帮助,决定要找一份事情,自己挣钱养活孩子。她听说陈家坝有个人卖卤肉很有名,她就跑到人家门口等,求他教自己做卤肉。
于是,小小的卤肉摊成了百口唯一的生存。“地震后我妈对我和我弟更好了”,母志雪说,“她想让我和我弟过上和普通家庭一样的生活,让我们活得更自傲。”
在记录片中,陆春桥采访了母志雪的母亲,母亲那天扎着马尾辫,一张圆脸,眼角堆满了皱纹。她没有哭,看似轻描淡写地聊起了逝去的丈夫。
“他们一起干活的有11个人,11个人一个都没出来。一年后,那边修路,又把他的尸体挖了出来,我又把骨头捡回来埋了。”
陆春桥问,“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
“实在自己的亲人就不怕,没有什么觉得”,母志雪的母亲笑了笑,“只是想着他能活过来就好了”。
何林烛的任务
在23公里之外,新北川在震后两年内拔地而起,所在地被取名为“永昌”,意为“永久昌盛”。城区整洁划一,有宽敞的马路、林立的高楼,重修了北川人的生活。
安昌河支流穿城而过,河东是当代化的居民社区、政务中央和旅游做事中央等,河西是北川中学、河西医院等公共做事建筑。在县城的中央,还建筑了“巴拿恰”(羌语,意为“市场”),到过节时,羌族公民都会换上民族衣饰,在这里相聚。何林烛每天就骑着电动小摩托车在新北川县城送外卖。
何林烛正在送外卖。受访者供图
2011年,高考过后,初三四班许多同学离开了新北川,到其他城市上大学。如今,许多同学都回到了新北川。
陆春桥曾问过留在新北川的同班同学:有没有后悔地震后留在北川?同学回答,去外地会被人分外关照,但在北川不会,“这里收容了所有受伤的心灵”。
何林烛也是留下来的人。他见告陆春桥,成都是他去过最远的地方,他原来打算在成都多待几年,由于妈妈,他决定回到新北川。
地震前不久,何林烛的父母离异了,由母亲一个人抚养他。地震后,弟弟去世,家里一贫如洗,全靠母亲在菜市场开的小店支撑。
何林烛很早就有了金钱的观点,常在中学宿舍倒卖小零食,挣个几毛钱。从家去学校间隔远,走路要三四十分钟,坐车只要一块五,他也舍不得花。
刚上高中时,何林烛学的是美术,期待考进艺校,成为一名美术事情者。但高三上到一半,他决定辍学打工。他仔细掂量了好久,认为自己最多只能考上专科,摧残浪费蹂躏钱不说,毕业了还不一定能找到好事情。
何林烛辍学后,带着仅有的两百块独身只身到成都闯荡。刚开始几天,何林烛白天找事情,晚上睡网吧。后来,他一天打三份工:送外卖、做家政、在KTV当做事员。每个月能挣七八千块,全都寄给母亲。
在KTV的事情最辛劳,身边的同事一拨接一拨地换,何林烛升上了主管。有时,他也会倾慕那些干了一个月就辞职的人,他也想像他们一样任性,但没办法。
何林烛部下的职员很多都是十几岁的小孩,看着他们,何林烛常想,如果弟弟还在,该当和他们差不多大,现在是在上学,还是已经像他们一样出来闯社会了呢?
何林烛回顾说,弟弟以前是孩子王,喜好带着一帮小孩出门玩,每到饭点,妈妈总会让他去叫弟弟回家。
弟弟走后,只给家人留下了三张照片,分别由何林烛和父母保存。留在母亲那里的是弟弟六岁时一个人去摄影馆拍的证件照。小男孩穿着橘色的外套,皮肤白净,单眼皮,招风耳,笑得羞涩,跟何林烛长得很像。
何林烛在成都待了一年半,便回到了新北川,他对着陆春桥的镜头提及回来的缘由:
“当时我在成都休假回来,我晓得我妈跟继父吵架了,当时看到我妈在那哭。我当时在想,他们如果再离婚的话,我妈在新北川只剩下一套屋子和一条狗了,没有谁陪她。也是由于地震,我弟弟不在了,再加上我爸妈离异,当时我脑袋里就想,哪怕我在表面挣再多的钱,如果不能陪在她的身边,我挣那些钱也没什么意思。”
“我妈真的很不随意马虎、很累,她是个女强人,我真的很佩服她。爱到深处是陪伴,我也以为是情到深处了,我就真的离不开她了。”
当时,何林烛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始终都是笑着的。
回了新北川后,他连续送外卖、去KTV打工。也考试测验过自己创业,开过一家叫“青春饭”的饭店,冬天卖板栗,夏天卖冰粉。“凡是能挣到钱的,都会试着干”。
我们的家庭与爱
十年过去,想起爸爸,母志雪更多的感情是遗憾,遗憾他没能见证自己的发展。影象中的父亲顶着一头卷发,高大帅气。小时候,她和弟弟总是缠着要爸爸背,在家门口的空地上跑来跑去。
地震前不久,十五岁的母志雪以为自己的姓不好听,偷偷拽着妈妈到了派出所,想改姓。地震过后,母志雪再没动过改姓的动机,“姓氏是爸爸给我的,那是我们之间最好的连接”。
最开始,母志雪理解不了父母的感情,不明白真正的爱情到底是若何的,直到遇见陈翔。“我当时耍朋友不是很负责,学校里的感情我不知道怎么去衡量。人要真的走到这一步,才理解我妈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2018年2月5日,母志雪和陈翔结婚了。婚礼前,母志雪带着陈翔一起去祭拜了她的父亲,陆春桥记录下了这一幕:
“在今后的生活中,永久都见不到他了,真的是很遗憾。事情、结婚、找到陈翔这样的人,我在想我爸假如看到陈翔这个样子,会不会满意啊?我有的时候在想啊,你能多活过来一天,就一天,我给你讲讲我15岁到25岁这十年。”
在母志雪的婚礼上,母志雪的母亲把母志雪的手交到了陈翔手中,三人相拥。那一刻,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客人们都打开了手机的闪光灯,跟随音乐,缓慢地摇着。那是所有镜头中最打动陆春桥的瞬间。
2017年,何林烛也结婚了,妻子是在KTV认识的同事,一个活泼爽朗的姑娘。今年4月,妻子又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他希望能养活一家人,过上稳定的生活。
何林烛辞掉了在KTV的事情,最近,他在绵阳学婚庆主持,操持回北川开一家婚庆公司。他还在左脚踝上文了一只小蜗牛。他以为自己便是蜗牛,背着重重的壳,缓慢地爬着。但他不累,由于壳里住着他最爱的家人。
记录片中,何林烛总结了他这些年的感悟:
“我以为我们经历了地震的这一代人,跟表面没有这段经历的年轻人来比,我们更懂得生命的主要,特殊是家,还有便是自己对自己的任务。”
2018年初,陆春桥的拍摄进入了尾声。她彷佛找到了答案,那些留在北川的同学大多数都在地震中失落去了亲人,他们选择留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陪伴身边的家人。
陆春桥看到了母志雪对父母感情的感同身受、何林烛对家庭任务的重视。她想知道,自己的父母看到别的孩子都留了下来、陪在身边,自己的孩子在上海为梦想奔波,心里是怎么想的。
春节前夕,陆春桥为父母换上了羌族的民族衣饰,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摆了一张椅子,母亲抱着狗,父亲一脸严明。陆春桥躲在摄像机后面。
陆春桥问:像何林烛比较早在北川创业,留在他妈身边,母志雪很早就结了婚,我几个月不回来,你们有时候会不会难过?
母亲答:还是有哦,但是我又想,没紧要,只要她过得好就得了,出息好。
父亲答:你说呢?肯定想,自己的女儿这么远,出门在外,儿行千里母担忧。
母亲眼泪落了下来:我要哭了,我不哭,我忍住。
父亲:是啊,不管你钱多钱少,一家人每天在一起,多巴适,多幸福。
母亲:你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我们原来两个人,还年轻,跑得快,现在我们岁数越来越大,只剩下了两个人,娃养大了不在家里了。特殊是生病的时候,想着想着就以为好不法,这是我的心里话。
记录片放映
12月16日下午,《初三四班》在北川电影院首映。
陆春桥刻意避开了那个分外的日子,把日期定在了今年的末端。“12月意味着一年的终点,对我们而言,也是上一个十年的终点”。
12月16日,首映仪式上,三位主角和他们的家人。受访者供图
班上的同学都回到了这座小县城。母志雪剪了一头短发,挽着丈夫和母亲,甜甜地笑。何林烛的宝宝成了焦点,孩子刚八个月大,挥着肉乎乎的小手,好奇的眼睛不住地眨。
看电影时,老北川的画面闪过,黄金城想到了自己的家,白色外墙,蓝玻璃。自己房间门口的柜子上,还摆着十四岁时的生日礼物,是那个年代最盛行的水晶苹果和纸星星,全是初中同学送他的,地震后也没机会再拿出来。
弟弟的照片涌现那一刻,何林烛没忍住掉了眼泪。
“很多年来,那园地动都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韶光可以治愈统统,当地震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这些幸存者,无论是创业、事情,或者是结婚,我们都在努力地探求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班真的很幸运,但幸好大家都在努力地不辜负这份幸运。我们这群人是分外的,但也是普通的。经历了这场大地震活了下来,但是生活依旧还在连续,我们也要面对和你们一样的发展,也要在争吵和沉默后,终极学会理解父母,也要在努力事情后,懂得承担任务,也要在跌跌撞撞往后,碰着可以相互陪伴的人。”
电影的末了,是陆春桥的独白。
(感谢腾讯“谷雨操持”对本文供应的帮助)
新京报周小琪
编辑 陈晓舒 校正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