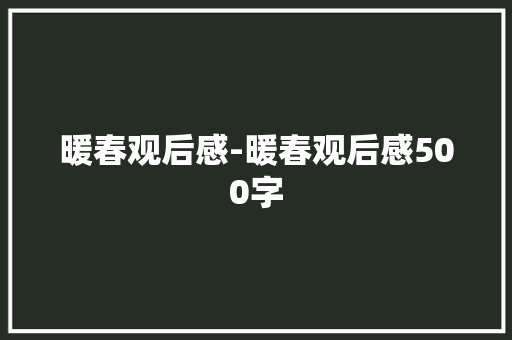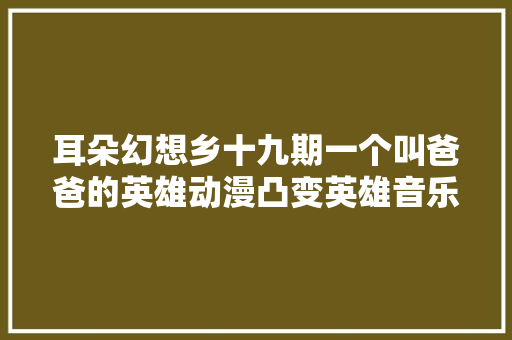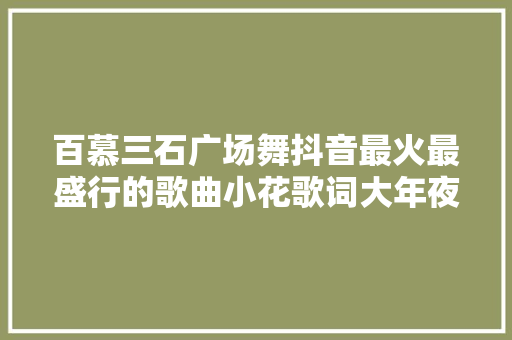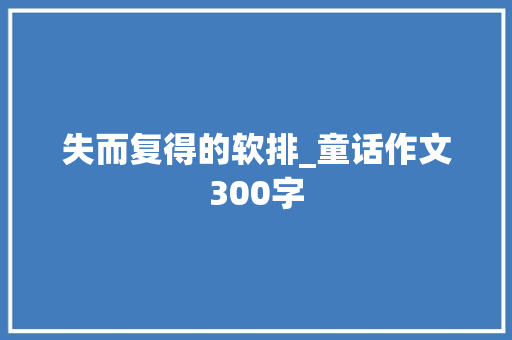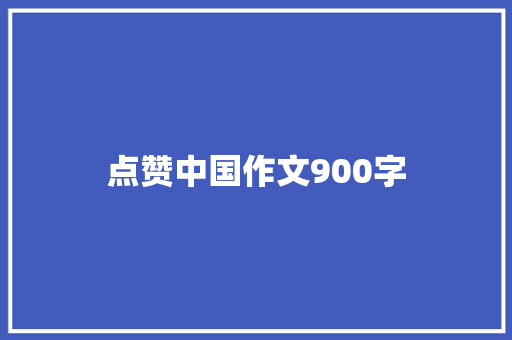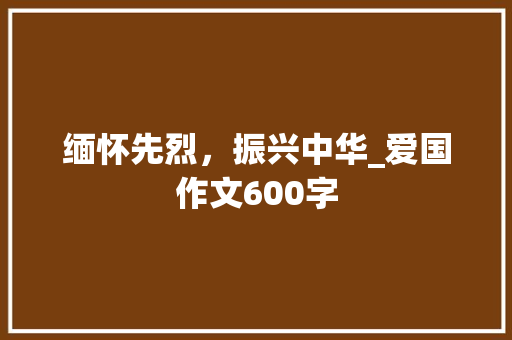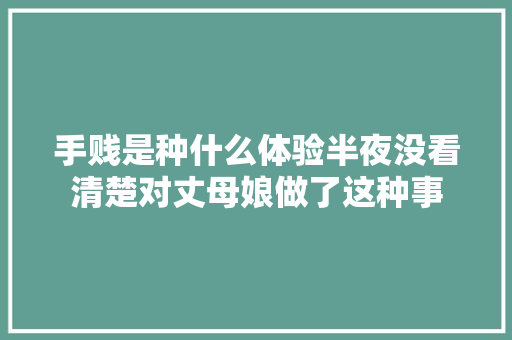一朵新颖新奇的小花
电影《小花》取材于军事题材小说《桐柏英雄》。由作家前涉于1972年创作的《桐柏英雄》,紧张讲述的是1947年我军由计策防御转向计策反攻这一历史期间,在桐柏山区与国民党反动派大胆奋战的故事。小说构造弘大,盘根错节,人物浩瀚。如何将这部小说改拍成电影呢?导演张铮等主创职员大胆创新,重塑叙事构造,将战役场面设为故事背景,将影片重点奥妙聚焦在兄妹亲情上。通过对战役中人物个体命运的关注来歌颂革命战役,一改昔日军事题材电影的“大场面”“大制作”“大英雄”的模式,其别具一格的叙事方法、创作表达和审美特质,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艺术空间。《小花》上映后,不雅观众反响空前,好评如潮。该片得到了文化部1979年精良影片奖,1980年在第3届百花奖中得到最佳音乐奖等四项大奖,《小花》成了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成为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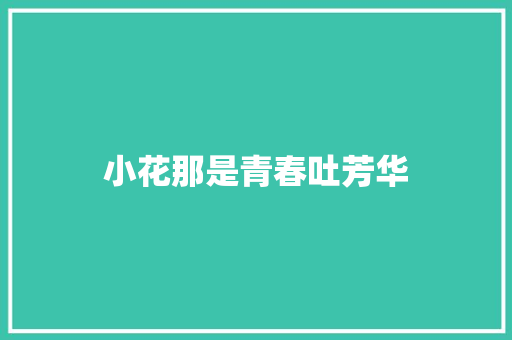
《小花》之以是能够取获胜利,缘于以下几点:
一是于小说是取材而非改编。将小说文本改为电影文本,褪去以往战役英雄的钢铁外壳,专注于英雄血肉之躯的柔情与忧闷,打破人物塑造“高大全”“三突出”等整洁划一的范式限定,从歌颂伟大的战役场面到关注人物个体的自身命运,更多地着力于对处在战役年代的“人”的不雅观照和关注。通过人性与人情,引入不雅观者对战役的思考、反思,替代直白、白描的战事描写,这成为影片的一大亮点,也是其之以是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是妙在“两朵小花并蒂开”。影片奥妙设置了两个女主人公,两个人都是“小花”。《小花》的片名具有双重指代浸染,不仅指代电影中由陈冲扮演的赵小花,也指代电影中由刘晓庆扮演的何翠姑。借由“换子”的情节安排,两个原来身份不同的女性得到了同一的身份——“小花”,并对这一身份进行着不同侧面的阐释。“两朵小花”没有亲缘关系,却由于战役年代的各类巧合有了胜似亲缘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两个不同的人物塑造同一个形象,形成互文的表达效果。
三因此情绪人,具有抒怀诗般的清新风格。《小花》在艺术上的显著特点便是敢于写人的情绪,敢于以情绪人。合营影片主题“兄妹情”,在陪衬抒怀气氛的视听手腕上,亦是形式多样,极大增强了艺术传染力。比如两个“小花”踩水车谈心、兄妹于青翠竹林中团圆见面、翠姑奄奄一息时波光粼粼的海面与阳光穿过树叶的亮斑等,皆表现出强烈的抒怀特色。部分情节的影像呈现更为诗意化,动听至深。比如何翠姑为救身负重伤的赵永生,困难地抬着担架走在波折的山路上。她咬牙坚持一步一步跪着上山,膝盖磨破,鲜血染红了山道的石阶。伴随着《绒花》那极具浪漫与温情的音律,画面与音乐相互领悟促进,形成了一种细腻蕴藉的美感,赞颂了主人公崇高的思想、美好的心灵。
四是旋律幽美的主题曲和插曲。由著名词作者凯传作词、影视音乐作曲家王酩作曲的主题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和插曲《绒花》,以新的角度和形式表现影片的主题,格调清新、缠绵细腻,有着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如果说主题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像是一首委婉、缠绵的叙事诗,那么插曲《绒花》便是一首悠扬、动听的赞颂诗。它们推动了剧情发展,升华了主题内涵,给不雅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听合一的震荡,深为人们喜好,传唱至今。
革命之情与亲情:两个“小花”的故事
对革命情绪的歌颂与弘扬一贯是新中国成立后战役电影的核心主题。电影《小花》在如何讲好革命故事上确实是匠心独运。不同于以往大多数战役主题的电影只是单一展现革命情绪,《小花》是将亲情奥妙融入于革命情绪,使之增长温情与人性色彩,使革命情绪呈现为一种亦是亲情更胜似亲情的亲密感情。《小花》的故事铺陈便是这样设计的。
故事源于一个桐柏山区的赵姓穷苦人家。一日,由于生活困苦,夫妇二人不得已将尚处于襁褓中的女儿赵小花卖与他人。当晚,伐木工人何向东却送来一个与小花同龄的女婴,希望他们夫妇抚养。本处在卖女痛楚中的夫妇二人,当得知这个女婴的父母是地下党员,因战斗须要只能将她寄养于老乡家的情形,毅然赞许。女婴原名董红果,小花父母思女心切,给红果也改名为“小花”。赵家儿子赵永生一方面对收养的小花妹妹疼爱有加,另一方面将探求亲生妹妹小花的欲望深深埋于心底。何向东将董红果送与赵家后,一贯探求被卖的赵小花。多少年后终于寻到,并将之赎出。因战乱迁徙找不到赵家之人,故独自将其抚养终年夜,改名为“何翠姑”。多年后,赵永生参军奔赴沙场。小花失落去哥哥音讯,在贫苦岁月中苦苦煎熬,“妹妹找哥泪花流”,找到哥哥便是她最大的欲望。一次有时,寻兄无果的小花却在部队卫生队碰着亲生母亲周年夜夫,她也在苦苦寻觅自己的女儿董红果,但此时二人相见不相识,但冥冥中彷佛相识的情愫使周年夜夫将小花认了干女儿。而此时真正的小花何翠姑,已经发展为游击队员,并在一次战斗中救了身负重伤的赵永生,但她却不知他便是自己的亲哥哥,赵永生也不知道救了自己的这个游击队员正是他多年苦苦寻觅的亲妹妹小花。在一次战斗中,小花与哥哥相逢,两朵小花也就此相遇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翠姑有时与养父何向东谈起小花找哥哥,才得知自己被卖的出生,而赵永生便是自己的亲哥哥。在后来的战斗中,翠姑为了救小花而受重伤,永生和小花一起去医院看望翠姑。在生命的末了时候,翠姑终于与自己的亲哥哥团圆,小花也和自己的亲生父母相认。末了,被救的小花接过哥哥手中的枪,踏着义士的足迹,开始了新的战斗。
影片中,两朵小花的命运推动着多少叙事线索交错并进,父母与孩子离散、兄妹离散,两个因战役而支离破碎骨肉分离的家庭之苦,因战乱而更加凸显的兄妹情、骨肉情,以及为革命战役前赴后继的两代人的火热空想,跃然呈现在不雅观众面前。
用亲情与人性的墨汁书写革命之情的伟大,这是《小花》带给时期的震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作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哀求文艺作品应将现实和空想、革命实践和历史趋向结合起来,塑造壮丽动人的艺术形象,激情亲切歌颂革命的新生事物,鞭笞反动的腐烂事物。从“革命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影片不仅突出了赵永生三兄妹同国民党军官丁书恒之间尖锐的敌我冲突与抵牾,而且几次再现敌我之间真实和残酷的战役场景。与此同时,影片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光鲜特色。无论是赵永生还是两位“小花”,都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被授予了浪漫主义的革命情怀,成为当时银幕上真善美的空想化身,使影片充分表示了革命现实题材“浪漫化”的美学追求。
绒花!
绒花!
一起芬芳满山崖
赤色经典作品是有着非常繁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的。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其主题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丰富性、多样性;另一方面,经典作品个中蕴含的精神内涵,仍是超过时空最为闪光的力量。《小花》中主人公身上所表示出来的那种“浩气长存宇宙间,耿耿赤心悬日月”的革命精神、捐躯精神,直到本日依然让我们冲动不已。当我们看到影片中共产党员董向坤和周年夜夫因革命而别离自己襁褓中的女儿,永生娘不顾家境贫穷毅然收养了革命者的孩子董红果,看到迎着阳光,头上淌满汗水、膝盖被磨破浸透着血水、脸上却洋溢着武断信念的何翠姑,看到何翠姑为保护小花而身受重伤等场景时,听到插曲“啊,绒花!
绒花!
一起芬芳满山崖”时,泪水依然会润湿我们的眼眶。
影片名称最初并不叫《小花》而是叫《觅》。后来剧组主创职员征询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斐的见地,钟老沉思良久,说“不如片名就叫《小花》吧,希望它是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妹妹找哥泪花流》和《绒花》更是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音乐经典。2017年底上映的《芳华》带领不雅观众又一次重温《绒花》这首老歌,演唱者空灵的嗓音和饱满的情绪,再一次带不雅观众重回那些逝去的光阴,体会上一代人在战火、集体和赤色中所谱写的“青春之歌”。《绒花》作为一种怀旧的契机,串联起两代人的“芳华”,在不同历史语境之间传达呈现代中国的诗意与冲动。
〔作者系中心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