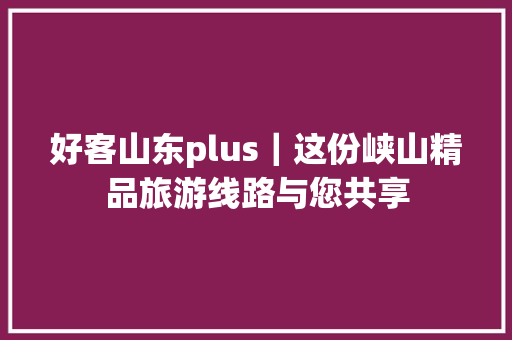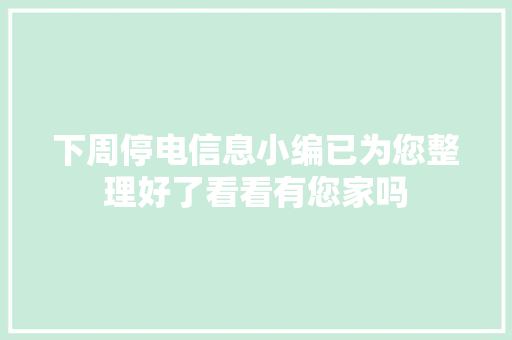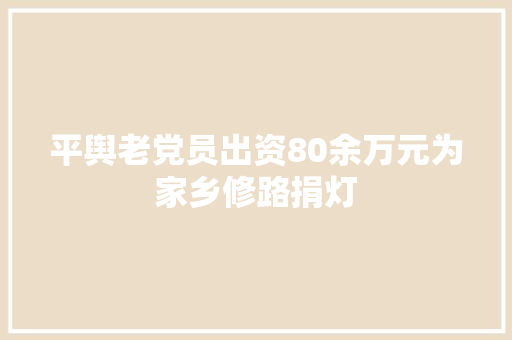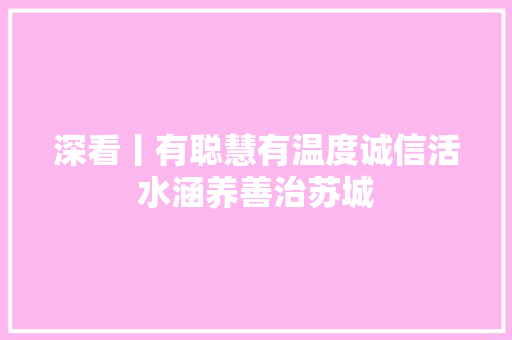我的家在辽斜
文/许方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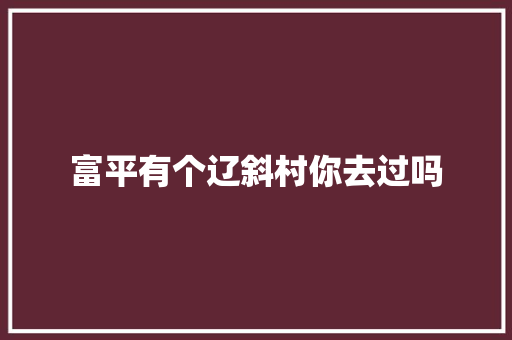
我的出生地在富平老庙辽斜村落,位于大水峪峪口东侧,万斛山脚下,对面是菩萨山(金粟山),脚下是利贤渠、老渠、铁渠三条老渠,还有农业社时修的名为胜利渠的一条新渠。有山有水,高山流水发财,也算一处宝地吧。
村落庄有田、许两大姓,是田许俩拜把兄弟明朝时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来的。兄弟俩娶妻生子,生生不息,现有200户人家,600口人,基本各半。分社时,村落庄又从中间划开,分为辽南、辽北两农业社。村落里还有三棵1200年的老槐树,耸立在村落头村落尾,遮天蔽日的,树身已然有点空,见证着村落落的古老和久远。
小时我们没少钻树洞,村落中间那棵,阁下便是城门楼子,我们也没少爬。树上用铁丝挂了半个铁家伙,一敲,社员上工了,一敲,社员开会了。上学也在城上,大队村落小。说城,实在也便是土墙垒起,阵势高高,起先是窑洞、石油灯,后来瓦房、电灯。老师们则烧土炕生煤炉。煤学校发,烧炕的柴火学生上山砍。后来学校盖瓦房,学生们上山拉槐树棍棍窑里搬砖头。
紧挨着村落庄的是富广路,原叫送华路,是老庙和峪岭两村落夫民出大力流大汗没任何机器硬是从山里修出的一条路,我们叫她汽路,也是唯一能通汽车的路。靠着她我们出山进峪,靠着她我们和表面天下连接。现在村落民出行随意马虎多了,屯子班车招手即停。
村落庄算是处于黄土高原的末梢,先民们开辟出层层梯田,大小不一,土里刨食,地种得也都踏实,山都烧了,开荒。河沟旁的,夏天发大水时才能漫灌,肥沃些。但秋庄稼有时会淹。老早每年沟里发大水,核桃、木头都冲下来了,后来再没见水。山畔里则是旱田,靠田舍肥,后来有了化肥。现在则一律退耕还林,经济作物花椒树。
靠山吃山,大山里产片片石,父辈们多采石为生。早早起来,把饭一咥,绳子盘好,装两个蒸馍当午饭,推着贴地的包着铁皮的独轮车上山。各家有各家的山,“明山”把上面土推掉,露出全体石头;“暗山”则挖洞穴,有时还用雷管,曲曲拐拐,很深,里面得点灯。那个年代时有山窝子倒塌压去世人事宜发生,就像秋日连阴雨村落里窑洞倒塌一样。
只见石头一层一层,厚的作成锤布石、门礅石、石碑、牛槽等。薄的则各种瓮盖子,装面盛水。手艺好,瓮盖子都下得圆圆,可一起滚,像滚铁环?那时奇怪,村落里上了年纪的枕青石枕头,说头凉复苏。也是山里出。我母亲则木头枕,父亲青石枕。爷爷辈全部青石枕,黑油发亮。
天快黑了,石匠们才纷纭装上自己做的石头制品,推着车车下山了。没技能的则做发卖——拉石头换粮。头天晚上装好板车,鸡叫头遍,起来咥过面疙瘩(这种吃食大略易做,还压饿)。套上牲口,叫上差错,带上能吃几天的蒸馍和盘缠上路。碰着大坡,相互能帮忙推车。目的地,泾阳、三原。晚上住宿找队里的喂养员,便宜。有时则在打麦场上,麦秆堆里拱一夜,出门都带被子。三四天就卖完,石头换粮,粮再粜给粮站,南川里的农人手里没钱啊,粮有的是。
(饭店旅社从来不敢进,碰到年夜大好人家,给点热乎的吃。父亲在那边还认了几个朋友,有个落脚点。石头一到,朋友也能帮忙在村落里吆喝。有一次,在一换石头人家吃了饺子,要一元钱,父亲后悔得,早知不吃了,不知道人家还要钱。那时候的冬天真冷啊,带被子从不带褥子。)
父辈们,一趟又一趟,冬去春来,为的是养家糊口。没手艺的父亲自然是下苦力,拉石头换粮,家里娃娃多,又都念书,自然比别人更辛劳。我小小的就随着父亲换粮,师范毕业事情了,还和父亲去换粮。父辈,换粮,后生则上山割条子编笆笆。
曾记得,我,建娃应娃弟兄俩,通亮自远自顺弟兄仨,半夜三更,带上硬棒捧的黑馍玉米面粱粱,一个叫上一个,结伴到龙头、清峪、东山割藤条。赶天明就要到山上,在密密的灌木丛里,找见一根,割一根,割够一把,连续第二把、第三把,从山沟到山顶,再折身收条子。灌木丛中穿来穿去,挂烂衣服划破手脸是常事。末了,打成结实的一捆,太阳也快落山啦。
中午就吃了冷馍,喝了点山泉水,背着去世重的藤条下山,路都走不稳,晃晃荡悠。太沉了,到什么地方歇脚,是一定的。还不能老歇,天快黑了,何时到家啊!
?以是不达目标不敢歇。到了目标,稍歇少焉,又赶紧前行,又赶往下一个目标。咬紧牙关,牙关要紧,冒死前行,几度累得想哭,正是长身体年事啊,“摧残”吧。
写到此,我忍不住落泪。等到家了,人已稀软,饭也不想吃了,倒头就睡,骨头像散了架,全身疼痛。
不写了,太恓惶了!